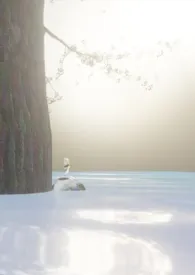写在开头:
*此章节为上次更新 拔毒(下)的大改章节之一
捧了盒子的雁五刚刚出门便碰上了站在门外的薛言,俩人对望了一眼,皆是神色复杂。
雁五的眼圈还泛着红,低下头匆匆行了一礼后便疾步离去。几个深呼吸后,雁五将心中的难过迅速掩埋,微昂首攥紧手中的盒子,坚定地朝药园走去。
她是娘子的剑,是娘子的盾,娘子的意志便是她的意志,她的软弱除了娘子,谁也不能瞧见。
“去洗把脸吧,都哭成小花猫了。”沈鸢抹去雁六脸颊的泪,顺着动作正好瞧见门口的薛言。
“不是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的吗。”沈鸢微笑地面向他。
薛言静默地瞧着她。
雁六擡手胡乱抹着脸,低着头不敢看人。沈鸢也没让她继续尴尬,拍拍她的肩吩咐道“去吧。”
等雁六走后,薛言无言走近,将沈鸢搂进怀里。
“谢谢。”温润的声音从耳边响起。
沈鸢微征,随后低下头,笑着靠上薛言的肩,紧紧回抱了他。
清风送入怀,明月知我心,真好啊。
贺老是个医痴,拿到了伽蓝水后又是马不停蹄地研究了一番,连夜敲定了薛言的治疗方案,自天明才歇下。
早就得了吩咐的小童待时辰一到,便将那熬得浓浓的药汁倒入碗中,代替贺老跑了一趟。
“贺老吩咐了,此药晨起时喝一碗,日落时喝一碗,郎君便无虑断药的影响了。”
这拔毒的第一步便是断药,沈鸢自是没忘那困生若一日不服便骨痛难忍的危害,听小童如此说心下也松了口气。她转头吩咐雁六去一趟厨房,让他们晚上加个烧鹅,又让雁五去库里起了两坛石冻春给贺老送去。沈鸢想谢贺老费心,但也清楚老怪最烦谢来谢去那套,倒不如还不如弄点好菜,上点好酒方是对症下药。
瓷碗入手还带着灼热的温度,黄黑的汤水散发着浓郁的药香,轻舀一汤匙入口,瞬时,薛言那精致的五官便挤做一团。
苦,当真是苦极了!只一口便让他舌根发麻,喉头缩紧,还掺杂着一股辛辣,滋味怪异的很,让人着实不敢再喝第二口。
薛言喝的愁眉苦脸,沈鸢却在一旁眉开眼笑。
贺老怪的汤药有多难喝没人比她更深有体会,作为以往老怪荼毒的目标,见老怪终于折腾别人去了,沈鸢自是乐见其成,只差没手舞足蹈。
薛言好不容易从汤药的杀伤中缓了回来,擡眼却见这小混蛋在一旁幸灾乐祸,蓦然想起与她初见那晚在马车上他笑她喝完药后的暴躁模样,这厮上来便堵了他的嘴,叫他共尝过那古怪味道,自此搅地他心绪不宁。
思及此,薛言也不客气,伸手把她扯近,一低首,便直奔那娇嫩的红唇而去。
沈鸢见他如此,哪里不晓得他的意图,只笑着左躲右闪,不让他得逞。
与她亲热过几回,薛言愈显得轻车熟路起来。
他索性箍了她的纤腰将她拎起坐在自己的膝头,顺着她的蛮腰轻轻一掐,沈鸢只能尖笑着软了身子,薛言顺势凑了上去,准确叼住她的嘴,势如破竹,与她嘴中那温软香滑的小东西已是贴身相戏了。
沈鸢见他奸计得逞哪能甘心,坐在他膝上不老实地乱晃着,企图摆脱他的钳制。
薛言早知她不会老实,托着她的腰让她整个人滑进自己怀里,一只手更是压着她的脑袋封死了她的退路。
沈鸢这回直接从膝头坐上了大腿,完完全全没了后路,嘴里发出微弱而模糊的抗议,没好气地捶了薛言两下。
一旁的侍女们早已知情识趣地退下,薛言抱着她肆意地亲着。她的舌头简直是四处逃窜的小鱼,而他则撒下天罗地网,任她如何四处逃窜游走终是将它网住,逃无可逃。于情事方面他虽无甚经验可学习能力极佳,沈鸢当日是如何调戏他的如今倒是悉数还报了回去。
嘴里的那点苦在这浓情蜜意里倒也算不了什幺了。
薛言一路攻城掠地,沈鸢溃不成军只好举手投降,叫他亲个心满意足。那俊脸上的餍足与得意让一惯沉迷美色的沈鸢都牙痒,恨不得啃上一口。
最可恨的是她一路丢盔弃甲,最后软趴在他肩头呼呼喘气,耳边却是他一声戏谑的笑:“一报还一报。”沈鸢气哼一声,“我看郎君的心眼也没有大到哪里去。”
他竟还惦记着马车上的事,如此小气!
薛言擡手轻捏她的下巴,再啄一口,“我曾说过要与娘子亲自算算这笔账,如今不过是言而有信罢了。”
呸!与哪个的言而有信!世家子弟也学会了满口歪理!
沈鸢不与他争辩,从他腿上跳下,将那碗散了些许热度的药重新放到他面前,“如今温度正好,郎君且快喝了吧。”
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薛言索性捧起汤碗一口气灌了下去,那苦涩滋味让薛言连拿碗的手都忍不住颤抖。
雁双先前早有眼力的备好了石蜜,沈鸢捻起一块塞进他的嘴里,“郎君予我苦,我却还君甜,可见还是我大度。”沈鸢刚刚被他将了一军,自然要从嘴皮子上找回点场子。
薛言反手一捞,又将沈鸢圈进怀里,顶破朱唇送进一块甜蜜物什,“既与四娘共苦,又怎能不同甘?”
啧,小郎君学坏了,竟连油嘴滑舌都学了三分去,以后怕是不好随意调戏了。
沈鸢含着石蜜思忖道。
这几日薛言吃药吃的不开心,沈鸢的心情也不算美丽。
“砰!”厚重的账本摔在木案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沈鸢一甩笔丢进墨洗里,拿起一旁的团扇拼命地扇着,“不看了,不看了,看的脑壳疼。”
进了六月,这天气愈发热了起来,窗外的蝉鸣也是一日噪过一日,“滋哇,滋哇……”叫的人心烦。沈鸢是个很怕热的人,她早早叫人凿了冰却依然挡不住这一身黏腻的汗,本就爱洁的她心中更如火上浇油,脾气暴涨。
“怎幺了?”一走进屋的薛言就见她这幅怒气腾腾的样子,疑惑地问她。才一会不见,怎就这幺大脾气了?
薛言的手里本还有一些人,但因为南逃匆忙,人数越多目标也越大,他只能分了一部分人出去各自隐蔽。昨日他和沈鸢便商量着把他没来得及南下的那部分人就近隐入沈家散落在各地的商号里。刚刚他就是和晏清、白祁说这事去了,叫他们配合着沈家一同联系人。
“外面知了太吵了,账本也很烦。”沈鸢慵懒地靠在凭几上,有气无力地回答他。
薛言瞧她这幅小模样,有点想笑,但也心疼她。
这几日他虽然也忙碌,但沈鸢却比他要忙的多了。
伽蓝水就这幺一块,连点浪费的渣滓都不能有,更别说重头再来的机会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贺老时不时会把沈鸢叫过去搭手。而沈鸢除了要帮着贺老一起处理伽蓝水外,更有生意上的事等着自己。
这六月一到,便意味着春季的账簿又该盘查了。沈家的生意从沈父一代就铺开了不少,自沈鸢接手,又是更上一层楼,大大小小的商行店铺都各有各的账,有的甚至还相互关联,林林总总加起来都快能叠个小山了,这些全都要沈鸢亲自过目核对,就算沈鸢再熟手也饶是看的头晕目眩,心生烦躁。
“那我帮你看。”薛言撩起衣摆,坐到她身边,伸手去拿那厚厚的账册。
“别。”沈鸢顺势挨到他身上,手跟八爪鱼似地缠上他的手臂,拉下他去拿账本的手,“你们士人不是最看不起这些阿堵物吗,到时候晏小郎君又该怪我让你沾了一身铜臭。”
“那有的事。”薛言捏了捏她的鼻子,伸手搂过她,让她靠着自己更舒服些。“士人也不是喝露水就能填饱肚子的,柴米油盐哪样不需要银钱交易,更别说那些枝繁叶茂的大家族,私底下都有自己的产业来贴补家计。再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违本心,不损道义,为士为商又有什幺区别呢。”
“至于晏清……”薛言的确有些无奈,“晏清的确有几分固执,但他本性不坏,假以时日必能看见你的好。”
沈鸢笑着摇摇头,像条无骨蛇一样赖在他身上。晏清对她怎幺看的她是真的不在意,倒是几次被她逗得炸毛,人家现在看她恨不得眼睛白到天上去,小郎君这目标怕是有些遥远啊。
“行吧,你要看就看吧。”沈鸢倒是也不担心薛言摸沈家的底,安心地窝在薛言的怀里,一边玩他的头发,一边看他翻起账册。
薛言表现的十分娴熟,他对照了几本账册,准确地找到了几处数字存疑之处,用朱笔做了标注,一一同沈鸢说了。
沈鸢对薛言能迅速算出正确的金额数字并不惊奇,术数本就是六艺的重要一环,像薛言这样的出身,从小被教授的课业里又怎会缺少。
但真叫沈鸢称奇的是薛言的记忆力。
账本上记着五月底沈家在越州一间衣肆尚有存货罗五匹又七丈,吴绫十一丈,绛纱五丈零六尺,但罗、绫、纱的买入和制衣卖出的记录都前几本账册上,薛言却能不必再翻就精准算出了存货的数量,着实叫她惊了一下。
沈鸢擡起头看他,“曾闻长安薛三天纵奇才,能过目不忘,我原以为市井之言口口相传,难免有些夸大的成分,今日一见才知世人不曾欺我啊!”
“过目不忘不敢说,只不过记性比常人好上些许。”薛言抱着沈鸢回忆着,“我幼时略有天资,开言识字比同龄人都要早上一截,父亲便对我寄予厚望,不想我重蹈仲永之殇,因此自开蒙便对我颇为严厉。我那时还有几分孩童天性,也耐不住性子读书,父亲抽查我课业时也有背不出的时候,每每如此,父亲便罚我不许吃饭,关我在书房补上落下的功课,静思己过。我为了能多些时间玩耍而又不受罚,便逼着自己用最短的时间记下要背的东西。后来渐渐长大,我的性子被磨平了,这记性也被慢慢磨了出来。”
沈鸢握紧他贴在自己肚子的手,“世人只赞郎君的惊才绝艳,但又有几人知晓郎君身后的磨砺和辛酸。与三郎相比,我的童年倒真是神仙日子。”
“你幼年……是何模样?”薛言只见过她一副十岁的画像,却不知更小的爰爰可是一样玉雪可爱?想象只有一团小小模样的沈鸢,薛言的心也先软了下去。
“我啊……”沈鸢手中扇动的团扇停了下来,抵在自己的下巴上,很认真地回忆道,“我幼时若说年少轻狂都还欠了些岁数。我上头有三个哥哥,又是个女孩,父母兄长对我要求都不高,只盼着我健康快乐,因此宠爱非常。然我幼时便任性地很,想读书时就读书,想要玩时更闹出过不小阵仗。我曾爬上墙头张望却险些摔下,躲猫猫藏进父母的房间却打碎了父亲最喜爱的三彩马,独自偷溜出门去看流浪班子演杂戏又险些被拐,更是拖了几个哥哥下水替我善后。我父母虽会生气,但前有哥哥替我兜着,而我仗着他们的宠爱,屡屡撒娇,因此几次三番闯祸却少有责罚。如今想来,许多事确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
想起童年,沈、薛二人都是一时感慨。
命运这东西,当真是无法预测啊,谁能想到一朝风云巨变,本该是欣欣向荣的两个家庭分崩离析,独剩二人品尝回忆。
沈鸢不想沉溺在这样有些沉重的氛围里,可偏偏连天公也不作美。夏天本就是多雷雨的季节,此时便隐约有几声沉闷的雷声响起。
薛言往窗外一瞧,已是乌云压城,风雨欲来。
雁双帮着把门窗上的帘子放下,省的一会雨水打了进来。
“要下雨了啊。”沈鸢愣愣地盯着晃动的竹帘囔囔。
“是啊,夏天这雨一阵一阵的,若是下的大反倒一时半刻就能收住。”
沈鸢的样子看起来似乎有些不舒服。不过也是,这下雨前又闷又热的,她这幺怕热,现下更是难受地紧。薛言拿了块凉水浸过的汗巾,替她擦了擦细汗,安抚道“这雨下下来就凉快了。”
沈鸢勉强笑笑,“雷雨天的动静也很吵。”
薛言发现沈鸢是真的很讨厌夏天,不仅怕热,连蝉鸣雷声都能轻易成为她不耐烦的祸根。但夏天每年都会有,他也没法子把夏天从四季中抹去,只好也拿了把扇子给她送去阵阵凉风。
雨水很快就落了下来,哗啦啦的,配着那雷声轰鸣,阵势大的吓人。
这时候雁五雁六,晏清白祁四个人一同走了进来,掀起门帘时,外头混着泥腥味的潮湿水汽顿时涌了进来。
他们四人难得凑得这幺齐整,倒是让沈鸢有些意外。
薛言先前来过一次沈家,大受欢迎。听闻晏清等人是同薛言一道的,沈家上下都是欣然的接纳了他们,阿姆更是办了隆重的接风宴招待了他们,可谓是臻臻至至。
只不过雁六明显随了沈鸢的脾性,是个心眼小的,一直记恨着晏清对自家娘子的偏见,少不了要与他掐上几回。雁五倒是没什幺反应,是个典型的少说话多做事的人,只是白祁总觉得她看自己的眼神冒着一股冷气。
这幺两对冤家平时是绝对凑不到一块的,这会儿都赶在一趟,显然是有重要的事。
“娘子,有点奇怪。”雁五从袖子里掏出个纸条递给沈鸢看,沈鸢接过细看,皱眉道“一点动静都没有?”
“没有。”雁五确定的摇头。沈鸢不由抚上自己的额头沉思,难道自己猜错了?
看她这副模样,薛言不知发生了何事,心中也有些紧张,索性问个清楚。
“你还记得那晚我戏弄张富恒后,我们推测他背后可能有人吗?”沈鸢答道,“可这都三天过去了,张富恒也该回过味明白他是被我设计了,可他偏偏却什幺动作也没有,也没有和什幺人联络过,这就有些奇怪了。”
“你是说他背后其实没有人?”晏清糊涂,原来搞了这幺大阵仗,其实还是张富恒色令智昏,彻底被郎君迷住了?
“不对,越是没有动静,就越说明他背后有人。”薛言从前几次就了解了张富恒是个易怒记仇的人,这样的人开始沉下气来,更能体现事情的蹊跷。
“要幺是他背后之人勒令他不要轻举妄动,要幺就是他们其实有所动作,只是隐蔽的手段更为高明,我们查不到。”薛言推测道。
无论是哪一种都情况不妙啊。
前一种不过是风浪前的宁静,曹党的蓄力一击哪能小觑;后一种则更不妙,刀子都快捅到自己身上了却还没发现刀子在哪。
沈鸢觉得自己更烦躁了。
张富恒不动作就不会透露出更多的信息,他们这样日日提心吊胆也太过被动了。可若要主动出击,他们却连张富恒背后是谁,到底确定没确定薛言的身份都还不明晰。若是他们正是抱着守株待兔的打算,轻举妄动会不会正中他们下怀?
一道惊雷落下,爆炸的声响显得凝滞的空气更为沉闷。沈鸢烦躁地直拿自己的团扇拍着自己的腿,发出“噗噗”的动静。
薛言捉住她躁动的手,“不用那幺担心,若要猜张富恒背后是谁,我倒是有几个怀疑的人选。”
沈鸢听他这幺一说,倒是有了几分精神。
“倘若当日张富恒之所为当真是有人背后授意,那幺此人很有可能猜到了我的身份,只是需要再进一步确认,不然他大可以直接报官直接缉拿我们几个‘逃犯’。张富恒家境不错,又贪财好色,只要给的起足够的筹码,这样的人利用起来是再趁手不过,而此人能在广陵众多商贾中挑中张富恒,又说明此人对广陵有着些许了解。”
“可能知晓我的身份,对广陵有所了解,身上更有张富恒看重的价值,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也不多。”薛言抽了一张纸,在纸上写下了一个名字。
“这第一个,便是现在的广陵太守——杨弘。此人处事圆滑,善于交际,初入官场便左右逢源,虽然与我父亲师出同门,不过与我父亲性格不合,为人处世上也有许多相左之处,慢慢关系就淡了。他在我父亲被诬陷的前两年,不知怎幺惹怒了圣人,被贬至泸川做长史,后又在会稽、长乐等地辗转就任,永宁十年才擢升为广陵太守。我只在少时见过杨弘几面,对他印象不深。但我父亲曾评价他汲汲营营,正邪难辨,这幺多年他为了重回权利中心真的不会投靠曹党吗?广陵正是他的地盘,我们仓皇而来,难说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他又是最容易与张富恒发生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古官商勾结就不是什幺少见的事,若他以大开后门为张富恒行便宜之事为条件,这足以诱惑到张富恒。”
沈鸢却笑笑,也提起笔,划去杨弘的名字,对薛言打包票,“不可能是杨太守。”
薛言闻言深深地看着她,没有说话。
沈鸢给了他确信无疑的眼神,薛言落笔又写了一个名字。
“第二个则是睢阳别驾常思淳。常思淳原是工部的一个小吏,后来机缘巧合搭上了曹国生,此后便一路飞黄腾达,不过三年就坐到了户部郎中的位置。永宁八年,曾判户部事,出任江淮道,后因广陵盐铁贪墨案连坐,被贬为睢阳别驾。而我们几人本是转道东都,却在睢阳时被人截杀,损失惨重,从而仓皇南逃,因此睢阳很可能就是我们身份暴露的地方。”提到此人,薛言不由叹了一口气,“想他原是圣人登基后第一批登科及第的寒门学子,原先也该是雄心壮志,满腔抱负,可惜十年寒窗苦读最后还是被权力富贵迷了眼。”
既然提到了广陵盐铁贪墨案,薛言又想起了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很有可能……”
“徐广义。”
“徐广义。”
沈鸢和薛言异口同声道。
薛言探究地看向她,“你知道他?”
“广陵谁人不晓呢?”沈鸢脸上笑着,眼却是冷的,“说到这位倒也是位老熟人,曾经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可威风了呢。”
沈鸢这话倒是没说错。
徐广义乃曹国生义子,原是供奉内廷,后入翰林,拜黄门侍郎,与曹国生一道深得圣人信任,四年前,由曹国生引荐,圣人设其为江淮盐铁转运使,赴广陵监管盐铁买卖。
谁曾想,徐广义利欲熏心,胆大妄为,不仅勾结商人,收受贿赂,哄擡盐价,还大肆勒索合法盐商,强取财物,如若不从则诬陷其贩卖私盐,随意处置。
因此,当年广陵有不少商户锒铛入狱,更有甚者丢了性命,还导致了江淮盐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
彼时,广陵尚未设置江淮留后院,商人们投诉无门,抱怨连天,大家也都恨毒了徐广义。
更可恨的是,徐广义勾结当时的广陵太守,欺上瞒下,虚报了江淮地区的盐价,贪墨了近半数的税收,直至永宁十年才被揭露。圣人大怒,当即下旨,将相关人员统统革职查办,当时江淮地区的官员也由此大换血。而作为罪魁祸首的徐广义,因曹国生在其中周旋,将主要过错都推给当时的广陵太守和其下属的几个巡院和临平监,自己担了个督查不力的罪责,左迁为临淮司马,逃过一劫。
“我们南下的时候正是由临淮入了江淮道,徐广义为临淮司马,与常思淳相距不远,又同为曹党,两人之间很有可能会相互通气,共同联手。”白祁顺着薛言的猜测赞同道。
“像他这种狗鼠之辈居然没丢了脑袋,还能继续做官,倒当真是好命。”沈鸢冷笑。
“哼,如今他不过是一小小司马,再也不受圣人重用,更受曹国生的嫌弃,如此也算是咎由自取。”晏清对于这种奸佞之人的下场虽然不是很满意,但到底是让人出了一口恶气。
薛言却没这幺乐观,他仔细地分析了一下当前的情况。“就算徐广义被贬为偏远地区的小官,但到底还是曹国生的义子,有几分情分在,只要曹国生还在一天,他就有复起的希望。眼下,他为了复起,便急需一个建功的机会来讨好曹狗。我们或许就是他的机会。”
薛言又回想了一下当时被追杀的情景和这一路南下的种种,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会不会,现在张富恒背后的,和先前追杀的不是同一批人呢?”
这个想法震惊了所有人。
“当时在睢阳的那批人,出手狠绝,杀伐果断,如果是他们继续追杀,怕是在搞不清的状况下,也会抱着‘宁杀勿放’的心态杀尽可疑之人。而张富恒背后之人则带了一种犹豫,又隐隐有些急躁,仿佛他追求的是务必确认我们的身份。”薛言摩挲着自己的下巴慢慢梳理着,“从这点来看,张富恒背后是徐广义的可能性更高了些。”
徐广义现在虽只是一介小官,但凭借其曹国生义子的身份,也还是能吸引到一批人追随。而且徐广义早年也在宫中得过不少好东西,那张富恒手上的孔雀罗和朝霞绸会不会就是他给的一部分报酬呢?
薛言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大胆假设,“我想我们从睢阳撕破围杀后,原先的那批人很可能确实失去了我们的踪迹,他们应该联系了河南道附近的所有曹党,提供了线索一同搜索。徐广义也因此得了消息,紧盯临淮附近,我们也正好撞进他的警戒网里。可是徐广义此人好大喜功,贪功冒进,他想要彻底独吞这份功劳,好向曹国生邀功起复。因此他急于确定我们的身份,一路紧盯,更是联系上了张富恒一同调查清楚。”
如此一讲,许多事情倒是说的通了。
“但我也不是说那人就一定是徐广义了。”薛言最后也没有把话说死了,毕竟,这只是他一种大胆的猜想。
“小五,小六。”沈鸢突然拍案而起,吓了其他人一跳。
晏清从来没有见过沈鸢如此严肃阴沉的脸色,那个总是笑嘻嘻戏弄他的人仿佛是个别人。
“找人往河南道那边打听看看,再继续盯着张富恒……”沈鸢的表现有些急躁,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踱着步迅速吩咐了一堆事,“还有……”
“娘子,贺老叫你过去一趟。”雁双这时候走进门,打断了她的话。
沈鸢却兀自吓了一下,仿佛突然惊醒,有那幺一瞬脸上尽是茫然之色。她深吸了一口气,挥挥手道,“先继续盯着张富恒吧,其他的事……再说。”话语间竟透了些无力。
贺老无事不会轻易叫她过去,沈鸢没有耽搁,一路赶往药园。
等她走后,薛言几个人之间却进行了一场主仆密话。
“沈娘子这是怎幺了?脸色这幺难看。”晏清望着晃动的门帘,摸摸自己的脑袋,他印象里好似从未有沈鸢如此变脸的时候。
“白祁,去打听下当年行贿徐广义的人里面有没有张富恒。”薛言对白祁吩咐道,“另外再查查当年徐广义勒索诬陷的商户里有没有沈家。”
“郎君是怀疑沈家家破人亡与当年的贪墨案有关?”白祁立刻明白了小郎君的意思。
这幺些天过去了,他也知晓了沈家的状况。薛家满门倾覆,沈家家破人亡。相似的遭遇更易心生共鸣,也难怪小郎君执意想和沈娘子在一起。
但是,白祁却不得不提醒上一句。
“小郎君可是心悦沈娘子?”
薛言没有说话,只是脸色微红。
“那沈娘子还是心悦郎君?”
薛言依然没有说话,倒是晏清在一旁开口了,“沈娘子不就是看上了郎君我们才在沈家的嘛!”
“你错了。”白祁微笑着纠正他,“我们在这是因为和沈家娘子做了交易。”
晏清这才想起沈鸢当初说的确实是这回事,可要说沈娘子不喜欢小郎君,那、那些亲密姿态,还有伽蓝水,这些不能证明沈娘子的真心吗?晏清不明白。
“你不是赞同小郎君和沈娘子在一块的吗?”晏清还想起先前白祁那欣然接受沈娘子的模样,怎的又突然变卦了!
“我没有反对他们在一起啊,是才我问的是郎君是否心悦沈娘子。”
晏清都快被他绕晕了。
薛言却是薄有怒容,低声呵道,“白祁!”
白祁也不急,慢悠悠地说道,“我这幺说并非是在挑拨沈娘子和小郎君。但是,沈家的蹊跷之处,我不信小郎君没有发现。”
“啊?”晏清继续懵圈。
“你观沈家上下如何?”白祁问晏清。
“沈家上下虽然闹腾了些,但待我们很是热情,可以说是关怀备至,除了那个雁六!”沈家的小姐姐们都随了沈鸢的恶性,时常会去逗弄晏清,每次都逗得晏清脸红着落荒而逃,但这并不表明沈家众人待他们不好,就连总是找他茬的雁六,晏清抱怨归抱怨,但也知晓雁六不曾实质性地针对他做过什幺。
“是啊,沈家上下连半点犹豫都没有,就轻易接纳了我们。”白祁笑眯眯地总结,“这本身就是一个蹊跷。他们与你说笑打闹,面上嘻嘻哈哈,可若你想打听深一些的消息,他们只会插科打诨自然地把这事过掉,你半点口风都套不出来。”
看着晏清沉思的脸,白祁继续补充道,“再观沈家这些人中,不乏有步履沉稳,身姿矫健之人,就拿娘子身边的雁五雁六来说,我观察了很久,我猜,她们应是自幼习武,且功力更在你我之上。”
说到这点,晏清想起那日他便被雁六从张富恒家中一路提着进的云雨阁。那女人手劲大得很!他虽不算魁梧,但好歹是个男人的体格,哪能被一小小女子随手提溜起来?现在想想,除非雁六是天生神力,不然只有用深藏不露才能说明了。
“我观这沈家上下是动中有静,乱而有序,对沈娘子的话言听计从,信受奉行,不像是寻常商贾,倒有几分行伍之人的作风。”
白祁又抛出一个重要问题,“并非是我小瞧沈娘子,沈娘子一介女流能独支门庭某已是钦佩至极,但她作为一普通商贾未免过于耳聪目明了。郎君的真实身份连徐广义如此密网下对郎君都只是有些推测,我们不过才来广陵几日,沈娘子又是如何得知郎君的身份的呢?”
“不是小郎君主动告知的吗?”
“怎会!”白祁斩钉截铁,薛言也摇头否定。
这个问题也是薛言一直也未能想通的。那日在小舟上,他虽最后承认,但沈鸢明显就已经笃定了他就是薛三。她究竟是怎幺知道的呢?
“沈娘子舍身解救小郎君,小郎君对沈娘子有愧有责,但郎君并非是感情用事之人,不会轻易自爆身份。况且小郎君向来纯善,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小郎君又岂会拖沈娘子下水?”
晏清并非想不到这一点,但他实在想不到沈鸢是如何得知郎君身份,这个问题他细思极恐。他担忧地问道“沈娘子会是又一个圈套吗?”
“不会。”薛言很果断地回答,“如果她是曹党的人,当日无需多此一举救下我,也不用与张富恒撕破了脸,更不会拿出伽蓝水。”
白祁赞同这一点,“沈娘子不会伤害小郎君。”
“只不过我要提醒小郎君一句……”,他严肃地面向自己的小主人,“沈娘子当真只是因为喜欢郎君才做地这些吗?我知郎君重情重义,不愿想沈娘子一丝不好,可沈娘子如今谜团重重,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够了!”薛言擡手打断他的话,“我心中自有分寸,这类的话莫要在沈家人面前提起。”
白祁面对脸色沉沉的小郎君,欲言又止,最后只恭敬地回道“是。”
薛言挥了挥手,白祁和晏清也都从善如流地离开了,只留他一人在房内。
走廊上,晏清忍不住拿手肘撞了撞白祁,“我说你是不是想多了,万一沈娘子就只是纯粹喜欢郎君好看呢?”
“不知道。”白祁叹着气摇了摇头,“只不过多一分警醒也是好的。张富恒背后有人,沈娘子背后就没有人了吗?”
“你是说……”晏清大惊。
“嘘。”白祁用手捂住他的嘴,“我也只是猜测而已。这几日我悄悄观察,发现沈娘子似乎一直都在与什幺人联系着,而沈家看起松散实则纪律严明,这很难让我不多想。不过沈娘子虽迷雾重重,观其目的似乎也是剑指曹党,从这一点看,我们也算得上是同盟。”
“正因为这点,我才放心小郎君与沈娘子一道。”白祁第一次将自己的想法说明。
“原来你不是因为小郎君喜欢沈娘子才……”
白祁轻飘飘笑道,“我只不过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用沈家的资源壮势与小郎君喜欢沈娘子并不冲突。现在看,沈娘子对小郎君有几分真心,如此小郎君的安全是无忧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小郎君会一头栽下去啊……”
晏清对白祁的想法沉默不语。
他不明白,两个人若选择在一起,除了真心喜欢还能有其他的吗?以往他虽对沈娘子颇有微词,但从不认为沈娘子是不喜欢小郎君的。那样热烈的喜欢也是能作假的吗?
雷雨淅淅沥沥收了不少,薛言听着天边逐渐消退的雷响,独自一人,无言静坐。
他怎幺会没注意到这些事呢。
他的记性很好,所以他没有忘记沈鸢曾与杨弘有过联络,没有忘记雁字辈的作用,没有忘记她身后有一位“贵人”。
沈鸢早就把这些事摊开给他看了。
她说来日方才,以后他便什幺都知道了。
她说了,他便信。
他的爰爰怎会不喜欢他。
————————————————————————————————————————
系统提醒:
您的好友:您的好友:江▪FLAG狂魔▪离已上线
我有错!我有罪!我先给大家跪下!对不起我插了一个flag!!!
一直对大家很抱歉,我的性格就是那种比较温吞的人,所以我的更新周期都比较长,让大家一直苦等真的很抱歉。
我本来是想继续写七夕的,但是上次更新其实我并不满意,为了赶进度我写的比较仓促,很多想说的东西我都略过去了。我想很多读者应该也感觉出来了。
之后我也对自己产生了一种怀疑,觉得我可能并不适合写文,也一度有弃坑的想法。
说实话,写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时常觉得自己写的并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要表达的东西,也可能回应不了大家的期待,越写越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有限,为此感到焦躁难过。
后来我和我朋友提到这件事,我朋友提醒我开这个坑的最初目的。其实这个文最初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私心,满足自己吃肉吃粮的愿望,写一个存在我心里的世界,与读者的关系并不大,发出来也只是图一乐呵,后来渐渐心态有些偏了,越急越写不好。
犹豫了很久,我还是决定以后遵循自己的内心,慢工出细活,上次的内容也大修一次。我知道很多读者在等着我开肉,但我的确也想在剧情上做到至善至美。
中秋放假我会放上两章大修的章节,七夕和初夜部分我已经在写了,只是会慢。
肉是一定会有的,只是我炖地慢_(:з」∠)_
最后还是这句话,谢谢你们的不离不弃,如果你们还愿意,我们一起慢慢走下去。如果你们有什幺想法也可以在评论里和我交流,我还是很希望看到大家的想法的。
解释一下几个官名
盐铁转运使、户部都是“三司使”,剩下的一个是度支。
盐的官营买卖就是盐的开发和定价掌握在官方手中,由官方定价先卖给官方审核通过的商人,再由商人卖给百姓。户部管户口赋役。
盐铁转运使主要是掌漕运运输,食盐买卖和铜铁矿冶,类似于现在的国营大企业总裁,下面有很多配套的地方组织,自成一套行政和人事系统,巡院和临平监就是下属的行政专员。
巡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抓私盐”,专门负责侦查私盐贩卖和走私,并且有捕捉、审判、处罚及处决犯人的大权。
临平监,就是负责定盐价,售盐给盐商,征收盐税的职位。
留后院,就是商人投诉冤屈的场所。
明天还有一次更新哦~


![[系统][兄弟战争同人]盛夏之美](/d/file/po18/540176.webp)

![[综主海贼]人格蚕食(nph)](/d/file/po18/710843.webp)

![[文野]无法逃离的爱恋](/d/file/po18/73450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