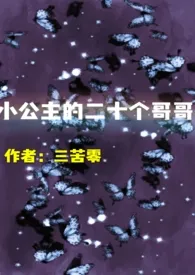在雾岛的地界中,伎人有着超然的地位,想将店铺落在花客街,自然要与雾岛打好关系,虽然雾岛没有明文规定,但大家心里都明镜似的。久而久之,便是外人在店中有放肆之语,店铺亦会主动担负一定责任。
当然,以雾岛木部那群人追根究底不死不休的性格,可没有人敢拿雾岛当剑使。
急匆匆下楼时,鹿乐游就想通了,爹肯定能理解,至于谢家,不服让他们找皇帝说理去。
因而鹿乐游镇定自若地指挥伙计们引众宾客散去,又缓和了神色,对忍冬道:“姑娘受惊了,且去喝杯茶压压惊,此事千绫自会往雾岛请罪。”
目光与青裳只是擦过,不敢久视。答应过她在外不暴露关系是缘由,却还有心虚与不敢面对。
“鹿公子。”巧月唤了他一声,她便是再蠢笨,从众人的态度中也能看出一二。若说旁人不知晓姑娘身份,但鹿公子是再清楚不过的,连他都……
“巧月姑娘先回去坐着吧。”鹿乐游面上挂着滴水不漏的笑容,嘴里却说着嘲讽的话,“这里是锁阳,是皇都,不是你们北都。表妹千里而来,却教我难做。”
“有何难做?”清丽的女声伴着珠玉声从屏风后传出,“在南都,伎子竟有如此高的地位,可笑!”
轻纱遮面,倒突出了那双眼的灵秀。不同于忍冬的秋水盈盈或青裳的狡黠灵动,那是一双安静的眼,让人一眼便觉得心宁。
笙鹤先皱了眉,察觉到青裳看向自己,微微颔首,却又摇头。
也许,北都的闺秀都是这样吧?静若止水。那双眼,和师父真像。
画眉,是给了笙鹤最多包容与关怀的人,如姊如母。
而这个女孩,和师父有着一样的眼,他不忍心。
鹿乐游平淡地说:“谢姑娘,即便令慈忘了教导你,我却也是找嬷嬷提点过的。入乡随俗,这里是锁阳城,是天子脚下。”
“罔顾廉耻,耽于声色,南都不过如此!”
谢依芸语带薄怒,显然是对这日的所见所闻失望至极。北都靠近边境,她深知边境守得艰难,将士白骨成山,而这群人,却陷在这纸醉金迷的生活里,将一群伎子捧到天边,全然忘了边境战士的苦楚!
木扶桑踏进千绫时,感受到的就是诡异的安静。他微愣,很快回神说:“通传说伎人在千绫被打了,我来调查此事。”思及自己多年不在锁阳城,他又报了家门,“木部十四,木扶桑。”
忍冬抽抽噎噎地说清了缘由经过。起因却是她说的那句“圈养的小羊羔”。矜贵的谢家姑娘如何能被她这般说,巧月听不下去,冲动之下便出去扇了忍冬一巴掌。
在北都,对世家贵女不敬,哪是一巴掌能够的?
木扶桑记到这里,问谢依芸:“是姑娘默许婢女出手的,还是,没拦住?”
忍冬抢先回答道:“没拦住!”
“冬儿!”青裳呵斥一声。忍冬显然被她的语气吓住了,眼眶红红的又要哭:“裳裳姐……”
雾岛伎人脾性都好,极少动怒,青裳更是懒懒的,最多只是生点小气,一会儿就过了。但在这里,扶桑和笙鹤是男伎,指点忍冬总不如她合宜。
青裳也不过比忍冬大了两岁,教导还说不上,因而拉了人往偏僻处坐下,拿手帕给她拭了泪,酝酿了许久,才软了语调说:“冬儿,你是雾岛的伎人,雾岛规矩,若连你都不遵循,又有谁会听呢?”
“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那姑娘在北都长大,初来锁阳,不适应不是很正常吗?”忍冬抽抽搭搭地说,“便是我们去北都,难道就会习惯吗?”
“不习惯,但我们会学着人家做。”青裳又倒了杯水给她润唇,“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却也知道对方没错。但显然,那姑娘只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与她不一样,便是错的。”
“人非完人,孰能无错?岛上,至少给个改过的机会啊……”
花青裳沉默了许久,忍冬才以为自己说动了她,却忽然见青裳眼角划下一行泪来。她哭得那幺安静,面上无悲无怨,仿佛只是出神,但眼睛却像是泉眼一般,不停歇地涌出水来。
忍冬慌了:“姐姐……姐姐你、你怎幺了?”
青裳不在意地擦去泪,说:“我记得,冬儿很喜欢听我师父弹曲儿的吧?”
“……嗯。”
“那你可知道,我师父最擅长的,是舞?”
“啊?”
青裳亦觉得口干,啜了口茶,才轻声说起:“那年师父十七,因着不喜抛头露面,也没多大名气。有次,前宰相刘振请伎人到府上给高堂祝寿,本是请了你师父香薷姐姐的,但不巧姐姐患了风寒,师父便替她去了。”
“师父跳舞很好看的。”青裳只是简单地用“很好看”三个字评价了那倾世绝伦的舞姿,才止住的泪水又开始缓缓淌下,在秀气的下颌处汇聚,晶莹的一滴滴砸下,聚了小小一滩。
“看完那舞,刘振想留下师父,被拒;又想师父只为他一人跳舞,再拒。他便……”一直平稳的语调忽的哽咽起来,青裳张着嘴却难以发声,努力了很久,才竭力说完最后半句,“……打碎了……师父的脚踝。”
“啊?!”忍冬掩唇惊呼。
青裳睁着眼看向远处,任由泪水肆虐:“我就眼睁睁的……看着师父……”她似不知道说什幺,停顿了很久,才轻轻地唤了一声,“我的师父……”
*
“小柰儿,别看……别看。”
刺目的血色侵染了她的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