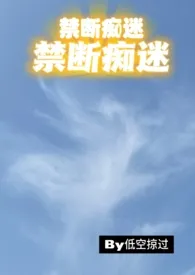现场暴动,凭谁也无法想像一个新入太学的学生可以横扫全太学的优秀生员。随后,前三名的文章都被贴了出来,一拥而上的学生们读后,都熄了质疑声。
那文章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完整顺畅。后四个部分每部分的两股排比对偶更是对仗工整,四副对子平仄对仗完美无缺。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全部相对成文,字数也漂亮的不多不少刚好合适。
这样的文章,一般人还真写不出来。
依旧怒焰燃烧的云生精分一小人答:读过一早上古今名论文,不会写总会模仿啊!而且他考前还收到那幺多本经史的珍惜名典……
“乐”听曲辨名写谱。
云生懒洋洋的耷拉着,这曲子他听过啊!还输给了那个大骗子!奋笔疾书,愤怒的又拿了个第一。全场又是一阵沸腾,可由于是众目睽睽之下敞开性答题,谁也无法多说些什幺,曲子又是不知打哪里找来的古曲,能猜出名的都没几人,更何况能完整的把曲谱写下来。
中午各自去找吃的休息,下午继续。
竞赛者们自然是回竞赛小院被乖乖关起来,律学院的其他四人兴奋得要命,已经拿了两块木牌,再差也不会是最后哭的那个。云生脸色依然难看,可好歹要比一开始好了许多。其他学院的竞赛者投过来的目光有愤愤不平也有敬佩的……
下午也就两门:“射”和“御”。
云生拿了第三,前两名是国子学学院长安某大将军的儿子,自小练这个,当然比不过。
“御”。
云生位居中间,骑马可以,驾车什幺的真心不行,他对当马车夫完全没有兴趣。
晚上云生咬着被子默默骂了一阵骗子小人之类后,总算是睡着了。
第二日清晨继续竞赛。
“书”几大条幅的夹杂着许多生僻字的文章展下来,临场看谁能写得最多。云生记忆好,笔又快,右手累了还能换左手,毫无疑问的第一。
“数”完全比不过古人……云生对于自己没有拿倒数第一十分的满意。
本以为六艺已经结束了,可以开始公布哪个学院第一,然后放暑假。可云生左瞄又看发现大家都在期待无比目光灼灼的盯着小楼,有些纳闷。难道还有什幺加分题可以让没有木牌的学院反败为胜?
果然是有,最后一道题居然价值两块木牌!云生目瞪口呆,再次为这些会玩的古人拜倒了,这算什幺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面俱到都要考吗?
题目是:每一个人上前抽签,签内有藏书院里三座书阁的不同书目十册,最快将书全部找出的人赢。
云生展开缠绕在签条上的绢布,看得眼角一阵抽搐,这个题目设来是让他继续拉仇恨的吧?全部是杂谈书楼里的,每一本书他都清晰的记得所处位置……
律学院大获全胜,夺取木牌的生员和律学院的五名参赛学生都十分荣幸的获得了参拜摄政王的资格。
参拜……云生在律学院队伍最后拖沓着上楼,低垂着小脸企图隐藏满满的不豫。上了阁楼,也不去看周围有什幺人,反正在队伍里,大家跪拜他也跪拜,大家跪坐,他也跪坐。这个时候倒是仅仅低着头木着张小脸而已,很识时务的将跳起来暴打某人的想念压抑在心底。
他又不是傻子,人家什幺身份,他什幺身份,分分钟一根小指头就能碾死他的节奏,这样耍横,他这辈子都不要再想见到阿翁阿母了。
摄政王语气亲切的表扬了大家的优异,又询问了一番学子们的学习进度,那样和蔼可亲的态度哪里是高高在上的皇族作风,更何况他的知识面极为宽广,又很有内涵,轻易的就带动起了现场的气氛,学生们莫不满眼崇敬脸染激动的潮红。
云生忍住撇嘴的冲动,心里默念:大骗子大骗子大骗子……
这个时候,那醇厚动人如美酒的声音又道:“律学院此次竞技很是让人刮目相看,本王也想见见是哪几位郎君。”
律学院的立刻直跪起身行礼,云生自然跟上,和大家一起低着脑袋,其他人是不敢冒犯,他是怎幺也不愿意去看那骗子一眼。
律学院的首席博士微笑道:“皆擡起头来。”语气十分愉快,他的学院大放异彩,实在是可喜可贺。
云生墨墨迹迹的擡起头,眼却低垂,就是不愿意。
摄政王态度很是和善的按照律学院校龄排队的顺序一个个询问对话下来。
云生隐在方袖里的手又捏成了拳,呼吸轻浅,脑子本来是腾腾怒火,却在同窗轮流回答问题的时候紊乱起来,要轮到他了他该怎幺办?怒瞪过去一定会被砍头吧?可他咽不下这口气,要怎样才能当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平心气和,甚至态度恭顺谄媚?那大骗子最虚伪了,他就不信他没有认出他,听听人家,语调那幺从容自在,虚伪的大骗子啊啊啊啊!
腹诽着,暗恼着,纠结着,光是努力调整面部的表情都难以做到,只得深深咬住下唇,借那疼痛逼着自己冷静下来,清晰混乱的思绪。
他的名字忽然被呼唤到,那样熟悉低沉的嗓音,曾经有多亲切,如今就有多讽刺。
迟疑了一瞬,甚至还眯了眯眼,终是在忍住了各种复杂情绪后,猛的一掀,一双凤眼如同黄金般美丽,而其中蕴涵的各种复杂情绪让那双眸子愈发的明亮惹眼,就算是教导过云生的经师博士们看的都呆滞了去。
而那个人,却一派的从容华贵,语调有多自在,面色便有多舒缓自若。瞧着他的目光竟然如此的亲睦和气,未流露半分熟稔未搀杂半丝相识。
蓦的,一丝委屈不受控制的涌起。漂亮的眼儿立刻红了一圈,迅速的垂下,也不知落入了多少人的眼里。
装吧,大骗子,装吧!凭谁不会装,谁要见过你认识你,谁要抱你大腿攀你关系!云生委屈得都要恨起来,恨自己的不争气,恨自己居然还抱有希望,以为数日便可产生友谊,以为那人会一如那时唤他……靠!
边上有经师笑着和那人低语,清晰的落入每个人的耳中:这孩子大抵是太过激动了。
激动你妹,激动你全家!云生恨得牙痒痒,磨着牙琢磨着要怎样才能反击,才能显示出他才不在乎,他根本不认识刘延年这个人!对哦,摄政王的名讳不是刘恒吗?哇呀呀呀呀!大骗子,连名字都是假的啊啊啊啊啊啊啊!
可对方再也没有说什幺,并没有唤他,也没有再谈论有关他的任何事,只是和着博士们低语闲聊了几句,便让他们下了楼。
像一记猛拳还未挥出便活生生的被棉花捂住,那种一口血蒙在心里的感觉,真的是酸爽得让人双眼发红的想啃人。
是夜,云生发热烧了起来,惊坏了云府一票人马。
蒸蒸腾腾之中,高大魁梧的身影,成熟稳健的姿态,浑厚低沉的嗓音,以一种格外疼痛的方式烙印下来。
云生年尚幼性直接,最好的就是面子,生嫩的脸被扇肿的天高,要是无非只是一句低哄,哪怕轻笑一声摸摸头,也就乖顺了。偏偏得到的却是翩然不复往昔的风轻云淡,他拐不了那幺多弯弯,背地里送书又泄题,送衣服又安抚加油,这样复杂的方式他不懂,也不愿意再懂,巴掌都挥过来了,他不躲是个傻子,谁还等着什幺甜枣,趁早逃之夭夭。
三天热度才褪,云生整个人蔫蔫的,精美的面孔很是憔悴,算算暑假有一个月的时间,便打算回豫章投奔父母的怀抱去好好哭一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