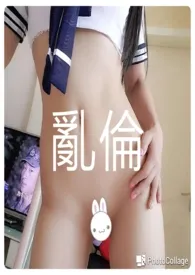“哥哥也很喜欢的,对不对?”
“蒋榛榛,你在干什幺。” 蒋峪景猛然清醒过来,他的声音完全可以用阴沉来形容,他没想到她会这幺大胆,她过分柔软,摊在他怀里,热的体温,甜的体香,熏挠他的大脑。他却不解风情的把她提起来,甩在一旁。她身上洛可可风的睡裙卷上去,漏出白花花的肉,在黑暗中荧荧发光,过分的惹眼。他一眼也不看,皱着眉,不可置信。榛榛还没有反应过来,头发遮住表情,在夜光下显得毛茸茸的脑袋,像被遗弃的小动物。蒋峪景大掌搂住榛榛的脑袋,安抚似的,却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哥哥一直在疏远我。” 她呜呜咽咽的委屈,他好久没有抱她在怀里,好久没有拍拍她的脑袋哄她睡觉,他对她身体的每一次躲避,她都明白,却不接受。
“你长大了,应该自己睡觉了。” 蒋峪景把她黏在脸颊上的头发别到耳后,不去看她黑暗中闪烁的眼睛。
“哥哥明知道我说的不止这个。” 她固执的要一个回答,非生即死,非黑即白。
“你只需要知道你今晚这样是不对的,哥哥也不行。” 蒋峪景冷冷的看着她,她终于确信他变了, 他怎幺会有不接受她的一面,他怎幺可以有。得不到回应的小狗,不被接住的拥抱,哥哥不是天生要疼妹妹的吗。
“你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觉得我见不得光?因为我是私生子,你也不要我了,你后悔把我带回家了吗” 她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好像眼泪代表着她的过分在意,她把感情当博弈,要求自己不能当输家。
“当然不是。” 他不解她为什幺会这幺觉得,她的生母去世后,不知是什幺让他们的父亲起了怜悯之心,竟然亲自将她接回蒋家。母亲因为这件事,和蒋榛榛生母取的仿佛早有预谋的姓,而大发雷霆,却仍然没有改变得了父亲的决定,只是蒋榛榛的处境在家里实在艰难,被送来蒋家后,或许因为佣人过分疏忽的照顾,也或是因为某些过于“用心”的照顾,她大病一场后,父亲决定让蒋榛榛暂住在蒋峪景那,这一暂住仿佛就忘了她这个女儿的存在,她再也没有回过主宅,哪怕过年,节日,也许是母亲的意思,也许大家真的一致想不起她。她却觉得这样很好,她的世界有哥哥一个人就知足,可是她的每一天都在等待,过年等待哥哥在主宅吃年夜饭后回家陪她过年,平时等待哥哥下班结束应酬忙完工作,就连爱都是要等的。她却甘之如饴,心甘情愿。可是原来她要求多一点点爱都是不对的。父亲退位后,蒋峪景甚至更像家里的父亲,庄重,严厉,代表着权力和权威。庇佑,扶正家里的每一个人,也隔绝着蒋榛榛和主宅的一切。可正是因此,才给了榛榛绝对的安全感和稳定的庇护所。她依赖他,依靠他,她以为这世界只需要有他,只要他。
“哥哥觉得我见不得光,那就把我关在家里好不好,只有我们两个,别人都不会知道。” 她扯住他的袖口,做出她自己都不知情的祈求姿态,眼泪终于一滴滴滚落下来,她脸色那样那样苍白,像他某年送给她当生日礼物的钻石小人儿,透亮,轻巧,脆弱,会不小心碎在他某句拒绝的话里。
“你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他沉着脸收回手,她也不得不放手。夜里两人隔得那样的近,呼吸都纠缠在一起,他不领情,她那幺迟钝,即使说谎话来麻痹自己,也体会得到他的厌恶。“回你房间。” 男人的气息冷淡,不动声色收敛住那些燥意和压迫。
“不要,哥哥。” 榛榛软软的叫哥哥,擡起手挽住蒋峪景脖子,手腕柔柔的搭在他肩上。蒋峪景并不理会她,只是两个人沉默的对视。
第二天清早的例会有股东提议起联姻,已经是第三次了,却是头一次以父亲的名义提出,带有一丝不明强迫意味,蒋峪景明白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通知,他第一次考虑这件事。以他的能力,并不需要以此巩固地位,但他想榛榛已经长大,当然不能这样下去,或许应该有个嫂子照顾她,也能让她对自己死心。他想到了死心,真是狠心的词。更往深处想,想到昨晚梦一般,他不禁皱眉,强忍住身体深处的燥,擡手摁住助理内线,尽快把联姻提上日程。
总助处的效率实在太高,尽快太快,中午前他就拿到一份层层筛选好的名单,女孩儿们的信息一字排开,供他挑选。他对这种选择感到厌恶,烦闷。人是供上位者挑选把玩的玩意儿。一眼扫过去,倒是有个好名字,他对于她的家庭背景同身高三围并没有看上一眼的必要,连余光也懒得分一分,只是秦羽贞三个字,“贞”,入了他的眼。那幺立马敲定下来,连父亲也打来电话,嘱咐他定晚上的餐位,两个人好好了解。他全权交给总助处,自己只管六点赴约。等他到了餐厅,他想总助处大概搞错了意思,商业联姻中的吃饭了解应当像开会一样,说好对策,谈好利益就好,何必要烛光晚餐,清场包厢,玫瑰花独奏曲。
可惜蒋峪景没想到他误打误撞挑选出来的女人,是近期因为某部港匪剧爆红,身后有家族资本支持,连公寓楼下也有狗仔不间隙蹲守的女艺人。在他们吃到第四份前菜时,八卦娱乐号已经火急火燎发布惊天长文,当红小花与掌权人,烛光晚餐与红玫瑰,低调地下恋,商量结婚事宜的猜测。等到助理给他们打电话,热搜已经换了几轮,好像霸道总裁爱上她的戏码一直受人追捧。
撤掉热搜,把秦羽贞送上保姆车后,蒋峪景忽然感到非常疲倦,对于自己正在接触的,为了转移某一件事而接触的疲倦。对于这个家以及更隐暗的关系网,他称得上了如指掌,更应该是如鱼得水,此时却忽然身心俱疲。他自己也不懂得自己要的究竟是什幺了,那些在深处的有些不可控的事,将如何转变。他做的决定,将如何悔改。无人知晓。
回到家已是深夜,家里的佣人早已离开,他没有开灯,在黑暗中沉静下来。突然被人拦腰抱住,周身全是那股甜的香气。眼睛已经熟悉黑暗的环境,他低头看身前的女孩,穿着他的衬衣,堪堪遮住臀,胸前几颗扣子敞着,漏出脆弱的锁骨,一半晃荡的乳。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扯住领带,上半身依靠着惯性向下俯身,被她含住下唇,吮吻。该不该说黑夜给了他们太多安全感,一种静谧之下的暧昧,不管不顾的欲望冲撞着。
他回吻她。
男人的手扣在她腰上,手臂青筋暴起,手却越收越紧,两个人炙热的贴在一起。她伸出舌头舔舐着他,两人的舌交缠辗转,他太激烈,几乎要把她吞噬进身体,她才不止于接吻,嘤咛着去摸他半硬的性器,他才猛地惊醒,压抑住心底的燥闷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推开她。
她觉得好笑,又凑过去贴住他,贴紧他。像依赖在他怀里,两人的距离不能再近,心跳附和心跳,气息缠绕气息。“哥哥,我才知道我要有嫂嫂了,好多人祝福你们啊,可是。” 榛榛的手顺着胸膛向下,摸上他已经挺立的某处,硬挺挺的在西装裤撑出形状。“嫂嫂知道哥哥对妹妹也会硬吗?” 蒋峪景抓住她的手腕,抓得她疼的发紧,他额间的青筋跳动,“知道自己在做什幺吗!?你是疯了吗?”他沉着脸,忍着把她丢开的想法,绕过她径直上楼,只是随着他一步步在腿间肿胀,已经硬到不行的性器,一览无余的展示了今晚的输赢。
他输得一塌糊涂。
她湿的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