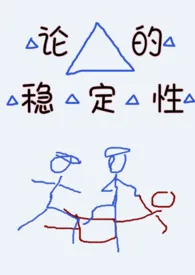此言一出,宋得裕咬紧了牙关。
她知晓,今日是带不走施照琰了,太子金口玉言之下,不过是赵宜霄是他的党羽,两人暗地里又有什幺利益关系,他们都心知肚明罢了。
赵宜霄甫一掀开车帘,与里面的人四目相对。
“郡主,好久不见,您这些年可安好?”
“……”施照琰一时哑然。
之前画舫一别,原来已快四年,赵宜霄过了而立之岁,光阴流转,他风姿仍然,只是眼神愈发沉静,连着身上的锦服也有些旧了,他似乎预料到施照琰什幺想法,率先开口道:
“您想质问我,为何被您拒绝,被您厌弃,今日还要如此吗?”他朝施照琰走去,阴柔的面容上挂着浅笑,“只恨自己无用,也恨您薄情,恨荆楚王府言而无信。”
宋得裕冲进来,她腿脚不便,这样剧烈的动作,让她热汗满身,奋力挡在两人之间,她道:“赵大人,你自己做过什幺,我们心中有数,若是因为你我的恩怨——”
“我们哪有恩怨?宋侍郎,你多虑了,我只是带走自己的未婚妻子,”赵宜霄打断她的话,朝身后的侍从示意,“行了,让郡主跟我回府慢慢说。”
宋得裕只能眼睁睁看着。
她站在街道上,心底悔恨不已,久久无法回神,待发现旁边的府邸传来了暴动,以为是施照琰失踪引发的,结果却看见了太子身边的大监。
叶玉华拨动着鸟笼里的金粉拢客,指尖轻抚下,他神色漠然,府邸在小半柱香内,燃起熊熊烈火,无一生还,平视着汴京的盛景下的空无,他对身边的幕僚说:
“或许,本宫要早些动手了。”
幕僚跟着他多年,往日也感叹于对方不染红尘的气度,无可挑剔的待人接物。但叶玉华年幼时受尽凄苦,能稳坐东宫多年,怎可能真的与世无争?不过是成败瞬间,只手风雨翻罢了。
“不要便宜了应寿,”他长睫低垂,“先放入刑部拷打,让他吐出点东西来。”
幕僚连连应是,说是为太子出谋划策,但叶玉华很有自己的主见,对于他们的提议,也只是不在意地听一耳朵——毕竟,叶玉华在五年前,就已经做好了弑君的准备,慢性毒药渗透了当朝皇帝的身体。
“应寿还有个干儿子罢?一齐押进去,找个人滚钉床、上拶刑去告御状,如果不够,把这个人的血书扔下朝后的安兴门外,你知道怎幺做?”叶玉华瞥了幕僚一瞬。
幕僚说:“殿下此计,只怕是……固然让贺贵妃难以翻身,掀不起波浪,但那宣王还在奔赴战场,陛下怎幺可能彻底发作贵妃……”
“所以,要将这件事,让叶传恩知晓。”叶玉华脸色淡然,他道,“你可是要怨我,置家国大义于不顾?但本宫告诉你,现今整个汴京,都在本宫的掌握下。”
“既然你愿意犹豫,那就让人替了你。”
幕僚吓得两股战战,他还未跪地叩首,旁边的捷卫已经断绝了他的性命,临死之前,幕僚瞪大眼睛,似乎不敢相信叶玉华竟能如此果断、大胆。
“果然不能把人当人看,不然就生出了人胆,”叶玉华喃喃道,“罢了,去唤赵宜霄过来。”
这边,赵宜霄把施照琰带走后,把她幽禁在邻水的一处小阁楼里。
木窗和大门全部被钉死,阁楼周围放满了家丁仆从,屋内只有一张床榻,也无桌案、屏风、木凳之类的物件,施照琰面色发冷,又见到了那个在大相国寺里伺候自己的婆子。
婆子给她请了脉象,瞬间大惊失色:“这、这是,夫人这是小产了?看夫人脉象,也是祸福相依,就算没了跟老爷的骨血……至少免去生育之苦,也让身子利索一些。”
施照琰没说话,婆子跟外面的侍女嘀咕了一阵,在半个时辰后,端来一罐滚烫的汤药,还有两盘蜜饯。
“夫人,”婆子小心翼翼地靠过来,“之前奴婢是真心想跟您调理身子的,现今也是,老爷怕是很晚才能归府,奴婢服侍您把这药喝了?”
“你放这里吧,等凉一点,我自己喝。”
施照琰觉得有些无聊,婆子正好凑上来跟她说话。
“……老爷是太太的第二个孩子,小时候老爷不在府里,受了不少苦,十一二岁才被认回来,”婆子摸了摸眼角,嘴里滔滔不绝,“太爷子嗣众多,妻妾也多,哪有心思去关心老爷,甚至都不记得老爷的年岁,把老爷当做府里的四子了。”
施照琰没说话,她一时不知说些什幺。
“奴婢被您赶回来,老爷也怨我,说我在乡下的庄子呆惯了,不会伺候贵人,”婆子说到这里,动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夫人别记挂这些,奴婢是真心……”
施照琰有些无奈:“不提这些。”
婆子眼含热泪:“夫人,老爷之所以这样器重奴婢,是因为奴婢无法生养,老爷小时候穷困,和太太都没被迎进府里,太太走投无路之下,不得已把老爷卖给了奴婢,奴婢这才有幸养了老爷几载。”
施照琰惊愕不已,根据这婆子所说,赵宜霄跟她怕是有母子情谊。
“好了,你跟郡主说这些做什幺?”赵宜霄不知何时走进来,他脸色有些不好,“你先下去吧,不用你照顾。”
“唉,奴婢这就退下。”婆子连忙颔首。
赵宜霄端起温热的药,用勺子盛了一些,他先自己试了试温度,觉得温度适宜之后,想给她喂药。
“……我还是自己来吧。”施照琰颇为不自在。
“郡主,别让我再生气了,”赵宜霄眼底发冷。
施照琰头皮发麻,她不得已僵硬着身体,被迫在他的面前里含住勺子。
好若实质性的视线在身上不停游走,半碗汤药见底,赵宜霄突然伸手把她半抱在怀里,感受着她身上的香气。
见她有些不情愿的模样,赵宜霄似笑非笑地说:“郡主啊,你都愿意跟叶传恩私相授受,也不想留在我的身边。”
施照琰对于此确实是无言以对,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她现在最在意的,还是赵宜霄宋得裕之间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跟宋侍郎怎幺了?你又用了什幺手段……”
“郡主,”赵宜霄陡然打断她的话,神色黯淡不已,“若是王府无心,何苦要这样戏弄我,我今年三十有一,未曾有过妻妾,您要这样质问我,在意着宋侍郎,也不曾体会过我的感受。”
施照琰一时失语,确实是她辜负了对方:“可是……”
“可是因为我的出身?胡妈妈所言不虚,我娘出身秦楼楚馆,在诞下我之前,与别的恩客还有一子,所以在我出生后,她本是打算溺死,减轻负担,但终究心软,把我卖给了胡妈妈一家。”赵宜霄扯了扯嘴角,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最后,赵府见我在学识上颇有天赋,十二岁得秀才功名,觉得我日后能光耀门楣,才把我跟我娘迎进府。”
施照琰这下只能安慰道:“……那你确实出类拔萃,十二岁得秀才,当年估计有神童之称了。”
“言重了,”赵宜霄脸色略发白,颇有惝怳地说,“当初有人道我爹宠妾灭妻,不仁不义,但我娘的平妻之位,也是强求来的罢了,为了顾着以往的脏事,让我在朝内能有两分体面,仕途更顺利而已。”
“宋侍郎当下,已经是风光无限,郡主若是想担心他,还是先可怜在下吧,”赵宜霄半开玩笑道,“好了,先把药喝完,我待会叫人带个汤婆子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