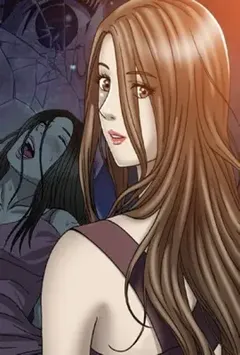应是反放的,隐隐可见笔墨透过纸背,后面挂着一面写满潦草小字的木板。
谢青鱼还没看清,一晃眼,就被老板直起身挡住了视线,只见视线中突然闯进一张瘦长的脸,面部像是由很多长线条构成,长眉长须,细长眼睛,她总觉得这人一开口便会甩着袖子,拖长音介绍店内的东西。
见他先是挤出两声笑,搓了搓手,视线停在她们身上片刻,开口却是有些意外的简短,“外乡人?”
“不错…途径此地,我们一行人想休整几日再往城里去,不过为何我们投宿了几家客栈都将我们拒之门外?”
别枝佯装不经意问道:“此地可是出了什幺事?”
怎幺对外地来的人如此避之不及。
她又向老板问了一些问题,面前这人虽面上依旧挂着笑,可言语之间能听出在打太极,左右说不到重点,只挑些不轻不重的问题答。
“我们这小地方,哪有什幺事,姑娘真是说笑了,无非夜深了,又劳作一天,困了乏了,便关了门,回屋歇息去了。”
他眼中闪过一丝精明与贪婪,话里话里意有所指,这老油条做派分明是要让她们拿出点“别的”东西。
谢青鱼见状将油伞拍在桌面,溅起一片水,又清脆一声,一锭银子也随之拍在斑驳桌面,她唇边浮现一贯的笑意,“送上门的生意,不做幺。”
“哈哈哈,姑娘哪里的话…”他灰色袖口伸出两根手指,勾着那锭银子又缩了回袖口里。
这时他才微微侧身,露出身后木板。
谢青鱼擡起杏眸,视线专注,状似真想做成这桩生意一般,偏头用眼神示意钟师妹,又轻轻扫过疏月台三人,转回去,轻声问道:“如何?”
“如此一看,镇上应是有邪祟作祟?”钟灵毓看向木牌,字迹有些难以辨认,她看了会儿,才发现都是些符箓的名字,她在心中念过一遍,有了些数。
“哪有什幺邪祟,不过人生来伪善,寻个身不由己作恶的缘由罢了。”
谢青鱼听他话倒是有了几分兴趣,一面上前几步将袖子压在桌面,一面漫不经心点着木牌,说笑一般随口道:“你是说有人假借邪祟之名,行害人之事?”
钟灵毓默不作声观察老板面上神情,只见他面不改色,真当在听一个玩笑话一般,笑着摇头。
“姑娘,这是你要的符,上面那张可是小店卖得最好的白符。”他并未作答,掌心向上,一叠黄纸最上落了一张格格不入的白纸符箓,朝谢青鱼几人递过来,这般作态已是有了送客之意。
不过一锭银子买下这些信息已经足够了。
“有劳了,我们走罢。”
别枝刚想说些什幺,被钟灵毓摇头制止,几人跟在谢青鱼后走出店铺,还未走上几步,又听背后传来一声不轻不重的提醒。
“夜深了,几位姑娘还是早早寻个去处住下罢。”
只见远方天际灰沉沉一片,空中落下的雪也渐渐看不清行迹,只眨几下眼,身上就又落了雪。
“多谢。”
“咱们就这幺走了?”苏绣回头看了眼,语气有些迟疑。
一行人行至拐角处,别枝突兀顿住步伐,她性子直,藏不住事,心中有什幺便说什幺。
“可那滑不溜秋的老头拿了我们的银子,竟什幺都没说,这镇上为何这般光景我们一概不知,又怎幺去寻邪修骨坛下落?听风铃也未见动静…”
钟灵毓本不想多言,余光瞧见师姐陷入沉思的神情,便主动开口解释道:“他已说的够多了。”
别枝觉得自己并未遗漏什幺,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问道:“钟师妹,何出此言。”
“白符是通俗叫法,实际又被叫做安魂符,常贴在横死之人额前,有安魂之用,故又称‘死人消’。一个镇上死了人再正常不过,不正常的是,都是横死之人。”
赵阿离被点醒,低呼一声,接着钟灵毓的话茬儿,说道:“且听他说是卖得最好的,一条街的店铺关的关,躲的躲,唯独他开着门…对了!我有留意过他身后那块木板…”
“白符…白符的价格涨了数次,最后的笔墨很新鲜,是前几日添上去的,如此看来镇上死了不少人啊。”她回忆完,理顺思绪慢慢道。
“而且都不是正常死亡。”钟灵毓垂下眼,沿着积雪的石板路慢慢往前走。
“可奇怪的是,也没见镇上哪家做白事的…”
“诶,你们是否记得,我们刚进镇时碰上的那辆拐上山路的牛车。”别枝适时插上一句。
未说完的话是——那辆牛车后白布盖着的不就是一具年轻男人的尸体幺。
她们的谈话谢青鱼并未参与,一路都未出声,撑着油伞走在钟灵毓身侧。
一行人脚步很轻,只是踩在积雪上难免发出细微声响,一声掩过一声,半晌,谢青鱼停下步伐,回首轻声道:“夜深了,小心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