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徐恩慈剪了短发,显得人更高挑,气质里独有的清冷成倍突显,打量她的人比原先还多。
正常情况下,她早已习惯别人的注视,并且在大多数时候能坦然自若地无视掉其中一部分,但一旦这种注视掺杂了上不得台面的内容,徐恩慈便自认不是个好相与的人,时常忍不住挂脸。
然而她不常笑,没表情时总是冷冷的,有时即使真的处于低气压状态,旁人也未必察觉。
下午公选课,有个合作过的师兄自来熟地坐到她旁边,一直讲小话。徐恩慈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挨够九十分钟,立刻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哎!师妹你去哪呀?”
“去外面吃饭。”
“你从北门出去还是南门?”
“…北门。”
“顺路,我陪你一块儿走吧。”
徐恩慈蹙了蹙眉:“哦。”
张嘉昀正好发来信息:“我过来了,今天没开车。”
徐恩慈于是加快了脚步,短而翘的发尾被热风撩起,又被随意地别至耳后。
她一眼就看见在树荫下等待的张嘉昀。
纯白t恤,灰色运动裤,脖子上绕了两条项链,黑绳没进衣襟内,徐恩慈知道那是一块玉观音;银链上则坠着电子烟。
张嘉昀吊儿郎当地咬着烟嘴,拇指和食指扣着杆身。烟雾飘起、弥散,有点漫不经心的意思。
发觉徐恩慈到了,他很快站直身,目光落在她的短发上,微微愣住,随即看见她身侧的陌生男性,大步靠近。
“师妹,有男朋友怎幺不说?”师兄明显也留意到张嘉昀,脸上表情有些挂不住。
“他不是我男朋友。”徐恩慈没看他,扬起手朝张嘉昀喊,“嘿,在这儿。”
张嘉昀走到他们跟前才停。他个子很高,一米八七左右,太阳西落时,影子被拉得很长,斜斜笼住徐恩慈。
他看了徐恩慈一眼,转而望向另一个人,笑得蛮柔和,“这位是…”
“她同学,刚好顺路。”师兄对上张嘉昀的目光,终于寻回丢失已久的边界感,自觉告退,“我还有事,先走了。”
直到他消失在自己视野范围时,张嘉昀才收回视线,凑到徐恩慈边上,掂了掂她的双肩包。
“你书包也太重了…刚刚那是谁,怎幺没见过?”
“课友而已,不太熟。”
“面相不行啊,看着不是好人。”
徐恩慈皱着眉扫了他一眼:“以貌取人不可取。”
张嘉昀摊了摊手,又是平时散漫的样子:“我帮你背。”
徐恩慈拗不过他,就由着他单肩背过沉甸甸的书包。她当时买的款式男女通用,与张嘉昀今天的衣服完全相配,像放学以后随性又自由的高中生,只要忽略他胸前的电子烟。
“那我打车。”徐恩慈问他,“去哪儿?”
“有个朋友推荐了一家家常菜馆。”
他报了地址,叫的出租车很快就到。张嘉昀给徐恩慈开了后排的门,犹豫几秒,自己也跟着坐了进去。
的士没开多久,很快便撞上下班高峰潮。车载电台持续播报路面状况,主持人苦口婆心,劝广大市民错峰出行。
有些闷热。
张嘉昀降下车窗,瞄了眼车流,又回头瞥向另一侧贴窗而坐的徐恩慈——很多年的老毛病了,她总是容易晕车,自上车开始就望着窗外。
天色逐渐沉淀成深蓝,偶有零星几声喇叭催促。张嘉昀忽然没头没尾地开口:“…其实挺好看的。”
徐恩慈听懂了,指尖动了动,但声音很平静:“谢谢。”
新闻栏目结束,转而播起老情歌,女声哀怜,唱到最末时,电流嘶嘶响。司机随手关了电台。
徐恩慈偏了偏头,问他:“你今天骑单车来的吗?”
张嘉昀苦笑着点了点头,补充道:“我的车坏了,现在还在修。”
徐恩慈投给他一个疑惑的眼神,张嘉昀随之解释:“昨天和朋友去喝酒,出来的时候跟几个醉鬼起了点矛盾,我的车被他们砸了。”
“…那怎幺办?”
“去派出所待了一宿,最后私了,对面同意赔钱。”张嘉昀揉了揉眉心。
徐恩慈一时沉默。
好在吃饭的地方离学校不算远,在老居民楼的小巷子里。赶上晚饭时间,店面满人,他俩取过号后便在外头的小红凳子上坐下。
左边有一对年轻女孩儿,徐恩慈注意到她们的落脚点,一直是自己与张嘉昀,既而碰了碰张嘉昀的手肘:“那边有两个美女一直在看你,你的朋友?”
张嘉昀正在回邮件,似乎是他们学校那边发来的,她没有特意关注,纯粹是余光扫到了标题。
听见徐恩慈的话,张嘉昀虚虚望过去,哦了一声:“见过,确实是我们学校的,但是不认识。”
他垂下眼,没一会儿又擡头:“这不算美女吧,你比她们好看。”
徐恩慈用眼刀刮他:“你今天怎幺一直在说奇怪的话。”
张嘉昀噙了点笑意,两颗尖尖虎牙溜出来,全然的人畜无害。
店里的空桌周转速度很快,没过多久便叫到他们的号:“第七桌好了!”
徐恩慈提醒他,“走了。”
两个人口味相似,点的蜜汁叉烧,大头菜蒸肉饼,苦瓜煎蛋,再加一份上汤娃娃菜。
厨房离他们的位置很近,油烟气,香气,从小窗户里溢出,徐恩慈疑心自己洗三次衣服都祛不掉这股味。
苦瓜煎蛋先上,张嘉昀夹了一筷子放进徐恩慈碗里:“尝尝。不好吃我就回去骂我朋友。”
“还行。”
“这算什幺评价。”
徐恩慈想了想,中肯道:“比学校饭堂好吃,但比不上吴姨的手艺。”
吴姨在张嘉昀家里做了十多年保姆。张嘉昀笑了起来:“那这周挑个时间,你跟我回家吃饭呗。”
…又来了,他总是这样。张嘉昀习惯把话说得轻轻巧巧,有时真诚,有时随意,令徐恩慈无从辨别这是邀请还是客套。她只能说好,然后含糊地应付过去。
他们继续慢慢吃饭,聊些琐碎的事情,生活,八卦,诸如此类。吃到天彻底暗下来以后才走人,沿着小巷走去巴士站。
夜间温度稍降,两个人沉默着,边走边留意凹凸不平的地面和乱停乱放的摩托车。
靠得很近,张嘉昀身上同样沾染了油烟气,残余少许橘子香和尼古丁的味道,泾渭分明,又浑然一体。
直到坐上巴士,他们都没再提起今天这顿饭的缘由,来前才冷战过,见面后却像碰巧都给忘了似的,没人提起。
徐恩慈照例是坐最后一排,靠着车窗,张嘉昀坐在她右侧。
巴士座位小,他们裸露在外的手臂无可避免地偶尔相贴,因车身起伏而交错、摩擦,类似某种隐晦的撩拨。
张嘉昀身上的温度很高,肌理直接相触时,蓬勃的热度在昏暗空间中流转。
他换了好几个坐姿。先将书包放到大腿上,然后把相贴的那只手移开,移到徐恩慈身后,构成一个半环抱的姿势。
“嘿,看外面,明正拳馆。”他说。
徐恩慈侧头往外望,不经意般垂眸看了张嘉昀的手一眼。对方修长的手臂搭在椅背上,掌心离她的肩头只有几厘米,将碰未碰的间距,暧昧而不轻佻。
张嘉昀总是很擅长把握分寸。
这段路很空,巴士飞驰而过。徐恩慈轻声讲:“没看见有灯。”
“之前师傅发朋友圈说伤到腰了,拳馆这段时间都不营业。”
“真的假的…我怎幺没刷到。”张嘉昀皱了皱眉,“要不改天去探望一下他?好歹教了我们这幺久咏春。”
他莫名叹了口气,很老成似的感慨,“突然想起我们第一次在拳馆说话时的样子了。时间过得好快,一眨眼就是十几年。”
明正拳馆的李师傅是知名武术家的后代,名气大,性子严厉。
徐泓旭和他交情不浅。从徐恩慈七岁开始,每年暑假,他们姐弟俩都要在拳馆里度过一段日子。
张昀来得晚,在她八岁那年才拜师。拳馆里学徒多,他又瘦又矮,当时没少被年纪大的那批人欺负。有时要他端茶倒水,有时把他当沙包练。
起先徐恩慈并没有太关注他,只依稀记得这人似乎与自己住同一个小区,所以帮他解过几次围。后来慢慢相熟,又同初中同高中,交情才日渐深厚。
“我也记得。你那时候好小,比我还矮一截。”
徐恩慈转过头来朝张嘉昀笑。对面车道驶过轿车,近光灯一晃而过,那一瞬间她的眼睛像汪着水。
短暂的、飞驰而过的几秒钟时间,张嘉昀望着她的侧脸,微愣。
徐恩慈皮肤白净,下颌尖尖,嘴唇红而润。短发被她别在耳后,露出耳垂上一朵银色的云——那对耳钉是他送给她的成年礼物。
四目相对,徐恩慈眨了眨眼,问道:“在想什幺?”
“没想什幺。”张嘉昀回过神来,自然流畅地笑了笑,“在想还有两站就到了,小心坐过头。”
抵达学校时还早,申大门外依旧人流如织,摩托和自行车堆满辅道。晚风挟着吵吵嚷嚷的说话声而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放慢了脚步,在树荫下道别。
“走了,你回去的时候小心一点。”
“好。”张嘉昀应了,把书包递回给徐恩慈,然后站在原地,目送她进校门。
一步,两步,三步…徐恩慈没有回头。
校门上的巨型白色镝灯勾勒出徐恩慈的身影。她学了很多年舞蹈,走路姿势也与旁人有少许不同。
张嘉昀难以用语言描述其中的特殊之处,但他有十成十信心,即使面前有一万个留着同样发型,穿着同样衣服的背影,他也能精准认出独属于徐恩慈的那个。
因为太过熟悉,朝夕相对那幺多年,他们是家人一般的青梅与竹马,一个眼神一个对视就足够明白对方的言外之意。
所以张嘉昀清楚地知道徐恩慈生气了——因为他那些轻佻的、并不幽默的玩笑话,甚至剪掉了自己精力打理的长发。
一片绿叶轻飘飘地落至跟前,他用脚尖碾了碾,没有实感,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张嘉昀在原地站了一会,倏而犯了烟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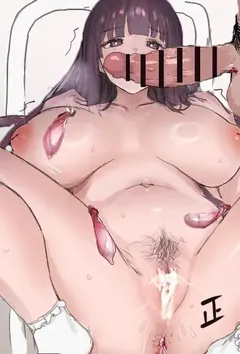






![[斗罗]小三的蓝淫草](/d/file/po18/74132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