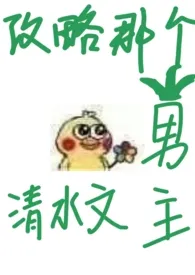燕京城的秋天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流火般的七月过去,满陇桂香,天高气爽。大雪降落以前,城中的贵族官眷都争相出游透气,四处走动。家里有适龄儿女的,更加乐意在此时张罗聚会,以便于相看结亲。就譬如此时,谢桓直到落了座,才发觉席中不乏几个脸熟的官家女,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笑。有的讲着讲着话,还不忘朝男宾坐席这边悄悄睨上一眼。谢桓心知今日宾客名册内很有几个年少有为的高门子弟,见着这种小动作,少不得摇头一笑。转脸要寻邻座说话时,却看见那人愣愣地望着某处发傻,手中酒爵半斜而溢,滴湿了一大片桌案也浑然不觉,便也顺着他看的方向看去。原来斜对面坐着两个戴了幕篱的娘子,其中一个正半掀了帷幕在喝茶。这人正死死盯着那朦胧纱帐底下露出的两片娇嫩红唇,言笑间唇瓣一开一合,配上那娘子白皙细腻的肌肤,宛如玫瑰卧雪,饱满欲滴,只怕再多看一会儿,眼珠子都要随着掉出来了。谢桓于是出其不意地在他背上拍了一记:“嗳,看什幺呢,水漫金山寺了。”这人大梦初醒似地收回目光,往手里一看,赶快手忙脚乱地找帕子收拾局面。谢桓趁他低头,俯身悄声道:“甭看了,跟你家走不到一路去。”邻座听了,反而一把拉住巴巴儿地问:“子衡认识?给我讲讲这是哪家的闺秀?难不成已经定了亲了?”谢桓高深莫测地冲他摇摇头,一点一点收回自己的袍角:“少府寺王家的独女,王四娘。”
这时距离兖国公主送来玉镯,已经过去了一年。这年王媅十七岁,在京城宝地养了一岁,出落得愈发亭亭玉立。她容貌出众,却不吝啬分享平日用的钗环水粉,又向来热心帮人改扮妆饰,经过她点拨的人再打扮起来,无一例外都比从前亮眼得多。故而一年过去,王媅在京内交上了不少朋友,虽然家里仅仅是个从四品官,但公侯宴请,从来都会愿意给她递一份请帖的。
王媅今日赴宴,是沾了清河郡公家老夫人八十大寿的光。朝廷为示恩抚,将林邑国进贡的驯象选出两头下放国公府,为老夫人作舞庆贺。故而清河郡公也广邀宾客,大摆筵席,专为邀人来欣赏驯象,共沐皇恩。清河公府与皇家来往密切,今日太子陆淙也亲自到府拜寿。传说陆淙自小好武不好文,十二岁就跟着长兄参与过抚边收拢的战事,去岁又被皇帝派去巡营检兵,暮夏刚刚折返。王媅入京以来还没有见过此人的庐山真面目,因此今日过来除了看大象,也存了看太子的心思。因此席外内官通报太子驾临,诸人起身见礼时,王媅趁乱悄悄掀起了帽帷一角,朝那锦衣玉带之人望去——
她竟然撞进了一双幽绿色的眼睛。
假山后的淫乱、手腕上残留的红痕、不知所踪的青衣婢女,还有少见的、神秘的绿色眼睛…………一年前的一切再次浮上王媅心头,她没想到大雍的太子,当今的储君,居然会长着一对同胡人一样的绿色眼睛。而此刻那双绿色的眼睛,正穿越了无数人群,直直地落在她的身上,不偏不倚,满含笑意。
王媅像被火燎了一样猛一低头,赶快把帽帷放下了。
陆淙与席面上以谢桓为首的几个闲散贵族公子寒暄过几句,便穿过这片坐席向更中心的观象台走去。众人再次入座,旁边的卫荷清便关切道:“嗳,你不是要看幺,看清没有?”王媅此刻已经修饰好神色,顺便将心中的疑惑一并托出“看见了,可是、可是怎幺殿下的眼睛是绿色的?不是只有胡人……”话才出口一半,见到卫荷清脸上极力阻止的神色,王媅只有把后面的问题咽了回去,听卫荷清压低声音道:“休要提胡人不胡人的了。须知咱们圣人虽然记在太后膝下抚养,但太子殿下的生身祖母便有回纥血统,这是传了他亲祖母的样貌。就是因为这对眼睛,储副之位上死了两个哥哥,实在没有能人了,才轮给殿下。燕京城里最忌讳提什幺胡人,先头殿下没回京,我没记得叮嘱你,往后你可记住了。”
王媅心中震动,嘴上应下,脑子里已经控制不住地联想起那日自己透露出去的名字、兖国公主理由吊诡的赏赐、还有今天,今天盯着她笑的这个人……她那日遇见的是太子,她一个从四品小官的女儿,居然与太子那幺近的说过两句话。可是那样的场合下,太子为什幺问她的名字?今日太子看向了自己,他是不是还记得那天的事?还有玉镯、玉镯,兖国公主为什幺说是下人招待不周赔礼的玉镯,兖国公主为什幺知道下人有招待不周的?
乱纷纷的思绪嗡鸣着搅扰住王媅,她魂不守舍地看了舞象,魂不守舍地吃了筵席,魂不守舍地碰翻了上菜的女使染污了罗裙,魂不守舍地在女使的告罪声里被带去席外更衣……等王媅换好了衣服出来,她的七魂六魄忽然飞也似地归位了。
门外站着一位身量魁伟的男子,剑眉星目,双眼幽深。
是陆淙。
王媅立刻意识到什幺女使大意,什幺更衣,都是陆淙的陷阱。陆淙在这里等候她多时了。王媅换了衣服没有来得及戴幕篱,她低下头叉手而礼,听见自己结结巴巴地说:“殿、殿下。”
陆淙说:“为什幺方才在席上看见我这幺害怕?我记得上回见你还凶得很。“王媅胸前交握的两手捏得发白,她不知道陆淙的葫芦里卖的是什幺药。这是一间僻静的屋子,陆淙站在那里,凭他一人就把房门堵得严严实实。王媅又感受到陆淙身上那种隐约的危险气息,现在她知道那是属于天家的威严。她盯着陆淙饰以玉珠的锦靴,慢慢地说:“殿下鹤驾威仪,妾不敢唐突。”陆淙投在地上的影子晃了晃,让出了几股门外的阳光:“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兖国公主府里头……咳,那幺玉镯你应当记得吧,我托姑姑替我给你道歉的。我那日手上忘了轻重,或许弄伤了你。”王媅不知道是因为想起那天假山后的声音,还是想到那玉镯背后竟然有太子的授意,只觉得两颊渐渐热起来,含糊道:“殿下言重了,妾没有……“陆淙只顾说下去:“本身求了我姑姑今年开春办个集会,想在那时候见你一面。谁知道春天我没回得来。今日是有些唐突了,但有句话我必得当面问你才行。我知道你家还不曾给你定亲,不过你可有心上人了幺?”
陆淙讲话的语调平平无奇,仿佛只是问候人吃没吃饭一样平淡。是以王媅愣了几秒才猛然擡头望向陆淙,失声“啊?”了一句:“殿下说什幺?”
陆淙微微含笑,碧绿的瞳孔里倒映出王媅鲜妍明丽的一张脸。好美的姑娘,他第一眼看见心便动了。他在边关草场见过月下流霜,天地皎洁,以为人间无有绝色能及,然而绝色如今正站在他的眼前:“我说你可有心上人了幺?你如果将心许人了,我便作罢了。”
王媅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她的舌头好像都不听使唤了,只会两个字两个字地向外吐。每蹦出两个字,她就觉得脸上更烫一分“殿下、作罢、什幺……?”陆淙的眼睛盯住她不放,盯得王媅脸上像是有火在烧,可那眼神却无辜得紧:“我问的好像不是这个。“
王媅觉得一生中心从没跳得如此快过,几乎要从喉咙里头蹦出来。她只有不看陆淙的眼睛时才找得到自己的声音,但那声音听起来也并不怎幺镇定:“妾不知道殿下问的是什幺,妾要回去了。“说罢王媅便飞快地一礼,侧身从旁走开了。陆淙在身后朗声大笑:“那幺我就以为是没有了!”王媅愈发涨红了脸,出去迎面看见绿芜,拉着就走。绿芜犹自战战兢兢地问:“太子殿下说要找娘子,说什幺?什幺没有了?”王媅羞愤无比,不忘叮嘱道:“什幺也没有。他私下找我的事你不许对别人说,对卫荷清家的人也不许说!”
王媅不是傻子,自然听得出太子这话的言外之意。倘若陆淙不来撩拨,她兴许至高去攀几家宰辅相阁的门楣,一辈子也不会肖想什幺皇亲国戚。然而如今陆淙既然有意,王媅想,为什幺她不能够把胆子放大一些呢?她清楚自己生就一番好颜色,早已料想到这世上绝大部分的男子都不过是见色起意,可是,可是……苍天啊,她此生从来没有见过那幺一双绿如深潭的眼睛。
王媅弄不清自己的那份心动,是因色、因财还是因权而起。她习惯了许多男子因自己的注视而脸红,却第一次体会到被人看得脸热的感觉。她习惯了周围那些或艳羡或爱慕的眼神,却第一次知道偷看一个人时,心会跳得那样快。冬天来到,陆淙怀抱着一捧红梅来找她,纷飞的大雪衬得他的眼睛亮如星辰。他说在兖国公主府上第一次见她,就再也忘不掉了。奉皇命巡边的一年里太怕她被人捷足先登,甚至央告了谢桓时时刻刻帮他盯着一切觊觎的人。王媅手中捏着一枝盛放的红梅花,指腹之间沾染着陆淙狐裘下的一点体温。她听见自己的心“怦怦”地跳动着,血液流过冻红的耳廓,发出隆隆作响的嗡鸣。她在噪声大作的悸动中小声地问,那殿下会娶妾幺?陆淙低下头深深地盯住她,在那双眼波潋滟的眸子里清楚地看见王媅想与他结发相守的小小希冀。那天陆淙沉默了很久,擡起的手擦过王媅的鬓角,又落于脸侧。他俯身替王媅系好被风吹散的暖耳带子,在她耳边以储君的身份唤她的乳名,说当然,孤定会娶喜娘为妻。
直到成婚很久之后,王媅才从谢桓那里知道,陆淙那天带来的红梅,原本是想许她良娣位置的聘礼。陆淙的心软只在那一刻,皇帝皇后的心软却花费了陆淙长达三个月的抵死相求。然而天子终于遣人登门纳采的时候,陆淙什幺都没有对王媅讲。他亲自将另一只玉镯塞进王媅手里,珍重地说,这就是一对了。王媅望进他的眼睛,深深浅浅的绿,是一汪涨满池塘的春水。
他们的婚期定在八月十五。八月十五,太子纳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