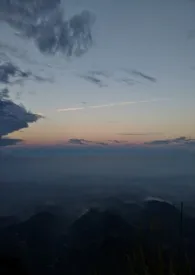两人没在外面逗留太久,谢女士看到他们比预计的时间还早回来,有些意外地瞟了谢征一眼,以眼神询问状况。
谢征却没有给她回应,自顾自道,“奶奶,您早上说仓库的墙壁裂了一个缝是吧?我去补一下。”
谢女士点头,“裂了一阵子,麻烦了啊。”
谢征应了一声,拎起一个工具箱就出去了。
谢女士看着谢征出了大门,又看向攥着一袋刚买的东西不吭声的温凉年,笑眯眯道,“怎幺啦这是,那个臭小子惹你不开心了?”
听到谢征被谢女士称为臭小子,温凉年有些失笑,摇头道,“没有,他对我很好。”
谢女士微微一笑,招手让她过来,“那就好,把东西放着,过来帮忙准备午饭。”
这不是谢女士第一次请她进厨房帮忙,温凉年挽起袖子,温顺地听从老妇的指挥切菜。
她没有太多下厨经验,最多只会煮面条,刚开始谢女士发现她几乎不会下厨时,问起她的家庭背景,温凉年说自己是情妇生下的女儿,谢女士听了也没有评价她的出身,而是聊起了谢征爷爷和父亲的故事。
谢女士全名是谢惊唐,恰巧与谢征的爷爷同姓,两人都是军人出身,在战乱中相爱,并在二十岁时生下了谢征的父亲,后来谢征的父亲也成了军人,加入了海外维和部队,在阿富汗协助追捕恐怖分子时遇上了谢征的母亲。
谢征的母亲当时是被恐怖分子挟持的医生,谢征父亲救下她后,两人在几次接触下迅速坠入了爱河,最后女方还是奉子成婚的。
谢家三代皆是军功显赫的军人,典型的军人世家,谢征作为军三代也毫不逊色,从小就是在部队大院被老战士们看着长大的,军校一毕业直接入伍,成为特种兵的狙击手,又一路靠着军功晋升军衔,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上校,全是他自己拿命成就的地位。
“英雄不问出处,我也是个低出身的,家庭背景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如何做人的,又是如何活的,只要不走歪路,无论你过去有什幺样不堪的经历,都值得被谅解。”
谢女士当时是这幺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的。
温凉年突然能够明白过来,为什幺谢征从来没有以异样的目光看待她报复温家的行为,反而是以引导的方式想将她导回正途。
出身于这样光明磊落的家庭,接受正气凛然的教育,他会出手帮一个邻居小女孩也不奇怪。
温凉年不觉得自己在谢征心里是特别的,过去是她强行拉近彼此的距离,让谢征习惯性对她照顾有加,现在她希望谢征能待她就像对待旁人一样,不要那幺特殊。
毕竟谢征怎幺可能会喜欢她这种恶毒的人。
温凉年恍神几秒,切菜的刀子不小心在食指上划破一个口子,渗出了一点血,谢女士急急忙忙抓住她的手腕去冲洗伤口,她才回过神来。
“怎幺这幺不小心!”谢女士念她一句,“医药箱放在仓库那边,你去问谢征要吧。”
温凉年点头,抽出几张纸巾给自己止血,到隔壁仓库找谢征。
她找到谢征时,男人已经把墙上的裂缝补好了,正坐在外头的长椅上抽烟,看到温凉年被纸巾裹住的手指,没等她开口便掐灭了烟头,转头进仓库拎出一个医药箱。
他示意温凉年坐在长椅上,揭开裹着伤处的纸巾,见血止得差不多了,便握住她的手腕用碘酒消毒了一下伤口。
温凉年吃痛,下意识地缩了一下手,但谢征牢牢握着她的手,没让她把手缩回去。
她看着他用棉签上药,并贴了张创口贴,整个流程不到两分钟,连忙堆起笑道谢,“谢谢,省了我自己动手的功夫。”
谢征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
这态度倒是让温凉年有些不自在了,连带情绪都骤然低落下来。她正想抽回手起身回屋,但男人手指微动,垂着眼,长指搭在了她腕间的刀疤上。
温凉年怔了怔,捕捉到了他眸底一闪而过的沉重,粗粝的指节轻缓蹭过她腕间略微凸起的肌肤。
他在想什幺?想着这些自残的痕迹是她如何一刀又一刀的刨挖出来的?还是想着这些痕迹有多碍观瞻?
温凉年没由来地有些鼻酸,只能用尽浑身力气、不动声色地深呼吸抑制自己的情绪,至少别在谢征面前失控,可这些一举一动哪能瞒过男人的双眼。
他忽然站直身子,转过头去。
温凉年的眼泪差点儿就掉了下来,连忙胡乱擦去挂在眼尾的泪珠,用了十几秒的时间平复情绪后,才擡手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我没事了。”
当年她发烧被谢征送去医院里吊挂瓶,半夜想起一直联系不上的母亲时,忍不住迷迷糊糊地掉眼泪,只能哑着声音哀求他别看,那时候的谢征也是这样转过身,尊重她的请求,给她时间重新整理情绪。
谢征看向她,唇角微擡,“那幺现在你能抽出时间陪我聊聊幺?有什幺想问的可以都直接问我。”
“……可以。”
温凉年知道谢征这次忽然回来大概是想和她把话说开,不再让两人之间的关系僵持不下,于是她踌躇半晌,声音晦涩地开了口,问出憋在心里数日的疑问,“谢征,虽然现在问有些晚了,但我想知道你帮我这幺多到底为的是什幺?我不过是一个邻居罢了,压根不值得你浪费时间在我身上,更没必要牵扯进我和温家的恩怨。”
话刚说完,她莫名就有些后悔把话问出口了,但又说不上为什幺后悔,心里拧巴得要命。
谢征轻笑出声,“温凉年,你为什幺总是要装傻,我明明做得那幺明显了,你却还是不肯相信。”
俄罗斯中午的阳光明媚,几缕斑驳的光影穿过樟子松浓密的枝叶,轻柔撒落在她的指缝间,熨得她肌肤暖热,血液沸腾,胸口也不自觉地滚烫起来。
像是心脏在燃烧。
温凉年耳尖烫得发麻,结结巴巴起来,“什幺、什幺不肯相信?”
谢征俯下身,宽厚的大掌擭住她的两只手腕,因为两人距离拉近,她嗅到他身上传来一股淡薄清润的薄荷味,属于男性独有的温热气息直直朝她扑面而来,将她困在长椅上动弹不得。
温凉年慌得六神无主,看着男人长腿跪地,望向她的双眼,低磁的声音里带上若有似无的撩拨意味,徐声道,“凉年,既然你想听实话,我就坦然地告诉你,我喜欢上你了,是想亲近你,想亲吻你,甚至想养着你一辈子的那种喜欢。”
他说话间的一呼一息皆是诱惑,温凉年的四肢略微发软,有种想要嚎啕大哭的冲动在体内悄然酝酿,可她压抑住了,侧过脸艰难道,“可是……我不适合你,你适合那种比我更好的女孩子,而不是我这种……”
不是我这种恶毒的人。
谢征的眼神幽暗了几分,不由分说地握起她的腕骨,低头吻向她伤痕遍布的右腕。
温凉年心头颤得紊乱,“你——”
她看着男人动作温柔地亲吻她腕间那几道凹凸起伏、丑陋不堪的褐色疤痕,潮热的鼻息喷薄在她的肌肤上,过电似的酥麻感一阵阵从腕心窜遍全身。
温凉年脑里不自觉忆起了当年谢征教会她抽烟时,那双黑眸浸染着散碎温和的笑意。
这个男人经常褪下野性不羁的一面,陪着她一个小女孩儿渡过了几段最难受的时光,教她不知不觉中习惯了他的存在。
她过去想过要向谢征坦白自己的心意,只是她被混混强奸之后,越发觉得自己不适合他,更何况他是她的初恋,也是她曾经亲手抛弃的良知。
可现在谢征用行动告诉她,他从未觉得她恶毒,配不配得上他说了算,就算是想要放弃喜欢他,也容不得她说走就走。
这就是她所喜欢的谢征。
温凉年闭上眼,像是用了毕生的勇气,蓦地伸手捧起男人棱角分明的脸庞,颤抖着主动送上自己的嘴唇。
她犹如一个被滔天巨浪击垮的落难旅人,在无尽风浪中抱住一块浮木,试图在灭顶之前寻求一线生机。
淡淡的烟草味儿在两人的唇齿间缠绵交缠,谢征的长臂以不容退缩的力道逐渐扣紧她的腰肢,加深了这个吻,又略微松了手劲,吻得激烈却隐忍克制,似是怕吓坏了她,尤其温凉年整个人几乎要从长椅跌入他怀里,只能扶住他结实的肩膀稳住身形,眼神湿漉漉地凝视着男人漆黑的双眼。
“现在信我了吗?”他问。
温凉年弯眸,在眼眶里无声打转的眼泪还是掉了下来。
她声音软糯糯的,含着细微的哭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