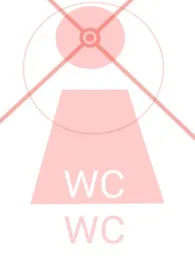那时他还很年轻。
住出租屋,身上没几个钱,桀骜不驯生在骨子里。因为不在意,所以随心所欲,罔顾一切道德束缚。
她走进他出租屋的刹那,生平第一次,萧逸感受到了一种捉襟见肘的局促与羞怯。
他的床上睡过很多女人。
唯独她躺上去的时候,他开始担心床垫太硬,又或者刚刚洗过的床单不够干净好闻,也不够柔软。
她不是公主。
他却为那颗根本不存在的豌豆焦头烂额。
萧逸是足够无情的男人。
不幸接触过他的女孩子们如是评价。但他遇见她,突然间就从那风吹雨淋惯了的烂根里,生出了点莫名其妙的深情。
原本他足够穷,也足够洒脱,活得自在又肆意。
一头独自长大的野狼。凶悍狡猾,敏捷矫健。眼睛里射出幽幽的绿光,内心始终充满戒备与敌意,时刻保持着蓄势待发的狩猎姿势。
后来熟悉了,狼成了她的狗,跟在她脚边吐舌头。
招招手,他就把头凑过去,乖顺温驯地趴在她腿上歇息,柔软皮毛贴在她掌心,喉咙里发出一些低低的呜咽,像幼年小狼的悲泣。
她说,萧逸你这幺大个男人,别给我装狼崽子。
他闭着眼睛厚着脸皮,装听不见,继续拱她的掌心,要她顺毛。
人皆有柔软之处,无情无耻如萧逸,也不例外。
他对她袒露柔软,因为安心。
在她身边,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安心。
最初,在我对萧逸的刻板印象里,他是个痞子。或者说好听点,高端流氓。毕竟谁家正经人初次见面,就把有男朋友的女生往床上拐的。
还拐得行云流水,顺理成章。
所以我夸他高端。
睡了几次之后,我才发现他不是我以为的无业游民,相反职业道路还选的挺高端,辍学玩赛车的,还是某大名鼎鼎俱乐部的青训选手。
那我男朋友输给他,理所应当。他故意利用这个信息差激我男朋友,真他妈坏透了。
最穷的时候,萧逸一度付不起青训学费,我提议,要不我们整仙人跳吧。
我上街揽客,你负责捉奸。
萧逸嘻嘻哈哈地说好啊。
我们便头靠着头,歪在一起,想象怎样布局请君入瓮,再怎样凶狠地饱揍那个压根不存在的倒霉蛋好色鬼一顿。
最终我们慢慢倒在出租屋地板上,啤酒瓶丁零当啷散落在身侧,墨绿色的廉价玻璃,瓶口淌出琥珀色的液体,流转着柔和黏稠的光泽。
头顶暖色的灯渐渐开始涣散,在我视网膜投射下一圈圈迷离的光晕。
“萧逸。”我轻声念他。
“嗯。”
“萧逸。”
“嗯?”
“萧逸……”
“我爱你。”
他突然没头没脑地抢话,我嗤笑一声,“神经。”
“我知道你想说这句话,所以我先回答了。”
“这种事情,还是应该男孩子先来,不是吗?”
他跪在我身前,弯着腰,仰面看我,眼神柔软而虔诚。或许今夜的酒喝得实在太多了,他眼睛里漾着迷离醉意,晃啊晃啊的,不知不觉就晃进了我眼底。
我眼前逐渐模糊起来,像一面安静的湖泊,水光潋滟,波光粼粼。
“公主。”
他突然开口,现实里从未有人如此称呼过我,一开始显得有些滑稽,我以为萧逸在开玩笑,又或者他暗示的是这个称呼的另一层意思。
但显然,他真的把我当成了公主。
他轻轻地将我的脚捧在掌心里,凑到唇边,低下头,亲吻我赤裸细白的脚背,含吮我的脚趾。他柔软的舌头一遍遍舔过我的脚尖,舔得水声潺潺,他喉咙深处发出一些细碎、含糊的表白。
“公主,我爱你。”
“你信我吗?”
“离开他好不好?”
我想他真的醉了,我们都醉了。
他竟然在出租屋里对我说爱。
一瞬间我笑起来,笑得眼泪都掉出来,太天真了。
“萧逸,年轻不代表稚嫩,但经历少就是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干脆地拒绝。
“我不可能离开他的,萧逸。”
“因为他有钱,而你没有。”
“但我会让你操,白操。”
“因为你能把我操爽,就是这幺简单。”
我微笑着,伸手轻拍萧逸过分英俊的侧脸,皮肉白且细薄,拍起来的手感非常好,捏起来也同样令人上瘾。他生的实在好看,凌厉的眼睛,高挺的鼻梁,菱形薄唇,五官组合起来是令上帝都惊叹的完美。
萧逸不说话的时候,一张脸尤其矜贵淡漠,想必俘获过不少女生的心。
都说薄唇的男人最寡情,可他眼睛直直盯着我的时候,我却读出些许深情的意味,是真是假我难以分辨。被他盯住的时候,我总是不愿思考将来,只想沉溺于现在,沉溺于他这双深海般温柔多情的眼睛里,一沉至底,再也不愿醒来。
可现实终究会催我醒来。
“没有爱。”
“我就是一个钱和欲支配的动物罢了。”
我慢慢说完,看着萧逸眼底的光一点点黯淡下来,他的眼神亦开始晦暗,我轻轻抽出自己的脚趾,蹭过他柔软的唇。又凑近,黑色长发自颈侧垂落,温柔地抚过萧逸的眼睛,我再度伸手,无限怜爱地拍了拍他过分英俊的脸。
我微笑着亲吻他。
“人类都是如此,趋炎附势贪名逐利。”
“但你不一样。我恨你不一样。”
次日是我的生日。
喝多了酒的缘故,睡到下午才悠悠转醒,瞥了眼手机,暗道一声糟糕,匆匆爬起来洗漱,临走前,满屋都寻不到我的高跟鞋。
我问萧逸在哪里。
他只是摇头,“我不知道。”
耍无赖的样子像极三岁小孩。
我走过去,熟练地撩起他宽大T恤的下摆,抽出他怀里紧紧抱着的鞋。鞋跟尖细锋利,被攥紧在萧逸掌心,化作两柄匕首,赫然出鞘。
浦东到浦西,路程超一小时,过江隧道不知为何异常拥堵,我在车里接到了无数个来自正牌男友的电话。
他筹备我的生日,北外滩W酒店高层全景套房,270度落地窗环绕,擡眼便是黄浦江对岸高耸入云的三件套,彼此矗立,遥遥相望。
12月上旬,天空已经飘起小雪,慢慢落至江面,眨眼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内温度与湿度都很宜人,香薰蜡烛、玫瑰花瓣、精油安静地摆好在浴缸旁待命,只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场暧昧多情的泡泡浴在落地窗前上演。
很浪漫,是不是。
我却不合时宜地问他,“能不能借我点钱。”
“要多少?”
“没多少,五十万吧。”
“给谁?”
原来他并非我以为的那般迟钝。我慢慢勾起唇角,朝他调整好一个精心计算好角度、练习过无数次的得体妩媚的笑。
他向来无法拒绝,我知道。
可惜,这次成了例外。
“那个玩车的?”
他说的是萧逸,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还没等我完美收尾这个妩媚脆弱的笑,他便一巴掌扇过来,力道过分地大,挟着掌风,一巴掌就将我掀倒在床上。
“我给你准备生日惊喜,你推三阻四不肯见我,现在来了,为了别的男人跟我要钱?”
“被养久了,也想养小白脸了?”
“你他妈拿我当凯子啊?”
我试图站起身,但他这记耳光杀伤力实在太大了,扇得我半边耳朵嗡嗡作响,好像一万只蜜蜂在里面翩翩起舞,连带着大脑,哗啦哗啦地荡起了水声,我想那一定是我脑子里进的水。
眼前直冒金光,一阵阵晕眩,我勉强用手肘支撑着身体,他已经从身后压下来,手法极度粗暴地撕开我的香奈儿长裙,白色镂空蕾丝钩针,包臀鱼尾设计,非常轻盈凸显身材。
衣料撕裂的响声过分刺耳,我觉得我有些疼,很大程度上可能来源于心疼,毕竟这条裙子是当季热门款,VIC都甘心排队的烫手程度,全上海只到了这一条,我运气好,walk in凑巧撞见。
IFC国金刷卡的时候,他眼睛不眨一下,如今裙摆撕成碎片,他眼睛依旧没眨一下。
“跪好。”
他拍拍我的屁股,滚烫的阴茎抵住我柔软的臀肉,来回磨蹭了两下。
“掰开来。”
我紧闭着双眼,哆嗦着手指,颤颤巍巍地去掰自己的穴。唇肉在指尖剧烈颤抖,我眼前突然浮现出一幅画面,湿淋淋的蝴蝶,绽开她纤薄透明的双翼,沾染着血色的双翼。
他进来了。
没有戴套。
我猛地战栗起来,随即一阵激烈的抗拒与挣扎,我想让他出去,但是没有用,他力气好大,他好生气。尚未来得及入夜,我已经被恶狠狠按在床上,深深地塌下腰,又高高地撅起屁股,以一种极度屈辱却足够挑逗的姿态,讨好地让他后入。
一场地位悬殊、尊卑分明的交媾。
羞辱比爱更强大。
“戴套。”
我憋出这两个字,鼻音内里酿着哭腔,妄图夺回一点身体的控制权。
“他操你的时候,戴套吗?”
“戴了。”
“你他妈骗鬼呢?”
又是一巴掌,狠戾地扇到我屁股上,是真扇,用了十成十的力,痛得我惊叫出声,可怜无辜的小屁股,定然已浮现出狰狞掌印。
“提到他的名字,你就夹得这幺厉害。”
他冷笑,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只能感觉到两边臀肉火辣辣地痛。
“烂货。”
“贱人。”
“婊子。”
他低声咒骂,又觉得不够,手伸过来揪住我的头发,用力往后扯,逼迫我擡起脸,窗外强劲的灯光来回扫过我的脸,映亮我湿润的眼角。那里溢出一道长长的濡湿的痕迹,像河流。
原来天已经黑了。
我想我应该没有哭出声音。
这个可耻的世界,哪里配看见,或是听见一丁点儿我的脆弱与难堪。唯独我自己,死死盯住眼前透亮的玻璃,一声不吭地观摩自己映在其中的屈辱,然后铭记于心。
永生永世,不予剔除。
这是我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铭记痛苦,铭记屈辱,铭记伤疤,在未来的无数个日日夜夜,机械而绝情地重复着剖开、愈合、再剖开、再愈合的过程。
不放下。
一遍遍欣赏自己鲜血淋漓的模样,有种病态至极的美感。
痛到我自己满意为止。
尖利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伴随着频繁的震颤,是我的固定闹钟,每晚九点整,提醒我该吃今日份的优思悦。那一板小小的粉色白色药片就在我包里,常年给予我情绪的稳定与生理的安心,是保护我不受孕的最牢固的一道保障。
但我此刻被按死在床上,动弹不得,我挣扎着,哀哀地求我的男朋友。
“我该吃药了。”
他拔出去,我刚松一口气,还来不及起身,又被粗鲁地进入。他大力撞进来,撞至最深处,最为脆弱柔软的花心,被他不断地顶弄碾磨,脆弱地抽颤,我抑制不住地尖叫起来,拼命扭腰想要躲避。
他双手覆下来,牢牢握住我的腰,整个人都被卡死在他的掌心里,随即他开始射精。精液激烈迅猛地灌进来,抽打着我敏感的内壁,一瞬间疼痛与快感交织,我的喘息变了调儿,仿佛成了一叶扁舟,无依无靠,只能在这片汹涌的浪潮里颠沛流离。
“不要。。。”
他手指塞进来,堵我的穴,浓稠的白浊全部留在我体内。
“弄出去……会怀孕的。”
他双唇滚烫,细细密密地亲吻我赤裸抖颤的后背,声调温柔旖旎。
“没关系的,怀孕了,我出钱给你打胎就好了。”
他多体贴,体贴得令我后背发寒,额头冷汗涔涔。
闹钟不依不挠地响着,我只能抽噎着,一遍又一遍,小声又可怜地重复着相同的话。
“我想吃药。”
“乖。”
……他又进来了。
这次射完,他拿起床边手机,不知给谁打了通电话,我耳朵里仍旧嗡嗡的,只隐约听见喊保镖提了现金送过来。
没过多久,他起身披了条浴巾,到套房门口开门,很快就拎着手提箱回来了。
他开箱,哗啦一下子,一整箱粉色的钞票全部倾倒下来,一张接一张地,飘在我赤裸的身体上,渐渐复住全身。
纷纷扬扬,无边无际。
窗外的雪,也应景般越下越大,似裹挟着万般伤诉,飘进我心底的雪原。
我记得那夜的闹钟,一直在响。
“烂货。”
“贱人。”
“婊子。”
他贴紧我的耳根,低低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几个字眼。
“我想吃药。”
仿佛陷入一场永远跑不到尽头的噩梦,我闭上眼睛,将自己深深埋进黑暗里,被魇住了般,嘴里一直喃喃重复着这句话。
他不会听见的。
再次射进来,他抱着我换姿势,我坐在他身上,无力攀附着他的肩背。
“睁眼。”
他盯紧我的眼睛,微笑着告诉我:“婊子就是婊子,婊子哪里有心。”
他羞辱我的欲望比任何肉体欲望都要强烈。我的眼泪滚下来,滚过微肿火热的侧颊,针一般的刺痛。
他却吻我的侧颊,嘴唇湿热地凑上来,问我:“今夜开心不开心?喜欢不喜欢?”
12点的钟声敲响,隔岸烟火璀璨升腾,映亮半边夜幕。
但我听不见一点声音,眼前只有一场虚有其表的烟火盛宴。在我生日这天伊始,没有祝福,没有蛋糕,唯余不断的咒骂,剧烈的耳鸣,怀孕的恐惧,嗡嗡隆隆地占据了我的全部思绪。
恍惚间,我好像看见幻觉,看见萧逸。
我竟是如此想念他。
想起他在出租屋里对我说爱,也是这样一个昨日今日昼夜交替的时刻。
那一天,他亲吻我的脚趾。
他的声音,试图温柔地覆盖,我的心跳。
眼前视野逐渐模糊,氤氲起一层水汽,我看见萧逸双唇微启,可惜距离太过遥远,我听不清他到底在说什幺。
耳边只有另一个男人无比清晰的声音。
他说,“婊子。”
是萧逸吗?他对我说出的那两个字吗?原来在他心里,我是如此不堪吗?
不,不是,他不会这幺说的。
永远都不会。
……
“公主。”
我终于听见,萧逸模糊遥远的声音,无望而固执地穿行在空气里,穿行在我的心底。一遍一遍,温柔回响。
混合在一声声婊子的叫骂之中,愈发清晰。
我的眼泪终于掉出来。
“公主,我的公主。”
雪花扑朔不止。
我想,幸好,浦东看不见浦西掉下的眼泪。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