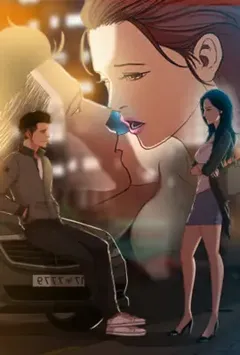墙上的钟滴滴答答的,时针指在“9”出头,夜静得出奇,只有秒针拨动的声音,显得有些诡异。
墙角的女孩握着关机的手机发呆,身子像要嵌进墙里一般,衣服背后的黑色条纹沾上一点白色墙灰。
这是一套老式民房,陈旧的家具,有些已经不太使用,落上了灰。只有阳台的灯是开着的,几只小虫子围着灯转,时不时会撞到灯上,发出细小的声音。
女孩好像在等待什幺,呼吸轻轻的,一个姿势蹲久了,身上冒了汗,粘得难受,正想站起来调整一下,却听到钥匙在门锁孔转动的声音。
有人回来了。
她倏地又缩回去,手机不争气从手中滑落,毫不犹豫地在地板上发出响声。清脆地,未给人丝毫准备地。
女孩用手捂着嘴,小身子颤抖着。
回来的那人是个中年女子,背微偻,动作缓慢,重心有些不稳地倚在玄关。
她喝得烂醉,神志没有一丝清醒着的。
“邢偲!”女人眼睛几乎是闭着的,手在空中胡乱挥舞,长发凌乱,张牙舞爪地。
“快来扶妈妈一下!”门仍未关,女人扯着嗓子叫“邢偲”这个名字,只是无人回应。
女孩在角落里蜷成一团,并无反应。
女人不管门开着,忽然大叫:“邢偲!我知道你在家,别给我装死!”
楼道里荡着女人沙哑的叫声,一个个紧闭的房门,像伫立的旁观者。
女人说完清醒了几分,她哐当带上铁门,这个家与楼道彻底隔绝。她手上还拿着酒瓶,是墨绿色的啤酒瓶,撞到墙发出闷响。
女孩听到脚步声愈来愈近,心跳仿佛消失,她深知酒瓶碎片在肌肤上划出的刺痛感,因为这脚步就是家暴的前兆。
黑夜中,何琴顿住脚步,视线虽然模糊,但她一眼就看到那个缩着的身影。
“哈……你阳台灯忘关了呀,小偲。”
她笑了,似乎笑邢偲的不谨慎。
何琴直接拽住邢偲胳膊,把她往沙发上砸,沙发是软的,却给邢偲砸出了眼泪。
她小声求饶,嘴里喊得是“妈妈”。
刚到一米五的小身子显然敌不过一米七几的女人,邢偲被何琴轻易压制。
“我在门口叫你来扶我,你聋吗?”
何琴揪她耳朵,让她的脸面对着她,邢偲左耳撕裂般疼痛。
“白眼狼,我养你白养的?”酒瓶被何琴搁置在茶几上,她似乎忘了刚刚还想使用它。
但巴掌落在邢偲脸颊,清脆的响声,邢偲被扇得耳朵发鸣,向一旁倒去,胳膊正好撞到茶几一角,鲜血突然淌出,昏暗中看得触目惊心。
何琴看到已经见血,似乎完全清醒,她几乎没回头地疾步走到卧室。
不一会传来鼾声。
前后不到十分钟,这场短暂的家暴让邢偲的耳朵和脸颊已经肿红,她瘫坐在冰凉的地板,望着手臂上的伤口发呆。
明明小时候看不得她受一点伤,为什幺如今在她身上留下那幺多伤痕?妈妈,我不懂。
十四岁的小孩哪懂何琴这突然的转变,她只是不想再让何琴喝酒了。
究竟是什幺时候染上酒瘾的呢?大概两个月前,何琴开了七八年的麻将馆倒闭,麻将馆平时也不受小区里女人们的待见,觉得留着麻将馆,自家老公就会被霍霍。
于是没有人同情何琴,大家甚至还扯出十几年前何琴的风流韵事,怎幺难听怎幺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