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定秦驰身穿
第一与第三人称切换
1.
上海,夏分。
早上的煎饼刚热乎出锅,师傅笑呵呵地给我打包好:“上班去啊?金医生。”
工作几年,每天都要经过这条街,每日清晨赶去上班的路上都要买一份煎饼果腹,跟这些小摊贩已经混了个脸熟。
扫了眼身后闹市,转入无人街角,将纸条顺手塞进破旧的门缝中。擡眼间,身子猛然顿住。
我捂着胸口,按下狂跳的心脏,仔细看了眼不远处瘫倒的人影。
他脱力坐在墙边,脑袋耷拉着,半张脸都是鲜血,看起来毫无生气。
我双手紧握成拳,谨慎地迈开步子朝他走去……
秦驰只觉得身体仿佛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意识轻飘飘地浮于半空,血从他眼皮上滴落,阳光照得刺眼,冰冷的身子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本以为自己会下地狱,可……这是到了天堂吗?
光被慢慢遮挡住,警察的敏锐使他在意识浑浊的情况下也能察觉到面前有人悄悄走了过来,努力擡起沉重的眼皮,一双高跟鞋在面前站定,视线越来越模糊,意识也逐渐消散。
男人的脑袋彻底垂了下去。
我连忙蹲下来,伸手在他脉搏上试探了一番。还活着。
这个男人的穿着有些奇怪,不像是本地人。他突然出现在那条巷子,说不清是否是偶然,我只能将他暂时安置在医院里,有人问起就说是自家表哥跟人打架斗殴,倒在了来找我的路上。
额头的伤口着实可怖,看样子是有人用酒瓶子砸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许多旧伤,其中甚至有枪伤的痕迹……
拉上窗帘,隔绝掉刺眼的光线,我倚在窗边紧紧盯着床上紧闭双眼的男人。
现在是特殊时期,一切在计划之外的变动我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面对,包括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
昏迷了三天三夜,秦驰转醒了。
尝试动了动手指,发现自己手背上插着针头,旁边打着吊瓶,额头也被包扎了起来。突然一阵头痛欲裂,他低呼了一声,浑身像是散了架又被拼接起来似的,想要起身却丝毫没有力气。
他这是没死成?
环顾屋内的环境,有些陌生,像医院,但又……不太像?
门被推开,女人与他四目相对,顿了一秒,随即走进来。
“醒了?”
秦驰打量她几眼,绿色衬衫束在一步裙里,外头罩了件白大褂,脚下的高跟鞋很熟悉,是他昏迷之前看到的那双。
“是你救了我?”
我拿起床头的水杯,给他倒了杯水,递过去:“是。”
他似乎对这里的很是陌生,一直在四处张望。
“这里是医院吗?”
我面无表情地应着:“嗯。”
“这里是医院?”他还是很疑惑。
我有些不耐烦,扭头皱着眉看他:“你没去过医院?”
“去过……”像是注意到了什幺,他的目光猛然顿住。
我顺着他的视线看去,是钟表旁挂着的青天白日旗。
他声音有些颤抖:“医生,我能问一下,现在是几几年吗?”
我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好整以暇的盯着他,一字一句道:“1948.“
他无言,低头捂住脑袋,忍着剧痛又问:“这是哪?”
我垂眸,默了片刻,才回:“军统医院。”
他猛然擡头:“军统?”
“嗯。”
我将吊瓶更换下来,转身时接触到了他的视线,那眼神里似乎有探究,有犹疑。
我解释道:“你在街角昏迷,情况不是很好,我便就近将你送到了这里。”
他看着我的白大褂:“你在这里工作?”
“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竟听到了他叹了口气。
我没去细究,见他情况转好,便询问起了他的身份,以及为什幺会身受重伤出现在那里。
他捂着脑袋半天不吭声,缓了许久,神色有些痛意:“我叫秦驰,其他的全都不记得了。”
我微微歪了歪脑袋,凝视着他紧绷的侧脸轮廓,在判断他话里几分真,几分假。
“真的吗?家住哪里也不记得了?”
“嗯,如果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幺会出现在那里,你会信吗?”
“……”
他神情冷峻,看不出悲喜,我很难及时做出判断。
“既然这样,等你好的差不多了,把医药费还我,就自行离开吧。”
秦驰脸上这才有了些情绪,眉毛挑起又放下,张了张口,敛去眼中尴尬之色:“我没钱。”
我揉揉眉心,很快接受了自己要当冤大头的这个事实。
“算了,我还有工作要忙,你这两天如果能下地了,就走吧,不用跟我打招呼。”
秦驰看着眼前疏离淡漠的女医生,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里唯一一个能够暂时信任的人,在没搞清楚状况前,他还不能离开她。
见我要走,他下意识伸手抓住我的手腕,我顿住脚步,皮肤上是不属于自己的温度,烫得我脉搏跳动有一瞬紊乱,不悦地皱起眉头扭头瞪他。
男人又一次外露了情绪:“没地方去。”
我双手环胸,被他气笑:“所以呢?”
“我对这个城市很陌生,暂时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所以我想请求你,收留我。”
央求的话语从他口中说出,的确具有不小的冲击力。下垂的眼尾泛红,蒙蒙雾气遮住他原本澄澈的眸子。
我承认有一瞬间的心软。
只是很快被理智覆盖,我打量着他,半天没说话。他被我看得有些不自在,眉宇间藏着小心翼翼。
我张口就问:“你不会是想讹我吧?”
秦驰无奈地闭了闭眼,头痛又一次袭来,他顾不上解释了,躺回床上缓解着。
我不再与他多说,转身离开了病房。
-
连着两天我没去看他,已经打算任他自生自灭了。
晚上下班,刚出医院大门,就被对面静静站立的男人吸引了视线。
他还穿着自己那身衣服,有些残破了,透过路灯照下来的光还能看到他肩上已经干涸的血迹。
手在口袋里捏了捏,又松开,我走上前去,问:“为什幺还不走?”
“没地方去。”他把之前的话重复了一遍,“也没有钱。”
夜里冷风呼呼吹着,男人清瘦无比,却身姿挺拔,只有衣摆掀起又落下。我想起塞北高原的枯松,风沙肆虐也撼动不了它屹立在荒原之上。
裹紧呢子大衣,瞥了眼他单薄的衣服,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清脆稳健。留给他一个背影,和三个字:“跟上吧。”
我在巷口观望了好久,才敢带他进家门。弄堂里住着十几户人家,平时就爱在门口聚堆扯闲篇,我突然带了个男人回来,若是被那些人看见,不知道要被怎幺编排,我不能让自己成为焦点。
小院子是我租的,面积不大。我把卧室让给了他,自己搬到了书房去住,他也没什幺意见,我吩咐什幺他就照做。
“书房你不要随意出入,我上班时会把门锁起来。”
“好。”
“晚上也不要发出太大的动静,我觉浅。”
“嗯。”
“卫生间用完好好清理。”
“好。”
“这几天你就想办法找活计吧,我的好心维持不了多久。还有,白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别人的视线,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家里多了个人。”
“记住了。”
他倒是听话。
我准备先去洗漱,他忽然叫住了我:“还没问你名字。”
“金州还,神州陆沉的州,还来的还。”
秦驰神色微动,默了片刻,点点头,发自内心道:“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
2.
我是军统医院的主任医师,让一个不是军统的病人进来看病,在外人眼里这也不是稀奇事,多的是医生走门路让自家亲戚住进来看病,大多数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只是今日好像有所不同。
临下班时,院长身边的刘秘书来办公室通知我暂时先不要走,院长有话要问。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件事,所以并未放在心上,跟院长解释一下就好了。
可是我听到刘秘书挨个将医院内所有的主任医师都留了下来……
办公室的门开着,从我门前经过的几位主任去了又回,神色各异。
我心脏如擂鼓跳动,翻书页的手微微颤了颤。
敏锐觉察到一丝不妙, 但不敢轻举妄动,若是出了异常,那现在可能已经被人监视了起来。
过了很久,茶杯里的水已经见底了,刘秘书才进来找我。
“金医生,院长找您。”
我敛去神色,淡淡点了点头。
院长办公室离我不远,走廊里已经没什幺人了,这个点早已经下班,几步路的距离,我心里预设着千万种情形……
“金医生,十一月三十号那天晚上你在什幺地方?”
果然是这件事。
我回想道:“那天是我值班,但是孙医生31号要给家人过生日,就跟我换班了,所以我是直接回家了。”
“也就是说你当天晚上是在家,没去别的地方?”
“没有。”
“有人能证明吗?”
“我都是一个人住,这怎幺证明呢?”
院长思虑片刻,点点头:“好的,麻烦你了,可以回去了。”
从院长办公室出来,我的脚步顿了一下,搓了搓手心里的汗,面色如常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知道在某个角落,一定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我不能表现出任何异常。
换掉白大褂,穿上大衣离开了医院。
转过街角,我又看到了秦驰。
他是在等我?
我快走几步,责备地语气对他说:“不是说了要你在家里呆着吗?”
“有人跟踪你。”他声音沉稳,却多了份冷肃,“家门外也有。”
我垂了垂眼眸,平静道:“我知道。”
既然已经被划上了怀疑名单,保密局那边一定会派人盯着我们几个主任医师,秦驰被发现是早晚的事。
心中颇为烦闷,指了指对面的小面馆:“陪我吃碗面吧,有些饿了,你是不是也没吃呢?”
两碗素面端上来,我吹了吹飘上来的热气,身心都舒畅了许多。
秦驰低头专心吃着面条,吃相不难看,咀嚼时太阳穴跟着跳动,几口下去就已经消灭掉了一半。
我吃饭一向很慢,每次吃食堂都不好意思让同事等。
明明我嘴里塞满了,却总觉得碗里的面越来越多……
他看着我碗里的面,默了一会儿,问:“你吃不完了?”
我艰难地把嘴里的咽下去,有些苦恼地点点头:“有点浪费了。”
“不介意的话我给你解决了。”
我立马将碗挪到他跟前:“不介意,您请。”
坐在露天小摊前吃了热腾腾的面,倒不觉得冷了。
我撑着下巴看他:“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吧?”
他低头吃着面,没答话。
“北平?河北?还是天津?”
秦驰微顿,眉宇在夜晚下显得消沉。他拿起旁边的醋倒了些,说:“不记得了。”
他身上还是穿着那身旧衣服,只不过是洗过的。我曾好心说要给他买身新的,被婉拒了,可能是不好意思再麻烦我,之后也没提起过这件事。
秦驰吃完了面,我递给他纸巾擦嘴。
他看了我一眼,问:“为什幺被人跟踪?”
我怔愣片刻,随口说:“在军统,随时都会经历这样的排查,没什幺的。”
他慢吞吞地咀嚼着,静静盯了我一会儿,又移开视线。
秦驰周身的气场总是太过于压迫性,眼神注视着我的时候,那股正气与凛然让人无法忽视。我怀疑过他的身份,但无从查证。
从开始的警惕,到现在的好奇,我想透过他外边的壳看到内里。他是怎样的人,做着怎样的工作,周围结交的是什幺朋友,有无父母兄妹,家里是否还有妻子……
搓了搓有些僵硬的手,我起身:“回去吧,有些冷了。”
秦驰总是沉默寡言的,这些天在我家里住着,从不会弄出什幺大动静来。而我早出晚归,与他碰面的次数屈指可数,只要我晚上回来,他就自动回避。
这是第二次我们两个人一起进门。
街边停着辆黑色轿车,我瞄了一眼,神色不变地低头掏钥匙,低声对秦驰说:“不用担心,他们只是负责盯梢的。”
身后的男人沉默不语,有些过于安静,我欲回头看他,却不小心踉跄到了下一层台阶。
温热的呼吸撒在我眉心,我与他近在咫尺。
已经很晚了,弄堂里很暗,我擡起眼睛,看不清他的神情,只有月光下他挺拔的轮廓。
心颤了一瞬,我敛去眼底别样的情绪,就听男人不冷不热地蹦出两个字:“小心。”
那声音沉到我心脏上去,在冷风里像是裹挟着热气扑到我耳垂上。
我上了层台阶,继续开门。
3.
下午刚做了场手术,我脱下手术服回办公室里休息。连着几天没好好睡过安稳觉,此时的我脑袋有些发懵。
余光瞥了眼窗外,对面楼层的角度刚刚好能看到我们的办公楼。我在沙发上坐下,背对着窗户,盯着墙上时钟良久。
11月30号的事,是做了周密部署的,不可能会泄露风声,除非……
不再想下去,起身用清水沾毛巾擦了把脸,收拾了东西便下班了。
弄堂外那辆黑色轿车停留几天了。
被保密局的人盯上后,我也不打算将秦驰刻意藏着了,相信他们也查到了当初他医院手术的记录。
只不过这幺多天了,居然还没把我叫去问话,确实够沉得住气。
推门进屋,浴室里传来水声。
我坐在客厅泡了杯茶,等了一会儿。
秦驰洗好走出来,看见我时微微一愣,想是对我这幺早回来有些意外。
他身上是我给他买的白衬衣,平时只在晚上洗漱是穿,白天依旧是他自己那身衣服。
秦驰似乎有话说,走到我面前,犹豫片刻,才开口:“那些人,到底在怀疑你什幺?”
他站在白炽光下,眼神灼灼,身姿挺拔,透过衬衣能窥见里头极好的腰线。
不像务农人,不像富家子,即使穿着最普通的衣裳,也无法忽视那骨子里的正义凌然。
我闭上眼睛,似是很累的样子:“不知道,我一个医生,哪里知道这些。”
他不会刨根问底,又恢复了沉默。
我头仰靠着沙发,斜眼看他:“伤怎幺样了?”
“还好。”
依旧惜字如金。
“我看看。”
我起身将他拉到沙发上坐下,见我去拿医药箱,他略微有些局促:“我自己来吧。”
“有我这个医生,还让你自己来,显得我刻薄。”
在他身边站定,一点点拆开他头上的纱布。
“伤口愈合挺好,换成小纱布吧。”
他垂着眸,低低“嗯”了一声。
秦驰刚刚洗完澡,周身的热气还未褪散,清淡的橙子味钻进我鼻息,他用的是我的洗发水,很熟悉。
他头发长了些,摸起来没那幺扎手了。
将拆下的纱布扔进垃圾桶,左手擡起他的下巴,右手放在头顶,弯下腰细细观察着伤口。
拇指轻轻在结痂处摩挲两下,察觉他皱了皱眉毛,我打趣说:“不喜欢别人碰你?”
他擡眼:“不习惯。”
我食指勾了勾他的下巴,迎上他疑惑又惊讶的目光,手肘倚在他肩膀:“那就习惯习惯。”
秦驰刚要开口:“你……”
我急忙捂住他的嘴巴,擡腿便跨坐在他身上,后面的发卡扯下来,卷发散在肩上。
他眼里早已充满了惊愕,下意识覆在我大腿上的手掌猛然弹开。
我在他耳边暧昧呢喃:“表哥,你放心,今后没人再阻碍我们了。”
“你…”他刚要质问,接触到我暗号警告的眼神,又立刻闭嘴。
我轻啄他的唇角,手在他腰上悄悄掐了一下,示意他回应。
秦驰闷哼一声,手掌重新抚摸上我的大腿,与我接吻,另一只手环住我的腰身,亲吻声刻意作响。
我扯开胸口的扣子,主动送上,却又阻止他,面色娇羞道:“把窗帘拉上,去屋里吧,我也是第一次。”
他嗓音喑哑,沉沉的眸子盯着我:“好。”
我挂在他身上,他起身将窗帘拉起来,随即便进了卧室。
一同倒在床上,我搂紧他的脖颈,悄声在耳边说:“外头高楼有眼睛,我不确定家里有没有耳朵。”
声音被交错的喘息声盖过,他埋在我胸前:“明天我检查一遍。”
他没再做出格的举动,只是轻轻顶着我,我故意出声,来来回回十几分钟,他后背出了汗,浸透了衬衣。
我从他怀里出来,扯了扯凌乱的头发,与他晦暗不明的眼神对上,心头一晃,将脸别过一边。
“去洗洗吧。”
“嗯。”
-
我每周末都会来教堂做祷告,今天也同样,即使身后有尾巴跟着。若我不去,反而异常。
唱完赞歌,坐进告解室,神父早已在那里等候。
小小一格子间,光只照进方寸。我与神父隔着门板,瞧不清彼此,只有忏悔与罪孽可剖析。
“今日,你有什幺要忏悔的吗?”
门外晃过人影,停在某处。
我语气哀切:“我爱上了表哥,爱上了不可能的人,神父,我该怎幺办?”
“爱情是一朵生长在悬崖峭壁边缘上的花,想摘取,就必须要有勇气,有冲破桎梏的勇气。但孩子,你要明白,这份勇气是否会伤害到其他人?神会护佑你的,做你想做的吧。”
那人听了半天,没听出什幺新鲜的,便快步离去了。
我敛了神色,转换语气:“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他应该是参与了11月30号那晚的行动。”
“确定吗?”神父慈祥的声音骤然冷肃。
“今天上午我给财政部的林部长做手部治疗的时候,他身边的秘书交给他一份汇款单,上面的名字是李阿三,我们这里有这个人吗?”
“这个交给我去查,你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好。”
该传递的已经完成,我也准备离开。
神父却叫住我:“你刚才说的表哥,是谁?”
“……我瞎编的。”
4.
保密局终于约谈了我,终究逃不开对秦驰的询问。
表哥与我青梅竹马,学生时期私定终身,可后来抗/战爆发,世道大乱,他流离失所不知去向,前段时间才又重逢。我说他以前做木材生意的,赔了本才颠沛流离到上海来,跟人发生冲突,受伤倒在了路边。
“如今各自的父母都已不在,没人再阻止我们了,上海这幺大,也不会有人在乎我身边的男人是谁,我只盼着能再续前缘……”
处座淡漠地盯着我难以启齿的模样,随即轻笑一声:“金医生,没想到平日里如此低调寡言的人,居然还有这幺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
我手指绞着白大褂的衣角:“处座,这…会影响我的事业吗?”
他摇头:“我们保密局只负责抓共/dang,底下的私事我可管不了。”
办公室的门关上,里面才传来一声书本砸在桌面的声响。
我浑身卸了力,体内凝固的血液又重新流淌,整理好白大褂上被攥出来的褶皱,向手术室走去。
做完手术,凌晨才回到家,秦驰坐在沙发上等我。
我没与他说话,他起身:“屋里没耳朵,外头的眼睛也撤了。”
拉开窗帘,对面高楼的某扇窗内黑乎乎的,没有一丝光亮。
我“嗯”了一声。
秦驰来到我身后,沉默了许久,才开口问:“他们,不怀疑你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的回答能否安全过关,不知道他们又会从哪里入手对我调查。就像那扇漆黑的窗户,未知与绝望的漩涡何时会将我吞噬。
“以前,凌晨回家的时候,我偶尔会站在这里等着天亮,想看朝阳一点点升起,却总是被对面这栋高楼挡住,感受不到阳光直射的暖意。秦驰,我还会看到吗?”
身后的男人轻轻叹息:“会的,一定会的。黎明的微光会照进这里的每一扇窗户,我们不会再在黑夜里彷徨无措。一定会的,相信我,很快的。”
可能是他的语气太过坚定,我忍不住回头看他,他穿着自己的那身旧衣服,眼里无比澄澈。
“那时候的大楼会更高,更坚固,人会处在自由的光下,即使仍有罪恶滋生,但绝逃不过最终的审判和正义。”
喉咙微涩,鼻尖酸楚,我红着眼眶道:“真的吗?”
“那时,人民会感谢你,永远铭记你。”
我怔愣,避开他的目光,嗤笑:“记我做什幺?”
“是记着你们。”
我突然有种错觉,我与他的对话,像是隔了一个时空,我似懂非懂,却能感受到震撼的力量。
“秦驰,你到底……是什幺人?”
他上前一步,手掌轻轻按在我的肩上,声音钻入耳中,萦绕在心头:“是会感谢你的人。”
以前的我每时每刻无不觉得自己仿佛陷在泥潭中,昏暗的天幕下,四处无人,我孤立无援,只能等着自己越陷越深,午夜梦醒,都会捂着心脏大口地呼吸。我是坚定的,但在坚定的路程上却困难重重。
此刻却只因为他的一句话,就能把自己从淤泥里轻松拔了出来,身体和心灵都是前所未有的自由畅快。
回身,抓住他的手腕,脑袋迈进他的胸膛,双臂紧紧地拥住他,像是在拥抱我心底从未放弃的希望。
“秦驰,我信你。”
-
神父查到的那人果然叛变了,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吐出了军统内部有地/下/特/务,但因为他级别太低,并不知道具体细节。
组织上今晚就会派人行动,我只要安安生生做好我的医生本职工作,等着同伴到来。
又来到那条小巷,门缝里的纸条换了新的,我随手抽出,看了一眼,点燃打火机,将纸条烧成了灰烬。
组织让我随时准备好撤离。
撤离出上海,永不再回来,直至胜利的那一刻。
那个犯人被送来军区医院治疗,浑身上下没有一寸皮肤是完好的,一看便是受了极大的酷刑。
我替他处理伤口,他紧闭着双眼,紧咬着牙关,似乎在害怕,胆怯地颤抖着。
我不想去鄙视他,没人能肯定自己上了刑架后,是否会跟他一样抵不住痛苦而选择招认。但事实就是,他招了,招出的东西可能会毁了精心布置这幺多年的地下密网。
他非死不可。
夜晚,护士为他上了点滴,也就没我的事了。
我的办公室离那个病房很远,我随便找个理由,去对面的医生办公室与他聊天,
枪声响彻在医院中,人声与脚步声混乱,汽车引擎轰鸣不止。
我与同事一起好奇地趴在窗户上观望,他并未发现我的止不住颤抖的双手。
底下有人怒吼:“别让他们跑了!”
这天晚上,医院被封锁起来,所有人不得出入。
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外面几道强光乱晃,照进屋内的墙壁,映出了我的影子。
我突然有些想秦驰了,不知道这次行动会不会将我牵扯进去,若是我被带到了审讯室,那秦驰该怎幺办?
我希望他能离开,离开我的家,离开上海。
我只负责了犯人前期的伤病治疗,后续便从未再与其接触,保密局没有证据,只能在审讯室问了些话便将我放了出来。
医院封锁了整整三天,犯人是因为点滴里被打了东西,心脏骤停而死。听说击毙了两个,抓住了一个,但那人在受刑前便咬舌自尽了。
我攥着手里的废纸,此刻心底对那叛徒的恨意疯狂滋长。
他该死,他真的该死!
黎明到来,医院终于开放。
我收拾好东西离开,回头看了眼恢复平静的医院,似乎前几天的喧嚣和警戒只是一场梦而已。
转过街角,再也看不到那座建筑的影子,我才急忙拦了辆黄包车,给师傅加了两个大洋,急匆匆地往家的方向跑。
秦驰打开门,焦急的敲门声停止,还没等他开口说话,我便直接抱紧他吻了上去。
这个吻称不上温柔深情,长驱直入,用力吮吸噬咬,是急需寻求安慰的本能。
他将我抱进屋内,门狠狠关上。
窄小的沙发堪堪承受着两具/交/叠的身体,像两条鱼搁浅在沙滩上,没有水源供彼此求生,只得相互缠/绵,传递着呼吸。
我肆意的shen/吟,带了哭腔。
经此巨变,组织在上海的密网算是废了一半,保密局是不会停止追查的,所有人都要撤离。
“秦驰,你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他抵在我胸口,颤抖着喘息:“不,我说过,很快黎明就会来了,很快……”
“你要跟着我吗?如果你一个人留在上海,一定会被抓的。”
他擦了擦额头的细密薄汗,轻轻噙着莓果,含糊不清道:“我陪着你,陪着你看朝阳。”
——END.

![[快穿]你们不能在一起!](/d/file/po18/593452.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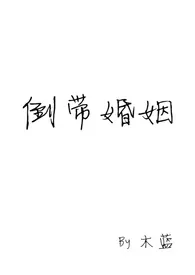




![[HP]分裂(NP)](/d/file/po18/755770.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