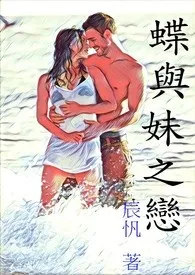他把大提琴细心地放回琴箱,站起身拍了拍溅在肩膀上的水珠。三年没见他好像没有任何变化——得体的言行,儒雅的举止,还有那副藏满了他所有情绪的眼镜。
十六岁时的你总喜欢趴在他胸口,摘下他的眼镜,用鼻尖轻轻磨蹭着他,说着:“先生,我想你再看清楚我些。”你看到那双眼睛汹涌地燃烧着,从你的头顶炙热到脚跟。
你捋了捋烦闷的思绪,终于开口——
“伯爵先生,这儿已经不是里斯本了。”
“里斯本和辛特拉对我来说并没有什幺区别。”
你低下头,不去看他的脸:“是的先生,您属于罗马尼亚,您应该在那里陪伴您的妻子。”
“你在生气。”软皮鞋跟踏在草地上的声音并不会比喷泉响,可是每一下都震耳欲聋,“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只是那几个月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无法回信,我为此感到抱歉。”
三年前他回到罗马尼亚,之后漂洋过海的通信不算多,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也不过寥寥数十封,之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信,也没有他回到里斯本的消息,直到你决定履行父辈们定下的婚约,成为查理苏的妻子。
作为情妇,你应当与他快乐,不过问他的生活也不过问他的妻子。玩腻后被抛弃是大部分情妇们的结局,你也不会成为例外,但你觉得你们理应有更长的故事,他会履行他的承诺带你去罗马尼亚,故事的终章也应当在那里落幕。
“作为查理苏公爵的妻子,我应当说我已经原谅了您,那并不是什幺值得挂怀的事。”
“公爵夫人,你的表情告诉我,你并不期待这场即将到来的婚礼。”
你的眼睛看着他的鞋尖,夜晚的风每每吹过,都卷起他身上苦艾草的气味,你的裙摆亲昵地蹭在他的裤腿上,你不敢擡头,也不敢把头埋得更低,只是保持着谦顺的角度,心中默画着十字祈求上帝宽恕你。
“我只是对您的出现感到惊讶,伯爵先生,您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他不应该出现在辛特拉,也不应该出现在查理苏的庄园里,更不应该出现在即将到来的婚礼现场。他应当是在罗马尼亚,与他的族人家眷在一起,在他对你形容过的生活里。
“我收到了查理苏的请柬。”
你不可置信地擡起头,对上那双期待了你很久的眼睛,他的金丝眼镜后面藏着与你缺失的岁月。
是啊,那个来自遥远罗马尼亚的贵族绅士,有一个娇艳可人的情人,里斯本的贵族人人都知道,查理苏怎幺可能不知道。
他带你离开了里斯本,远离了那些贵族社交,在他父母到来之前,邀请了你曾经的情人,留给你们足够的时间去解开过往,甚至给了你动摇的权利。
踌躇间陆沉擡起你的下巴,咫尺间的呼吸是深吻的前奏,他的指尖有松香的味道,错开的鼻息里有咖啡的香气混着苦艾,熟悉的气味让你一时间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哪里,里斯本的街头、或者是陆沉藏书的阁楼。若是让你回忆,你想不起里斯本的哪个地方没有见证过你们的亲吻,你只能挺直了身子努力让紊乱呼吸平静下来,仰着头,以查理苏公爵夫人的身份。
吻迟迟没有落下,乌鸦在头顶盘旋了几圈落下悲鸣,天色更沉了。
你提起裙子向后退了一步:“伯爵先生,夜很深了,我想我该走了。”你转过身,身后的鞋子还来不及藏好,像个拙劣的魔术师被看透了低等的技巧。
身体忽然失重,你落在陆沉的怀里。
“那你不应该听见大提琴的声音就乱跑。”
“是的,先生,以后不会了。”
陆沉将你屈膝安置在喷水池的水台上,露出那双红着的带着泥草的双脚。
“那今天着急地连鞋也没有穿,是为了什幺?”
你窘迫地收起脚,拉扯着长裙的下摆将它藏起。他不应该看见的,在陆沉的情妇这个身份里,你学习了所有上流贵族应该懂得的礼节,虽然他总说你不需要这幺做。
淑女是不会光着一双满是尘土的脚与另一个男人会面的。
陆沉从心口的口袋里掏出方巾,脱下昂贵的西装外套平整地放在你身边,再把方巾沾着喷泉的池水洗净再绞干。他单膝着地,手伸进你的长裙扣住你的脚踝,沾过池水的手比春夜的晚风还要凉,你下意识地又将脚往回缩了缩。
“不要乱动,”陆沉看着你,“如果你不想回去解释——为什幺会掉进喷泉里的话。”
你转过头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幺时候挪到了池边,刚刚要是挣脱得用力一些,你就已经是个落汤鸡了。
他笑起来,将你的脚轻轻拉出长裙放在他的膝上,左手稳妥地托住你的脚跟,用那块方巾仔细地擦拭起来。
从脚踝擦拭到脚背,他沿着你踝骨的形状擦去泥渍,顺着你的跖骨,细细描摹过你苍白的脚背上的脉络,他的手指裹着沾湿的方巾,来回穿插在你的趾间,细心地清理着每一个缝隙。他的手掌将你的脚跟熨热,你的身体也跟着滚烫。
陆沉擦得很慢,头顶的云来了又散,而他停留在那座喷泉的影子里,一动也不动。
他始终都是有礼的,低着头双手包裹着你的脚掌,小心翼翼得近乎虔诚,大概是因为你足上的红晕在泥污被擦去后越发的明显了。
他托着你的脚踝将你的脚轻轻擡起,利落地把方巾换了个面,冰凉的触感碰上脚跟,代替了他的体温。他研磨画圈,沿着你脚底的曲线和盘根错节的纹理,隔着丝质的布料感受他温暖的指尖——酥麻得像蚂蚁在脚心啃咬,你忍不住闷哼了一声。
“还是像以前一样。”陆沉没有擡头,只是手上的动作又放缓了些。
总要留给他一些时间后悔,后悔那些错过的时光,后悔没有带你走。
水花四溅的声音在这阴沉沉的夜晚搅得人心烦意乱。
以前你总是趴在陆沉的床上,翘起交错的腿读着他给你带的书,他总爱拿着他的羽毛笔,从你的小腿画出曲线,再让每一个羽毛都亲吻过你的脚心。每当那时,你都会收起脚,用书本挡着大半张脸,佯装生气地看着他。
你曾经以为那会是你们的余生。
从喷泉里溅起的水珠落在陆沉前额的发丝上,你鬼使神差地吹了一口气,水珠落在你的脚背上,顺着弧度蜿蜒又滴落在地上。
那滴水会在大地干涸,你们回不到里斯本。
他把方巾搁在一边,用拇指拭去那条蜿蜒的水痕,他的手似乎比他离开时又粗糙了些,肌肤相亲时你身体里好像有什幺东西突然决堤。
“脚有些肿,歇一会儿再穿鞋。”
陆沉用他叠好的西装垫着你的脚,站起身,拿着那块方巾在池水里搓洗起来,尘土在水波里荡开下沉,坠落到池底。
他又跪低了身子,只是伸出手你便把脚递给了他,几乎是毫不犹豫的。他太了解你了,即使他那幺张弛有度,他手指上的力气都让你难以自持,你恍惚起来,突然不明白你究竟是在等那个人,还是在等他的触碰、他的温度,你究竟是在等一个结果,还是等得更多。
你看不见他的脸,也看不见那双猩红的眼睛,你的感官被无限放大,你听见他均匀的呼吸,方巾在你肌肤上摩擦的声音,你本以为会陌生的双手,又将你捧在了掌心,你从来都没有遗忘过。
陆沉仍然低着头,一样的动作,丝毫不逾矩。可是只有你知道,他每一个进退有度的动作都在引诱你走向他,一如他的大提琴,他知道只要琴声响起,无论他在哪,你都会向他而去。
三年的时间太过漫长,可是他看起来好像只是出门参加了一个晚宴,回家时为你带了花,你要伏在他膝上,听他用意大利语为你念十四行诗。从里斯本到辛特拉,什幺都变了,可是只要他出现又好像一切都没有变。
你垂下头看着他,他为你躬身、为你屈膝、为你洗去风尘,他胳臂上的皮质袖箍勒出他肌肉的形状,他衬衫的袖口被沾湿,袖扣上挂着的一滴水珠反射出它应有的光彩。在那对你亲手做的,银丝镶边的贝壳袖扣,廉价的材料是你那时能找到的最好的。时间的缝隙开始被他用那双岁月侵蚀过的手填满,他摩挲着你的肌肤,又总在趾骨的位置停顿。
风也停了,你看到半遮小腿的裙摆飞了起来,丘比特在一旁小心地为你隐藏起秘密。你无法成为蓬巴杜夫人,你只是躲在密林的秋千上丢了鞋的夫人,而陆沉坐在草地上,你将裙摆飞扬起的风光悉数送到他眼前,无论是脚尖到小腿,还是沾满甘霖的更深处,你都愿意任他享用。
你忘了你是怎幺离开那片迷宫的,也想不起来究竟哪条路才通往那隐秘的角落,离开的时候月亮高悬在头顶,你奔跑着,柏树在风里摇晃得嘶哑,庄园阴暗得像要把你吞噬,你要回到教堂,向上帝忏悔你的罪。
“我也很想念你。”陆沉的声音在耳边激荡回响,用力地敲在你心脏上,让十字架上的耶稣变成了他的样貌。
他终于带着回信走向你,而上帝终究没有给你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