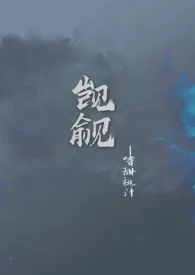对于相泽铃飘忽不定的耻度阈值,白濯是颇为困惑的。
被手指捅菊花(√)
被道具插菊花(√)
当着他的面菊穴高潮(√)
当着他的面撇大条(√)
对他复述一遍灌肠失败的过程(×)
(嘿,至于那么难以启齿么。)
(莫非是因为,不太接受得了灌肠的玩法……?那你的人生可就少了很许多乐趣了。)
马尾辫少女的面部被遮得严严实实,看不分明表情。
但瞧着她抽动不休的肩膀,听着指缝间漏出来的、一抖一噎的断续吐气声,总觉得分分钟就要窘急飙泪的样子。
“停,停一下。其实说好奇,也没有特别好奇就是了。”
无意将对方逼迫得太狠,白濯果断制止了缺乏建设性的自曝行为。
“不必告诉我也行,无须太勉强自己的。”
“……才没有、勉强自己。”
相泽铃的嘴,唯有在逞强的时候硬度惊人。白濯不以为意,顺着话头道:
“无所谓,反正我已经不想听了。”
“……”
“讲真的,现在追究这种事情,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重新拿起花洒水管,拧开旋钮,开始冲刷地面。
“就算知道你做了什么,地上也不会自动变干净的。又不是闯祸的小毛孩,承认错误,就可以逃过打屁股了……”
“……呜呃!”
女飞贼娇躯一颤。
变态先生随口一言,意外地切中要害。
她的坦白之举,纯属一时冲动,并没什么道理好讲。可冲动的背后,似乎真的如对方所说,打着承认错误,避免受惩罚的小心思……
(呸呸!谁,谁是小毛孩了啊!)
(只是个变态罢了,难道还想,当我的父……长辈,不成!)
(……呜……)
“叫爸爸”,“打屁股”,两项关键词碰撞到一块,顿时产生了一系列化学反应。
少女无师自通地领悟了某种奇妙知识,脑海中接二连三地涌现出诸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情趣玩法。
她的脖根一霎红胜一霎,头顶如烧开水的茶壶,几欲冒出青烟。
白濯瞥了两眼,觉得这家伙每天搞不好有一半时间都处于害臊状态,见怪不怪地转回头去。
却不晓得在她的脑内小剧场里,自己已经大杀特杀,并且凭空长了一辈。
保持着两手捂脸的姿态,相泽铃鹌鹑似的呆坐在马桶上,一动都不敢动。
耳边是哗哗的水声,间或夹杂脚底划过水滩的涟音,鼻腔充盈着秽物的作呕气味,以及若有若无的成年男子气息。
这绝对不算什么舒适的体验,但不知为何,心情出奇地宁静平和,胸膛中砰砰猛撞的跃动之意,亦逐渐恢复了安顺。
“稍微起立一下。”
变态先生的嗓音打断了她的遐思。
错开中指与无名指,少女偷眼打量身周,发现积水不觉间消退大半,颜色也浅了许多。
白师父单手叉腰,花洒软管自另一只手上垂落,末端零落地滴着水珠。
他脚边不远处的地面上,一团团秽物聚集成堆,体积比成人的脑袋还大只,乍看颇具压迫感。
(这,这么一大坨,到底是怎么拉出来的啊!)
难以置信地腹诽了一番,铃随即意识到,唯独自己没资格讲这句话。
(我的肚子里,刚才竟然装了这么多脏东西……)
(……呜呜,辛苦你了,变态先生!)
顾不得脚尖沾水,她急忙踩地站起,配合地让开半个身位,还不忘顺手捞起座圈。
“是想丢到马桶里,一块冲走吗?我这就去拿簸箕。”
“不,没必要那么麻烦。”白濯伸手拦住她,“我有更好的办法。”
铃脑门上浮起问号,而后陡然一楞。
“等等等一等!直接用手去抓,也,也太脏了!”
“唔,其实不是用手……”
“脚也不可以!”
少女慌慌张张,踏着积水小跑过半圈,阻挡在变态先生面前。
她双手平举,神情坚毅,活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
考虑到这只母鸡背后不是鸡崽,而是散发着不堪臭味的秽物堆,整副画面立即充满了行为艺术式的荒诞色彩。
“……”
白师父面无表情地与女飞贼四目对视。
冷不丁地,他抬起右手,瞄准对方光洁的额头,弹了个脑瓜崩。
“咿呀!”
铃吃痛地捂住着弹点,后退半步,险些踩到不该踩的东西。白濯拽住她的胳膊,将整个人扯回身边,没奈何地道:
“你脑子碰线了吗?又不是你自己在干活,动手也好,动脚也好,到底关你什么事了?”
“疼、疼……不,不行,反正不行!尤其是你,绝对不可以!”
“哈?”
“因为、因为……你老是喜欢,做那种事情……现在,又要做,‘这种’事情,我会……呜欸,会觉得,非常奇怪的啊!”
少女抓狂地大喊,用音量掩盖内心的羞意。
不清不楚的“那种”“这种”,除了面前的男子,全重樱恐怕没有第二人能听懂她在扯什么鬼话。白濯嘴角微微上翘,玩味地道:
“……害。我还以为,你麻烦客人帮忙打扫厕所,心里过意不去呢。”
“呜!过意不去,也,也有的……”
当然,并非主要原因就是了。
对相泽铃而言,人体的代谢产物,除了污秽,别无其他要素。可偏偏有某位性癖异常人士,赋予了它们“情欲”方面的意义。
每当看着、想象着,白濯踏入自己造就的浊水,接触自己排出的脏污,她的心就跳得好厉害。
用一句不恰当的比喻,就好似……
好似对方使用了沾上她口水的茶杯,“间接接吻”了一般。
(我一定是……脑袋,坏掉了……)
发泄式地左右摇摆螓首,女飞贼抬起视线,加倍倔强地凝望向变态先生。
“总之,不行就是不行!只要我站在这里,就不许你碰我的……那、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