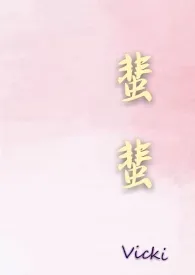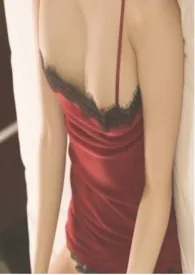官路之上,一列车队缓缓而行。
当前一匹高头大马之上端坐一人,身形秀美,头戴宽大黑色斗笠,身披红色织绒斗篷,胯下一匹枣红大马,鞍辔上悬挂着一柄翠绿宝剑,脸上轻纱覆面,一双媚眼春水横流,遮掩之下更显动人。
秋风萧瑟满地金黄,衬得女子更加艳丽动人,她催马前行,行走间被风拂起面纱,露出轻纱下秀美容颜,唇红齿白,面容姣好,正是云谷县城陈家寡妇应氏应白雪。
落叶被马蹄踩踏发出悦耳声响,应氏纵马而行,一马当先登上一处高坡,远眺望去,远山含黛,满地秋凉,回首看处,车队蜿蜒行来,十三辆马车缓缓而行,两队兵卒分列车队前后,十几个镖师散在车队之中,倒是戒备森严、张弛有度。
一辆驴车行在车队之后里许,车厢破旧不堪,看上去极是穷酸。
应氏勒住缰绳,一直等到车队慢慢过去,这才驰马下坡来到驴车跟前。
听见马蹄声响,车窗布帘撩起,一个英俊少年探头出来,正是书生彭怜,他轻笑问道:“原来竟是夫人到了,吓了小生一跳。”
应氏见他言语轻薄,不由心中一荡,抛个媚眼过去,余光瞥见车中女儿正在为情郎舔舐阳根,不由更加心荡神驰,只是笑道:“公子不会骑马倒是颇为遗憾,否则如此秋日纵马奔行却也是一桩美事!”
彭怜故意身体后仰,露出车中泉灵样子,只是笑道:“此间却也别具趣味,有劳夫人惦记,若是骑行疲惫,不如也来车中休息片刻如何?”
应氏心中千肯万肯,只是前面坐着车夫,便是进了车厢,怕也不能弄出声响,总不能再次杀人灭口,她摇头轻笑,口唇微动无声轻呼“相公”,而后说道:“晌午前后过了风鸣峡,稍行不远便到宿头,再往前便是一马平川,不用担心劫匪强人了……”
彭怜轻轻点头,妇人言下之意,一路上最凶险所在便是风鸣峡,据应氏所言,那处地段两边皆是高崖深林,地势险要又是商队必经之路,平常盗匪尽皆在此出没,有此一端,峡谷两端两座县城不知借此养活了多少绿林豪杰、江湖人士。
应氏故布疑阵,车队弄得声势浩大,其实真正贵重之物皆在这架破旧马车之上,相隔里许之遥,便是前方遇险,彭怜陈泉灵亦可全身而退。
应氏心知,以彭怜本领,若是搏杀经验丰富,怕是自己都不是他十合之敌,有他相伴,女儿安全自然无虞。
只是江湖险恶,生死之间并不全以武功高低论胜负,绿林中人剪径,从来不必光明正大以武服人,她心中始终放心不下,因此仍是不时驻马照看。
“当日少夫人归乡省亲也是这般兴师动众么?”
见彭怜问起,应氏双手叠放马鞍之上淡然笑道:“她轻车简从,不过几箱书画傍身,便有盗匪,却也抵不过护佑镖师……”
“若是我等也是这般,岂不免去许多烦恼?”
应氏轻笑摇头:“便不携带这些贵重器物,府里家人丫鬟总要二三辆马车,随行带些细软和日常用度之物,一来二去便也为数不少……”
“便是明知财物不多,有那居心叵测之人,也不肯我母女生离此境……”
彭怜轻轻点头,陈家族里对应氏搬家之举持异见者颇多,族长得了好处缄默不言,旁人却不知其中就里,应氏母女婆媳一走,搭好的牌坊名存实亡,实在称得上族中奇耻大辱。
“坊间已有传言,有人买通盗匪,欲取我等性命,还有人说山中盗匪已然合流,目标便是我们母女……”应氏轻轻摇头,吩咐车夫说道:“车速再慢些,缀后一里便可。”
车夫年岁不小,连忙点头答应。
彭怜端坐车中,身边放着一柄长剑,身前泉灵小姐跪在锦垫之上为他含弄吹箫,听母亲马蹄声远,不由吐出阳根问道:“既是这般凶险,母亲为何还要这般兴师动众,纵有亿万家财,若是无福享受,不也毫无意义?”
彭怜轻抚少女面颊,低声笑道:“你娘并非贪财之人,她这般安排,自然有其深意……”
见泉灵不解,彭怜便解释道:“自来恶人欺侮,好人都要退让忍耐,所谓避其锋芒,大概便是此意,然而恶人不除终究为祸绵延,若能拔而除之,却好过时时退让……”
“你娘既有此番布置,定然已是胸有成竹,你且安坐便是,不必担心。”
泉灵知他暗示何意,继续舔弄片刻,这才微笑问道:“早间倾城姐姐过来相送,却与母亲极是相得,我还道她们要有些纠纷呢……”
彭怜轻声一笑,低声说道:“你娘诸事劳心,哪里还有心思与人争风吃醋?等到时过境迁,你再看她如何不迟……”
两人车里亲热说笑,不多时前方车队已到风鸣峡,应氏吩咐下去整顿车马加强戒备,这才一马当先催马行入峡谷。
峡谷两侧遍布密林,几处高崖俯瞰深谷,埋伏下数十盗匪不过轻而易举,应氏策马而行,细细观察各处险要所在。
行至峡谷中段,只见远处山林树枝微动,应氏呛啷一声宝剑出鞘高举,神情无比戒备看着远处高坡。
“嗖!”一声箭鸣响起,应氏侧倒马鞍一旁堪堪躲过飞来箭矢,回首看去,车队之中已有家仆中箭。
“敌人持有弓弩!到岩石后面躲避!”应氏高呼一声,飞身躲到一处石坡后面,弓弩乃是管制之物,寻常盗匪莫说无法买到,便是买了怕也没有这般精准,应氏情知对方箭矢数量有限,此番偷袭只是开胃小菜,正餐还在后面。
果不其然,箭矢未绝之时,山坡之上冲下数十滚石,当先一个击中一架马车车辕,断木崩碎,恰好将一家仆穿透胸膛;一颗滚石撞在一处凸起之上腾空飞起,直将一个镖师头颅撞碎。
受伤之人惨嚎声中,山坡上忽而杀声四起,却见数十道人影从树丛中闪露出来,借着山坡形势冲锋而下,盗匪们皆是皮麻服饰,脸上神情凶恶,若是平常百姓见了自然吓得半死,自然不敢轻易反抗。
车队中人,一应家仆婢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只是躲在车厢附近不敢露头,那些镖师倒是神情镇定,各个擎了武器在手,准备与敌人厮杀。
两队兵卒早已整列队形,手持长枪严阵以待,丝毫不在意对方如何人多势众,气势沉凝稳重,绝非平常江湖人士可比。
“白指挥!对方不是寻常恶匪,叮嘱兄弟们小心!”应氏大声呼喝,背对山石后退数步,待对方冲势力竭,这才挥剑上前缠斗。
盗匪人多势众,漫山遍野喊杀声极是吓人,家仆婢女吓得面无人色不敢出声,偶尔被那盗匪突入人群,便有一两人惨遭屠戮。
两列兵卒汇合一处,迎着山势将车队护在身后,盗匪不敢直撄其锋,便调转刀口专攻那十数名镖师。
那些镖师各个勇武,却并无多少协同配合,被盗匪急攻之下,不多时便有数人殒命。
应氏身形起落翩若惊鸿,她心智冷静果决,阵上经验丰富,用上彭怜那日所授剑诀,进退转圜间已杀伤数人,远远见此情形,一剑斜劈虚晃,而后抽身而退加入镖师队伍,呼喝进退,顿时改变颓势。
盗匪们见久攻不下,不由慌乱起来,此消彼长之下,被那兵卒长枪先后挑翻数人,不由军心浮动,便要一哄而散。
匪徒斗志将散未散之机,山坡之上号角声响,十数骑士呼喝而下,马上之人各个高举斩马长刀,威风赫赫、声势迫人。
那几名镖师何曾见过这般阵势,平常山里盗匪剪径不过喊打喊杀,一些大的镖局商队甚至找那中人提前打点,如此生死相搏却是从未见过。
盗匪虽是恶徒,却也皆是贪生怕死之辈,能够躺着赚钱喝酒吃肉,谁也不愿舍生赴死,便是陈家车队如何富庶丰饶,这般卖命也是莫名其妙,如今又有骑兵助阵,却更是从未见过。
自来马价昂贵,寻常糙马还要十数两银子,若是应氏所骑那般高头大马,怕是要百两银子上下,单是购买已然如此昂贵,日常豢养更是一笔不菲开支,山中盗匪便是抢来马匹也要早早卖掉,根本不会蓄养骑兵。
那些兵卒皆是精挑细选厢军老兵,不少人真正上过战场,见那骑兵冲来,早已各自躲避,好在山下岩石众多,只有数人被骑兵冲散砍于马下。
镖师们却没那么幸运,慌乱之下被骑兵冲入人群胡乱砍杀,不多时便死伤数人,剩下几人躲到兵卒队列之中才得幸免。
仆役丫鬟死伤亦是不少,翠竹珠儿随彭怜同车,其余人等却没那般幸运,幸存之人躲在车队后面草丛之中,看着眼前修罗场景,俱是吓得面无人色噤若寒蝉。
应氏无暇他顾,飞身而起将一名骑兵刺死,躲过身后刺来长枪,一个倒地滚身逃到车厢下面,随后翻滚而起从另一边飘身跃起,将一名盗匪手臂砍下,鲜血淋漓,将她溅得面目鲜红。
众人正自酣战,远处喊杀声起,应氏不由眉头一皱,情知有人袭扰彭怜所乘马车,情急之下却抽身不得,心中关切之下,不由心慌意乱起来。
她剑法微乱,战阵之中被一名骑兵长枪刺中臂膀,心神不由一凛,暗道若是心有旁骛,别说顾不得情郎女儿,便是自己也要横死当下,心中定念,应氏收摄心神,专心致志与敌搏杀起来。
残余镖师早已丧了胆气,兵卒们也有些疲于应付,那白指挥使挥刀砍倒一名盗匪,挤到应氏身边小声说道:“夫人!对方人多势众,这样力抗不是办法!”
应氏舞剑刺瞎一名盗匪,大声回道:“此处地形于我等有利,若是溃散,只怕难以幸免,你且吩咐弟兄们坚持下去,一会儿便有援兵到来!”
“这里杀声四起,如何能有援兵到来!”白指挥使年纪不小,以为应氏故意提振士气,心中暗自腹诽,却也大声喊道:“弟兄们坚持住!援兵已在路上!莫要散了阵型!”
山坡一处大石之上,四人并排而立,看着山下杀得人仰马翻,听见应氏这般叫喊,其中一名枯瘦男子皱眉说道:“若是真有援军,只怕于我等不利……”
“五爷莫要多虑,若是真有援军,暗桩自然早就飞鸽传书,岂能等到此刻?”男子一身书生装扮,看着山下厮杀,不由拈须得意微笑。
“幸亏五爷借来这十六匹良驹,不然仅凭我手下弟兄怕是难以成事。”
枯瘦男子点头说道:“确是这般道理,却是不知驴车那边情况如何?”
“车上不过书生小姐车夫三人,王良一人其实便已足够,又有五爷手下相伴,自然万无一失!”男子胸有成竹说道:“果然如同五爷所料,那应氏用了李代桃僵之计,虽然算是好计,只是遇到薛某,却要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也!”
说话之间,却见远处山路之上数人四散奔逃,其后一人手持斩马刀纵横来去,身形竟是迅捷无比,将几人一一砍翻之后,径自朝着山顶大石奔来。
薛姓男子不由面露惊讶之色,问那枯瘦男子说道:“这个少年是谁?竟能将王良众人屠杀殆尽?五爷你可是对薛某有所隐瞒?”
枯瘦男子便是陈家族长,他此时也是惊骇莫名,他将随身五名亲随交予那匪徒头目王良去擒拿马车上彭怜泉灵、收缴应氏财物,谁料竟然被彭怜反杀,这会儿看着彭怜提刀而来,自然吓得心胆俱寒。
陈五与应氏定下协议,却耐不住族人撺掇,要将应氏一家尽数屠戮,若能人财俱得自然最好,若是不能,也不肯让应氏就此离去,他使了大把银钱撺掇几伙盗匪汇聚起来,又雇佣一些退伍士卒,务求将那应氏一网打尽生擒活捉。
谁知千算万算,竟不知少年彭怜也如应氏那般是个杀神,屠戮六人竟然犹有余力,直朝自己这边扑来,看着杀意汹汹,实在来者不善。
薛姓男子虽慌不乱,挥手吩咐说道:“你二人过去结果了那少年性命,到时论功行赏,你二人算个头功!”
“大哥放心,看我兄弟二人取他项上头颅!”身后二人虎背熊腰,一人提着双锏,一人擎着长枪,一同飞身跃下大石来战彭怜。
彭怜腰间佩剑,手上倒提着抢来的斩马刀,眼中凶芒暴起,与二人厮杀起来。
他方才与人动手,因为经验不足,被一人刺伤胸腹,堪堪躲过要害部位,却也流了不少鲜血,此刻身上银白衣衫被鲜血浸透,看着却也极其瘆人。
眼前二人能被匪首留在身边护卫,想来自然武艺高强,一试之下果不其然,比之方才众人,确实强出不少。
彭怜收摄心神,将那厚背长刀舞得刀光赫赫,他修为精湛,所缺不过对阵经验,旧日闲来所习刀法历历在目,生死之际用将出来,却是事半功倍,连杀六人之后,已是颇有心得。
只是他不曾与人对敌,不知如何应对长枪铁锏,若非方才那几人持刀拿剑,他也难以轻易得手,此刻被二人夹攻,不由捉襟见肘起来。
慌乱之时,却听远处马蹄雷鸣声响,薛姓男子不由眉头紧锁,神情顿时慌乱起来。
陈五一眼望去,却见府城方向官道上驰来一队骑兵,奔驰之际带起道道烟尘,声势浩大,显然人数不少。
手下不在身边,薛姓男子自己捡起铜锣敲打起来,山下盗匪听见锣响便即一哄而散,狼奔豕突便要夺路而逃。
只是骑兵来势甚急,须臾已到近前,那些盗匪慌乱逃跑,有的被骑兵追上砍下头颅,有的被应氏等人拦住斩杀,局势急转直下,不过呼吸之间。
薛姓男子眼见大事不妙,转身便朝山上爬去,哪里顾得手下如何?陈五见状也是吓得半死,跟着薛姓男子一同逃窜去也。
彭怜正自左支右绌、应接不暇,却见二匪无心恋战便要脱逃,不由大喝一声奋起精神,一刀猛劈斩断长枪,长刀余势不竭,砍入匪徒肩胛,而后抽刀不成,便掣出长剑去追那用锏匪徒。
山下应氏脱出战团,急速奔行过来,将那持锏恶匪拦住,与彭怜双剑呼应,几个起落之间,便将那人一剑刺死。
彭怜初经战阵便杀伤众多,此刻面色苍白几无血色,看见应氏无恙,不由心中欢喜说道:“雪儿可曾受伤?”
应氏轻轻点头,看彭怜衣衫带血,也自关心问道:“相公伤的重么?”
彭怜摇头,应氏又道:“可看到匪徒首脑了么?”
彭怜长剑一指说道:“朝那边去了,追是不追?”
应氏面容微冷,“既是图穷匕见,自然除恶务尽!相公且随我来!”
她大氅早已脱落,此刻举着宝剑急速奔行,彭怜随后相随,想及眼前妇人床上妖娆,阵上却有如此风采,心中不由更是热爱不已。
两人俱是习武之人,虽是透支过度,步伐依旧轻快,尤其应氏自觉比之当初年轻之时更加精力充沛,心中默默感激情郎回春之功,几个起落之间便赶将上去,一脚将那陈五踹翻在地。
彭怜后来居上,飞身跃起落在匪首身前断住去路,扬手便要取他项上人头。
应氏连忙出言制止,“公子且慢!留下这二人性命扭送官府发落!”
彭怜收回长剑,一脚将那匪首踹翻在地防他逃跑,却听应氏旁边对陈五说道:“妾身想过陈家会有人不甘心,却没想到竟是叔叔亲自前来……”
陈五眼中流露出狠绝之色,冷声说道:“陈某顾念家族脸面行此险棋,成王败寇自是无话可说,你且与我扭送官府发落便是!”
应氏一愣,随即笑道:“倒是妾身想差了,叔叔身为族长,自然与州府官员有旧,若是投进府衙,只怕定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到时再来袭扰,岂不反而不美?”
陈五听她叫破自己心思,不由面现惊恐神色,却听应氏说道:“黄泉路远,叔叔抓紧上路,妻儿老小,想来族里亲戚善良和睦,定然能够照顾妥当!”
话音刚落,剑光骤起,陈五咽喉泛出汩汩鲜血,双目瞪圆指着应氏呛咳不已,随后气息断绝殒命当场。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匪首伏地扣头,口中连声求饶,“小人什么都不知道,都是陈五教唆,还请女侠饶命!”
应氏冷冷一笑,轻声说道:“本想留你活命送官审讯,如今看来却是留你不得!纳命来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