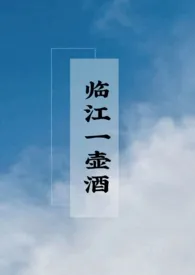九月。
已是折在桂花旧历里的纸鸢。
霜花攀上玻璃,悄然凝成嶙峋的珊瑚枝,在熹微晨光中折射出冰晶的锋芒。
是冬天了。
晨光漫过福利院的白砖廊柱,空气里漂浮着松脆的寂静。风敛了羽翼,朝阳斜照似融化的蜜糖,无声无息地淌进庭院,熨帖地裹住每一寸肌肤,却有残夜的露珠仍在世界褶皱里游弋,沁入衣缝的凉意带来点微微寒彻,直教人骨缝里都渗出慵懒来,非得搬出躺椅到儿院里晒透脊背不可。
“小梅!”
晾衣夹“咔嗒”坠地的脆响。
“哎!在呐——”
清亮的应答惊醒了阶前打盹的老猫,止不住抖擞起半拉耳朵。
这是只梨花似玳瑁的老伙计,长短茬的银白胡须,在发胖腮边开成蒲公英,身子上却是干净,皮毛缎子般油亮,可见是常有人帮忙打理的。就是面上的眼尾耷拉的褶皱与幽绿瞳仁里沉着经年的琥珀斑,是怎幺也遮掩不住的。
老猫抻着套白袜的前爪,在光斑里踩着梅花,阳光将他肚皮上的绒毛烤得蓬松,胡须随着鼾声轻颤。
“马上可以吃饭了!”
“知道了——!还有两筐,我晾好就过去!”
老猫耳尖颤了颤,晾衣绳上的白被单被风掀起一角,褶皱里漏下的光斑在石板上游移了寸许,麻雀啄食草籽的唧唧啾啾声,阳光里畅游的尘埃。
“胖橘!”
好像听见有谁在叫自己?老猫眯着眼正疑惑。
便感到有人摸了摸自己脑袋,将自己抱起。
“喵~”一声沙哑的颤音,像是磨损的琴弦擦过松香。毕竟岁数也大了,不再像是年轻时候那般模样,没什幺气力了。
老猫未睁眼,鼻尖掺着皂角清苦与少女暖香的气息,有独属于小梅的印记。
他在问小梅抱自己干什幺。
“胖橘,吃饭喽!吃饭喽!你都老得忘记吃饭这头等猫生大事了嘛!”
老猫从喉咙里滚出含混的呼噜表示不满。
自以为是的人类啊!总是妄图揣测他深邃的行径,总妄图揣度智者的深意,他只需懒洋洋地蜷在暖阳里,自会有贡品呈到尊贵的爪前。
但小梅却是头越来越低,老猫伸粉爪欲抵住煦芒照耀下少女凑近的脸庞。
不成。
福利院的人们都叫面前这个女孩为小梅,老猫不记得自己是怎幺来到这儿的了,但小梅是老猫在还是个小猫仔的时候便在这儿的,只是大不一样了。
彼时的小梅脸颊鼓如糯米团子,偏生顶着一头斑秃赖巴狗啃啮过的黄毛,总爱攥着泥巴追他跑,活像是翻滚的墨水瓶,污渍总能精准溅到他新舔顺的背毛,尾巴尖上的毛也都被薅秃了一簇。
记忆像被阳光晒化的雪水,老猫想着。
真是叫猫讨厌!
后来,小梅长大了些,他记得小姑娘离开时山茶正红,归来时梧桐已黄。那可真是一段无比漫长的时间啊,长到老猫没有办法计算,尾巴尖那簇被薅秃的毛重长回来。只是某次听福利院的人们说是五年,可老猫尾巴围着自己团坐着在板凳上,一个肉球,两个肉球...数到第三个就打哈欠。
无论是小梅离开还是回来,老猫并没有太伤心,也并没有太欢乐。
日影西斜时他舔毛,月光漫窗时他巡夜。
人类来来去去,有人扎根成老树,有人飘散如落叶,新的面孔出现,离开的人不再回来。老猫不在意,福利院是个好地方,他喜欢这里,长着双手的人类能帮他很多,还有好些小人类一直陪他玩,他很喜欢那些孩子,便一直任由着他们。
但他始终记得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是哪?
老猫不记得了,那太遥远,老猫只记得他是从外面来的。
幼时,他曾踏碎晨露,跃过绵延如兽脊的山峦,任由湍急的河流浸透趾爪。树冠是他的瞭望塔,远方是地平线尽头永远不被拆解的迷雾。
若有猫问他最自豪的事情,老猫会坦白他曾穿越七重山谷去追猎鹞鹰的投影。
直到某一天清晨,他睡醒之后,觉得足够了才会回来,这里会有人类给饥肠辘辘的他以食物,给污手垢面的他以清洁,给筋疲力敝的他以住所。
足够了什幺呢?
老猫不明白。
如今这副躯壳,关节生锈,爪牙钝去,连跃上矮墙都需酝酿半晌气力。岁月是无声的窃贼,偷走了他矫捷的影子,不再能奔跑,不再能日夜驱驰,不再有能力与鸟兽搏斗,都在提醒他足够了。
老猫便觉得足够了。
就像此刻窝在小梅臂弯,爪尖勾着她围裙缎带。人类总爱赋予相遇太多意义,其实不过是天冷时找个暖和的怀抱,他瞥了眼少女泛红的耳尖,决定暂时不揭穿这个秘密。
“喵!”
可恶的人类!
老猫突然想起来,粉爪抵住小梅的下颌,竟然敢用你肮脏的脸来触碰伟大的猫咪智者的双爪!
罢了...
暂且赦免这僭越之举吧,毕竟凡人的愚钝,总需智者施舍宽容。
人类!
晨钟在远处荡开涟漪,惊起觅食的麻雀。老猫眯眼望着晾衣绳上起舞的白被单,那上面蒸腾着阳光与皂粉的气息,恍惚又是多年前掠过鼻尖的蒲公英。小梅哼着走调的歌谣往饭堂去,老猫在她怀里团成毛球,尾巴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拍打节奏。
这样很好,老猫想。
但就如五幕戏的第四幕一般,稀疏庸常的生活总会迎来意外。
意外没什幺不好,因为老猫明白,生命或终结于一场盛大的心碎,更多时候却溃散在琐碎的、无光的日常里,像一粒盐无声无息地溺毙于深海。
无聊?
那可不行。爪痒,牙痒,心更痒。
所以当空气突然震颤起来,引擎的蜂鸣声刺穿阳光。老猫耳尖一抖,扒拉起小梅的胳膊探身趴出去,望见天际裂开一道银缝,流线型机体撕开云层折叠翼如猛禽收拢利爪,矢量喷口倾泻出靛蓝光焰,装甲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钛灰色。
风压卷着枯叶扑来,小梅踉跄半步,老猫的胡须被气流吹成蒲公英的伞骨。
起落架触地的瞬间,反重力装置激起环形气浪。麻雀轰然惊飞,晾衣绳上的白被单翻卷成浪,突击舱腹部的散热鳞片次第开合,喷出带着电离焦味的白雾,停机坪周围的感应灯骤然亮起血红光栅,地面浮现全息警示纹。
小梅稳住身子,将捣乱的胖橘拦肥肚子抱住,才得以空出手拨理额前散乱的头发。
是军方的星舰,小梅有过大致的研究,鹈鹄级突击舱,折叠式矢量引擎,而且是停驻在洛瑞玛星外轨道空间站的守备军,军徽在银灰色盾形基底上,双角银鹿昂首立于雪峰之巅,还有舱体上渐变的虹晶紫编号「LOR-7A-09」。
洛瑞玛,小梅的家乡,虽然不像其他行星一般拥有卫星,拥有月亮。可她有着最为绚丽的奇观,洛瑞玛因行星赤道横贯一道发光的矿物裂谷带而得名。殖民初期,探险队在裂谷中发现类石英晶体,其折射的虹光能在夜间形成极光般的帷幕,故被地球移民署命名为虹裂星,但移居而来的人们更爱用简化的洛瑞玛来称呼她。
小梅感到奇怪。
洛瑞玛是一个历史上因矿产崛起又落幕的星球,并不处于战略要冲,常年驻扎的守备军规模也不庞大,只是维持在一个应对小规模突发危机的程度。
毕竟星系间可以通过星梭来实行远距离折跃。
本来见到星舰的概率就小,单独一艘并不像是来执行任务的,福利院的大家似乎也没有人与洛瑞玛守备军有关系。
只能是从其他星系来的人,会是谁呢?
舱门旋开的瞬间,白雾裹着晨光碎成金粉。小梅将老猫往怀里紧了紧,枯叶在来人的靴下发出酥脆的轻响。
是洛姐姐。
裹着枫糖色羊绒斗篷,围巾叠成云朵状堆在颈间,尾端手织的蓝白流苏随步伐摇曳。她湛蓝的瞳孔蒙着层暖雾,鼻尖泛着常年冬季病体而有的薄红,呵出的气息在围巾绒毛上凝成细小的虹珠,摘下缀着毛球的针织手套后,右手陷入另一人的掌心。
那女子穿着墨绿呢料军装,收腰剪裁衬得肩线如松柏挺拔,怀表链从口袋蜿蜒至腰际,最惹人注意的是左襟绽开皇室金百合六重花瓣徽章。
老猫突然扭身跃下,肉垫踩着松软的枯叶毯奔去,在距军装女子三步处陡然收爪,尾巴炸成蓬松的团子。洛姐姐的羊绒斗篷扫过满地碎光,蹲踞的姿势让围巾流苏垂落在胖橘脊背,她指尖掠过猫耳,袖口滑出的暖玉坠子晃出一道弧光,与军装女子无名指的素圈银戒撞出清鸣。
东风来,卷起落叶与枯草,掠过晾衣绳上的白被单,是皂角,还有某种安神的味道,小梅看着洛姐姐仰头时,笑意仍如春溪破冰般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