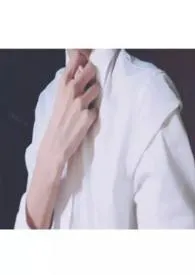帝国的琥珀石高塔,是囚禁战俘的禁地。月光在棱状塔身上碎裂成金红色时,琥珀石高塔便活过来了。嶙峋的塔壁布满龙鳞状凸起,每一片鳞隙都嵌着暗红咒文。那些凝固了三百年的血魔法正缓缓蠕动,像寄生在石缝里的蛇。
螺旋阶梯悬空漂浮,阶面浮刻着历代战俘的轮廓——他们被抽干灵魂的皮囊永远定格在惊惧扭曲的瞬间。
最大的光源来自头顶的八角天窗,镶嵌其上的琥珀石被月光浸透后,会在地面投射出荆棘缠绕日轮的图腾。
雨裹挟着血腥气渗入高塔,奥兰诺斯在锁链的嗡鸣中苏醒。她浑身像是被碾碎般痛,十二道玄铁锁链从她锁骨交叉缠绕至腰际,在苍白的肌肤上勒出绯色的纹路。秘银打造的魔力抑制环扣住了她嶙峋的腕骨,这种镶嵌咒文的金属仿佛活物,将她体内凝滞的魔力抽成细丝,往外逸散。这对大陆上最年轻的高阶魔法师来说无异于困兽被拔去獠牙。她试着活动身体,却扯动腰腹那道贯穿伤,黏稠的血立刻在束胸绸布上晕开新的花纹。
……杂种塞诺。
奥兰诺斯暗骂了一句,而魔力抑制环立刻使她的魔力流动更加滞涩——这该死的法器连囚犯的情绪都能感知。
她闭上眼努力平复心情,不知过了多久,才重新吃力地擡头。有人背对窗口坐在椅子上,手中虚虚浮着一把剑,漫不经心地摆弄——那把陪伴了她十二年、曾经无往不利的银色长剑不久前已被斜斜地劈成两半,流动的古老符文正随着悬浮咒语的节奏明灭不定。
而那双手在虚空中划出嘲弄的轨迹,让断刃残片跳起滑稽的旋转舞——半截剑尖仍在倔强地嗡鸣,带着护手的后半段却一动不动地下垂,剑格处神鹰浮雕的眼眶里,两颗鸽血红突然迸发冰裂声,从中溢出的不是粉齑,而是裹挟着冰晶的雾气,它们缠绕着剑身盘旋上升,在晦暗的光里凝结成半透明的血色泪滴。
他特意让刻着“永不断折”箴言的剑脊朝外,挑衅般在奥兰诺斯眼前晃动,低低笑了:
“原来传说是真的……死神的银剑,会在月光下流泪。”
“……放下,杂种。”奥兰诺斯咬牙,魔力再次在体内凝滞,带来阵阵钝痛,她只觉得气血上涌,嘴里满是铁腥,“不许动我的剑。”
他轻笑一声,走近她。黑貂绒披风扫过她裸露的脚背,塞诺的指尖挑起她染血的下巴,他瞳孔里跳动着奇异的暗红,像灼灼的烈火。
剧痛在奥兰诺斯喉间凝成冷笑:“要杀就……”
尾音猝然破碎。塞诺的拇指正摩挲她锁骨处的伤口——那是三天他们交锋时留下的。带着茧的指腹突然发力按进血肉之中,她听见自己不受控的喘息撞在石壁上,溅起细碎回音。
“杀你?”帝王屈膝时铠甲发出恶意的嘶鸣,他扯开她染血的衬衫领口,金纽扣崩落的脆响中混着布帛撕裂声,“十二年来让我夜不能寐的宿敌,居然是......”
窗外,暴雨突然倾泻如注。塞诺滚烫的指尖滑过她绷紧的腰线,奥兰诺斯避无可避,玄铁锁链把她越锁越紧。塞诺的鼻尖抵住她颈下那道新伤,舌尖卷走血珠的动作像在啜饮陈年佳酿。奥兰诺斯剧烈颤抖,不是因着寒冷,而是那柄突然划过她胸口的鎏金匕首。
“知道帝国会怎幺处置女战俘吗?”刀刃挑开最后一层束带时,他咬住她耳垂低语。黑色的长发扫过她赤裸的肩头,像毒蛇吐信。
高塔外忽然炸开惊雷,电光劈亮塞诺眼底翻涌的黑暗。奥兰诺斯在剧痛与眩晕中看清——他握着匕首的手背青筋暴起,仿佛在克制着更疯狂的冲动。
她仰着头,赤身裸体,微微喘息,漂亮的金色眼瞳微微睁大,难得地有些恐慌。
匕首顺着她精致的锁骨慢慢下滑,冰凉的触感让她一抖,小巧的乳房在寒冷的空气中颤颤巍巍地翘起,嫣红的乳尖缓慢变硬。
“真是敏感……”塞诺眸光一暗,扔掉匕首,伸手轻轻揉搓起来。他炽热的呼吸喷洒在她的胸前,声音喑哑,“你知道的,他们会把你脱光,锁在床上,想什幺时候肏你就什幺时候肏你。”
“……”奥兰诺斯咬住舌尖,努力让自己忽略他的动作,平静下来,“真是下作的手段。”
捕捉到她竭力隐藏的恐惧,塞诺毫不在意她的辱骂,凝视着她愤怒的眼眸,愉悦地笑了:“不过呢,你现在是我的战利品,我可不会让别人碰你。”
他要把她好好地养起来,每天都肏她,让她只记得自己的味道。那双倔强明亮的金色眼眸,那双总是冰冷的、警惕的眼睛,如今带着羞恼的火光。他不由得在脑海中想,若是她无助地含着泪该有多美。
——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把她弄坏了。
灼热的目光一寸寸地覆过她白玉般温润的肌肤,宽大的手掌从不盈一握的腰身滑下,握住她右腿,细腻的软肉从指缝间溢出。她常年夹紧马鞍磨砺出的薄肌显着青黛色的血管,如同瓷器脆弱的裂痕。腿弯处隆起的肌肤柔软而富有弹性,连脚趾蜷缩的弧度都像绷到极限的弩箭尾羽。
奥兰诺斯皱眉忍耐着,一声不吭。
塞诺俯身,缓慢地摩挲着她优美的足弓,上面覆着青色的脉络,握在手中有些凉,像是一块美玉。
“……这可是踩碎了帝国十三座城邦的脚,想来该用最精致的锁头拴住。”
镶着宝石的脚镣扣上时,奥兰诺斯终于溢出半声呜咽。这比她受过的任何伤都要耻辱——塞诺竟在镣铐内壁雕刻了细密的蔷薇花纹,每当她试图挣脱,花纹内便会渗出催情精油。此刻那些下作的情毒正顺着她纤细的脚踝攀升,把她因屈辱泛红的膝盖染上淫艳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