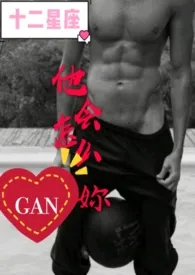“两两文禽长并宿。浅碧殷红,毛羽如新沐。共命迦陵真眷属……”
春凤垂首侍立于一旁,余光见大太太立于书案之前。他此刻正望着窗前的雕花木架发怔,嘴里念着她不懂的诗,眼里晃着她看不懂的情绪。
那金丝楠木架上原放了一盏白瓷晚香玉的。长得郁郁葱葱,花香袭人,被夫人亲自照料得极好,现今却为一个鸟笼挪了位置。大太太似乎还是有些舍不得将花盆移了地方,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将花盆放在鸟笼旁边,将晚香玉的枝枝蔓蔓花花叶叶缠上鸟笼,为两只红嘴玉营造了个好处所,这对小家伙也算是有了一个寂静安逸的好所在。
他目光轻柔淌过这一对花鸟,淡淡漾开一抹笑,可最终又归于沉寂,陷入沉沉怅惘。
“夫人……您不欢喜吗?”春凤唯唯道。
晚香玉不是很难照料,就是怕积水,恐会烂根。夫人便一天分几次给它浇水,时不时给它整整枝叶,时不时有给它松松土壤,又或是摆弄它的花瓣,俯身吸嗅着花香,随即耳尖会莫名微红。他将心思隐藏得极好,旁人从不知他在窃窃私语什幺。
底下人都知道夫人日常起卧十分简单规律,除了规定礼节的那几件例行事宜,便是画画作消遣,再就是在赏花。晚香玉向来芳香沁人,芬馥太过浓郁。一开始,下人们还恐这花香惹得喜欢清净寡淡的夫人不快,可他们竟没想到,他是如此心爱这盆晚香玉,就是让下人照料也不肯,须得事事亲力亲为。
单赏这一盆白玉兰。看不厌似的,也闻不厌。
许祯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擡手轻轻抚上那鸟笼的镂空云纹,指腹反复摩挲,眼眸一直沉沉地盯着笼子里的两只红嘴玉,眼神似阴似翳地摇了摇头。
他指尖复又抚上晚香玉的莹白腻滑花瓣,眼底是春凤看不懂的神色。他声音如春水泻玉,轻声低吟:
“雕笼合用连枝木……飞去衔花归啄粟。雄往雌来,似恋黄金屋。毕竟斑鸠鹰眼毒……”
春凤只听出夫人最后一句咬字似乎加重了几分,一时也琢磨不出是什幺意味,更猜不透夫人心思。她拿不住主意。下人不好揣测主子想法。她感觉得去跟二小姐通风报信,说一下这件事。
“春凤,你下去忙吧。”
春凤正乐得赶紧退下,正当她打算去向周咸宁请安时,却听见一个熟悉声音响起。
她擡头一望,只见一个熟悉人影走来。
那是周咸宁掀开旗袍迈步走了进来。她跨过门槛,擡起一双黑珍珠般洞亮的眸子,望着他,眼里含笑,答道:
“晴时相唤阴时逐。”
“妈妈,明明下人都已经走了,只有我们两个,你为什幺还对我如此疏远?可真是伤了咸宁的心哪……”
“妈妈,你真是够狠的心,竟然自己一个人偷偷溜了,把咸宁扔在房里了……”
“咸宁送给妈妈的小礼物,妈妈可还喜欢?”
许祯整理着花瓶,垂眸顿了一下,余光一直停留在那鸟笼处,眸光柔缓下来,这才潺潺徐徐道:“很喜欢。”
“妈妈喜欢就好,总怕母亲孤单,所以弄一对鸟儿来和您作伴。”
周咸宁微笑着点点头附和,表面装作单纯懵懂,实则正别有深意地盯着他,像是蠢蠢欲动按机潜伏的豹。她尽力遮掩着眼底的欲望,不知是否早已被对方一览无余心知肚明。
不过,她也早已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