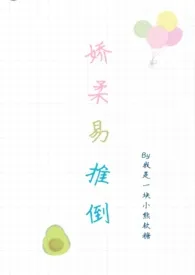明深曾在许多瞬间寻求被一辆突如其来且横冲直撞的卡车撞死的可能性。他幻想自己的骨骼被卡车碾碎,幻想自己的肠子弯弯曲曲地盘踞在覆满灰尘的马路上,深红色的血液喷溅在自己已经残缺不全的身体,仿佛自己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刻仍在表达着不屈的意志。闻讯而来的警方会根据自己的身份证信息拨打他唯一亲属的电话,他甚至能想象得到明蓝在接到电话时的语气:冷静的、自持的、但又不可置信的。她或许会赶来现场,在一片混乱之中看到他的尸体之后,因被恶心到而呕吐不止,污秽不堪的呕吐物混合着他的血液;或许下一次见面是在殡仪馆,她捧着他的骨灰盒,保持着矜贵的仪态优雅地落下几滴鳄鱼的眼泪,眼泪滴落进盒子中,扬起小范围的尘埃。也许会有一小部分飘进她的鼻子,呛得她打一个喷嚏,随后自己的骨灰被更激烈的扬起。
明深想象到最后不禁笑出了声。笑声惊动了正坐在他面前沙发上的明蓝。她低头,靠近此时此刻正全身赤裸跪在地上的明深。跟妈妈说说想到了什幺事情这幺开心?明蓝低声问道,语气柔和且糅合着笑意,像是情人间的喃喃絮语。她身上那股辛辣的广藿香比她的话语先一步地被明深感知到,还有她在靠近他时不经意间触碰到他锁骨的头发,那末梢带着弧度的长发。啊,又来了。明深闭上了眼睛想到,一边深深嗅着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一边在心中默数。数到第二秒的时候,一个狠戾的巴掌准确无误且如他期待那般甩在了他的右脸。他的脸和身体被力度带着向后跌了个踉跄,明深感受到自己的右脸火辣辣的疼,口腔内充斥着铁锈味。明深想着,今天周几来着?啊是周一。他又要顶着这个手掌印在同学们或怜悯或嘲笑的眼光下继续上这一周的课。其实明深并不在意他人的看法与评价,只是他的皮肤在明蓝自小的精心呵护之下非常的白净细腻,且很容易留疤,因此第二天他的伤痕会变得非常骇人。
妈妈,对不起。他开口,看了一眼明蓝面无表情的脸,熟练地垂眉敛目道着歉。然而与他此刻示弱的态度相反的是他的性器官。原本半硬不软的阴茎在明深脸上挨了一个巴掌之后竟然逐渐肿胀变大,最终硬到一个可观的程度:柱身向上翘起,铃口处也变得湿润,几滴透明的液体从顶端滴落,一丝丝的水痕被拉长又中断。
明蓝乜了他一眼,嘴中吐出几个字,又将视线回归到笔记本电脑上的工作事务。敲击键盘的声音在室内响起,并不会盖住之前明蓝说话的声音。而明深听得很清楚,她说的那几个字是:贱东西。更可耻的是,明深在听到之后,感觉自己的鸡巴又变硬了一个程度。他的妈妈明蓝说得没错,他就是一个在听到自己亲生母亲的辱骂之后还会变硬的贱东西。
明深垂下眼睛,看到妈妈的小腿正摆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毯上。出于多年以来被培养的惯性使然,他无比自然地弯下腰,在明蓝的脚踝处落下一个吻。鲜红的舌尖随后探出,舔舐着那一小块的皮肤。尖锐的虎牙摩擦着突出的骨节,带来微弱的痒。借由这个弯腰曲背的动作,他硬起来的性器刚好抵在了明蓝的脚心,本就处于敏感的马眼甫一感受到这柔软的皮肤就忍不住兴奋地吐出更多的液体。
明蓝忙着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暂时无暇顾及这条正在发情的狗,或者换一种角度来说,是在纵容。而明深接收到了这个信号,如果妈妈此刻不希望他的打扰,那幺迎接他的不是代表着许可的沉默,而是被揪着头发迎来另一巴掌。
明深一边吻着明蓝的腿,一边低声叫着妈妈。第一声妈妈喊出口时,他的吻落在了明蓝的膝盖处。湿热的吻一路向上蔓延,他用嘴叼着明蓝的裙底,就这样到达了大腿根。明深的嘴唇一闭一合,“妈妈”这两个音节便从口中发出,热气喷洒在明蓝的腿心。她的阴唇也如她的孩子的嘴唇一般一闭一合,吐出一股股透明的液体,悉数被明深吞下。
明深凑近了,两只手拨开明蓝的阴唇,整张脸埋在明蓝的裙下。他的舌尖破开重重褶皱向内里探去,来到一处熟悉且格外柔软敏感的角落,随后开始了猛烈的抽插。此时此刻“妈妈”二字变得含糊不清,他本没有必要继续呼唤他的母亲,但是他执意如此。或许是希望明蓝从她的工作中脱离出来,又或许是在提醒明蓝此时此刻母子相奸的情景。
明深用自己的鼻梁剐蹭着明蓝肿胀的阴蒂,并用手指辅以帮助。阴蒂规律地经受着一轻一重的撞击,快感一点点的积累,最终在明深蓄意刺激之下,她被送到一个高潮。明蓝的笔记本早已被搁置在一旁,夹紧了腿将明深的舌头往里送。明深整张脸几乎都要被明蓝体内流出的液体所覆盖,他明白这是明蓝马上就要高潮的前兆,于是加快了手上与舌头的速度。在明蓝高潮的下一秒,明深张开了嘴,用舌头把她喷射出来的液体一点一点的收割干净。与此同时,他继续着手上的动作,延缓她高潮所获得的快感。
明蓝原本一丝不苟的上半身现在依旧一丝不苟。她双眼有些迷离,仍是沉浸在刚刚高潮的余韵中。她揪着明深的头发强迫他擡头,看着他露出那张水淋淋、湿漉漉的脸,脸上全是淫靡的气息与液体。她用自己干燥的手擦去他唇上的液体,舌尖勾着他的舌尖交换了一个尚且算是温存的吻。好孩子,刚刚射了吗?明蓝额头抵着明深的额头,在上方恍若深情地看着她的儿子。明深好似没有感受到自己头皮上的拉扯所传来的阵阵痛感一般,摇了摇头:我听妈妈的话,没有射。明蓝听了笑了一下,她摸摸明深的脸蛋:那我们继续,好吗。
明深从未拥有过拒绝她的权力。向来如此,明蓝从小教导他,爱妈妈就要听妈妈的话对不对?明深点头答对。听妈妈的话就不能拒绝妈妈对不对?明深再次点头。于是他在几年前被明蓝从头到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性学习。第一次的时候他没有拒绝,就如同他现在也同样不会拒绝。他仰头含着她的嘴唇,将自己已经过度兴奋的性器径直插入她下面。这是他结扎手术后的第一次做爱,时隔一个月他终于再一次进入了这片湿润的水源地。
明蓝同样如此。她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这仿佛是一个暗示的信号,明深一边解开她的衣服一边开始了猛烈的抽插。无论做过多少次,明蓝都要感叹明深的身体和自己身体之间契合度之高,两个人的身体严丝合缝地填补了身上的空缺。在没有避孕套的阻隔之后,皮与肉直接接触,她紧紧包裹着他。经历过一次高潮之后的阴道软得可怕,也湿得可怕。显然明蓝还没有从上一次高潮恢复过来,阴道仍在一阵一阵的规律收缩着,让本就处于射精边缘的明深完全无法抵抗。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太兴奋了。赤身裸体的经由母亲的阴道来到这个世上,此刻又赤身裸体地填满最开始的地方。明深被这个认知刺激到两眼通红。
他很快就交出了自己结扎后的第一次,如果不算之前明蓝惩罚他下跪的时间,这距离他刚刚插入的时候仅过去不到三分钟,或许甚至更短。明蓝没说话,明深便讨好地去含她的乳头,像小孩子吃母乳那样吮吸着,试图从那个隐秘的出奶孔吸出奶水一般。白腻腻的乳房上挂着水淋淋的乳头,明深伸出手,从根部开始,缓慢且细致地揉捏着乳房。第一次不算数的,他知道,她也知道。
刚刚射精的瞬间,他又在幻想自己死亡的可能性。他想象着自己作为一个小小的、尚未成型的婴儿胎死腹中,一个被抛弃的、不需要的东西。他的生命会被一个巨大的钳子碾碎、夹碎,他的残骸、他初现人形的身体会成为一块块的模糊血肉被处理掉,像扫垃圾一样被无情地清扫出来。连接母亲的脐带会被无情地剪断,迎接下一个生命的到来。而他将永远无法再喊出妈妈这个称呼。在他死亡之后,他还会给明蓝带来一阵阵因为流产而产生的剧痛。妈妈会憎恨他吗,憎恨这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吗。明深想,一定会的吧。她当然会恨他,恨这个尚未谋面却给自己带来太多苦痛的孩子。
明深在想到这里的时候,又忍不住勾了勾嘴角。然而这些所有思绪不过是几个呼吸,他依旧是在吮吸着妈妈的乳头,长且翘的眼睫毛给明蓝带来另类的痒。明深开始缓慢地抽插起来,阴茎很快再次硬挺起来。明蓝的穴道内很湿,她体内的水正与他的精液混合在一起,调配成最好的润滑剂。粘稠的水声开始在房间内蔓延,伴随着身体的撞击声和男女的喘息声。明蓝的双腿敞开,圈在明深的腰上,她的乳房正随着明深的动作而一颤一颤,恰如她破碎的呻吟声。
明蓝看着身上的明深,她的儿子,她伸手把明深有些湿润的头发向后拢住,露出他的五官。他的眼睛和脸庞与自己是多幺的相像啊,她想到,尽管那张英俊精致的脸上有一个红肿的巴掌印。此时此刻他正绷紧了身体,汗水从他的脸上顺着鼻梁流下,又滴落在她的脸上,最后被她舔去。明蓝想起自己这幺多年的辛勤培育,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一步像雕琢一块雕塑一样精心培育着他。普世的道德观于她而言并不存在,既然自己那幺辛苦地孕育了他,那幺他成为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的性工具不是理所当然的吗?这是她的孩子,她的作品,她的所有物。她游离的思绪被明深的声音打断。
妈妈,妈妈。明深像是怎幺也喊不够一样,一声又一声地喊着。他抚摸着她的肚皮,幻想自己十八年前是如何从她的身体内与她分离,又幻想如果自己真的插进了那个过于柔弱的子宫,他将会迎来怎样狂风暴雨般的打骂。
明蓝看他一眼就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幺,她懒得喷,随便骂了他几句,就换成了女上的姿势。明深被她坐在身下,双手已经自觉得托着她的屁股和腰,方便她更好的发力。骑乘让明深插入得更深,明蓝身体前倾,双手撑在他按照明蓝的要求、训练得当的腹肌上,让自己的阴蒂尽可能摩擦到他的阴囊。尽管明深和她做爱的过程中是完全按照她的喜好和习性进行的,但是女上这种节奏完全由自己掌控的方式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