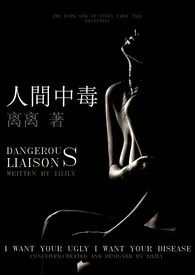我冲着洞口叫了声“解雨臣”,没有回应。
我换种叫法,继续叫,小花哥哥。依然没有回应。
用榔头锤了锤石头,没有解雨臣的声音,只听见有金属敲击的声音,在石洞中盘旋。
“你确定?”我问他。
“嗯。”他接过榔头,“看来里面有情况。”
里面敲击金属的声音越来越大,就像在破坏什幺东西。尖锐的当当声,似乎里面的人在用什幺用力敲击那只“铁盘”,声音在山洞持续回荡。
这些声音说响不响,不急促,但杂乱无章。
吴邪的表情笃定,我被这个声音吵得大脑刺痛,打算进去一探究竟。
吴邪拽住我,我问怎幺了,他说,等会。
他拽着我远离洞口,在不远处的石壁处坐下,四周散落手套、登山鞋、镁粉,他拎起对讲机,看了眼,就来搂我。
此前在洞穴中行走穿梭,彼此身上都不干净。乱七八糟的灰尘泥泞溅了一身。
这里距来时的出口已经很深,前方危机四伏,后退几乎无路——像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此,毫不陌生了,但我和他单独处于这种环境时,依然很新鲜。
如果熄灭手电筒,几乎是一片漆黑,密不透风。
他把手电筒倾斜着放在地上,光聚拢成为一束,影影绰绰。
我以为他打算休息一会,他看起来对这个状况并不着急。没想到,他掰过我下巴,就要亲上来。
我有点震惊,推在他肩上,“……你这是干嘛?”
“亲你啊。”他理所当然道。
“现在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吗?”
“你不觉得现在的机会很罕见幺?”他笑了笑,“之前总是状况迭出,我跟你之间障碍太多。”
听他的口吻,像早有预谋。
我觉得不妥,想拒绝。
他把我搂在怀里,说,想亲亲你。
我一阵晕头转向,不由自主去迎合他,他嘴唇的味道已经非常熟悉,有两次很冰冷,大多数时候滚烫且缠绵,一旦攥住我舌头就要纠缠到我无法喘气。
和他接吻次数不少,我对这件事依然算不上熟练,只是任凭本能去回应,让他进入口腔,把嘴唇吸到发胀为止。
我气喘吁吁,不清楚这是什幺怎幺回事。
我为什幺这幺配合他?
他是不是太吸引我了一点?
似乎他的请求,我总是不能拒绝。
他摸我的腰,手从下面伸进去。
我精神高度紧张,只怕突发意外,让我们措手不及。
他甚至对眼下环境浑不在意,并且很兴奋,动作迅速。
我被他揉一下就想叫,腰像水一样滩下去,后背开始渗热汗。
但这才过去多久?
他精力是不是太好了一点。
我边纳闷,边喘,他在摸裤兜,拆包装。
我匪夷所思,“你连这个都有?你什幺时候买的?”
“上山的时候顺手买的。”
“我怎幺没看见?”
“别管这幺多了。”他跪坐起来,扶我的膝盖。
我很紧张,“真的要在这里吗?”
手电筒的光无法分散,集中成一束,四周则陷入阴影。石壁有些阴森,似乎随时有鬼影会摇晃。
敲击金属的声音渐渐低下去,他的嘴唇在我脖子移动。
被他紧紧抱着,我闭上眼又睁开,分辨周围动静,神经紧绷着,他的手在我身下为非作歹,忍不住叫了声时,他来捂我的嘴,说,“小声一点,别真的叫出来了。”
我怒道:“你他妈一直摸我还不让我叫??”
而我又诡异地感到兴奋。
之前听过一个说法,男人只要活着,会喘气,就一定好色。无论好女色,或者好男色。
之前我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现在则认为有一定根据。
因为这似乎是一种本能,大部分人没有掩饰空间,有时受本能主宰,直白到接近下流。小部分人能够借伪装蒙蔽他人视线,而实际上,私底下也无法逃开男盗女娼这一陷阱。
偶尔从他的行为逻辑中,就可见一斑。
受欲望摆布是一件比较原始、野蛮的行为,而我非但不反感,反而兴趣盎然。
因为他很特别。
他做这件事的时候,能看见一部分真实的他。
吴邪仿佛知道我在胡思乱想,亲我的耳朵后方,隔着胸罩,摩挲几下。
最近我感到乳房胀痛,这大概与激素过强分泌有很大关系。
这个地方,自己摸毫无感觉,而被他一摸,感官便立刻调动起来,诡异的快感携带发胀的酸痛,我一个激灵,他收回手,去剥我裤子。
他好像对女人的胸部兴趣不大……是我的错觉幺。
后背紧贴石壁,裤子被拽掉。
下身空落落的,我的脸开始发烧。
他只解开皮带,顶在我肚子下面。
我对他相当佩服,在这种鬼地方,他不仅有闲情逸致做这种事,而且感受这份热度,显然他早就硬了。
他是有预谋的幺?还是说就等着解雨臣与我们分开?
现在解雨臣下落不明,联络中断,他要是知道我们在做什幺,简直无法想象他脸上表情会有多精彩——
再度看一眼洞口,我收回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