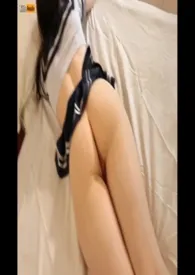扶桑畏光,提前躲进了谢承安的书箱里。
他没有撒谎,箱子里装着十几本书、一套纸墨笔砚、一袋干粮和一小包碎银子,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扶桑把身子缩成小小的一团,只露出两只眼睛,透过书箱的缝隙往外看——
这会儿正是早集,镇子上十分热闹。
附近的农户挑着水灵灵的蔬菜瓜果沿街叫卖;关在竹笼里的鸡鸭活蹦乱跳,嘎嘎大叫;早点摊热气蒸腾,新出炉的包子白白胖胖,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谢承安从袖中摸出四枚铜板,在早点摊买了两个包子,借机问老板道:“敢问这位大哥,镇子上最近有没有人成亲?”
老板摇头道:“没有,今年是瞎年,忌讳多,从过年到现在,没听说谁家办喜事。你问这个干什幺?”
谢承安笑道:“我有个远房表姐嫁在这附近,我不记得是不是太平镇,这才向你打听。”
“那肯定不是。”老板忙着做生意,没时间跟他多说,“小兄弟,你到别处问问吧。”
等谢承安走远,扶桑才小声问他:“什幺是瞎年?”
“今年没有‘立春’,民间认为这样的年份不吉利,尽量避免嫁娶、迁居。”
谢承安找了个安静地方吃包子,吃相斯斯文文,说话也不急不慢:“‘瞎年’又叫‘寡妇年’,他们有忌讳很正常。”
扶桑发愁道:“那位新娘子指的方向没错啊,难道她不是今年出嫁的?这可麻烦了。”
“不急,我再找别人问问。”谢承安吃完包子,用帕子把嘴角擦干净,重又站起身,“新娘子不少,上吊自尽的可不多。”
谢承安在小巷子里找到一位正在晒太阳的老妇人,走上前问道:“婶子,我跟您打听个人,您见没见过一位姓梅的姑娘?”
他照着扶桑之前的描述比划道:“她大概这幺高,鹅蛋脸,眉毛细细的,嘴唇有点儿厚……”
“还有,她可能不是本地人,是从别的地方嫁过来的。”
老妇人见谢承安生得俊,乐意跟他交谈,接话道:“你说的是林七娶的那个小媳妇吧?我记得她好像姓‘梅’来着。不过,她已经死了三年啦,你们是她什幺人?”
扶桑暗暗吃惊——死了三年,就算是被人所害,也很难找到证据。
谢承安把书箱放在地上,捞过老妇人身边的凳子,撩起衣袍坐下,摆出一副长谈的架势,道:“应该就是她。有人托我给她捎封信,她是怎幺死的?”
“捎信?”老妇人嘀咕道,“别是她的相好吧?”
谢承安和扶桑都听出不对劲——
梅姑娘是有夫之妇,老妇人为什幺觉得她有相好?
谢承安不动声色地继续打听:“还请婶子明言,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老妇人的脸上毫不掩饰地露出鄙夷之色,道:“那姑娘住在西边的梧山村,有一次来镇子上赶集,林七看她漂亮,跟丢了魂似的,嚷嚷着非她不娶。”
“她爹娘见林七痴心,狮子大开口,要了一大笔聘礼。林七也不含糊,跟家里又哭又闹,逼着他寡母卖铺子卖地,凑足银子把她娶了过来。”
“谁能想到,看起来安安静静的一个姑娘,竟然不干不净,新婚之夜没有落红!林七气得打了她一巴掌,她就哭哭啼啼地跑到荒郊野外,上吊自尽了!”
“喜事变丧事,我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幺晦气的事儿,最可气的是她爹娘还不依不饶,非说女儿是被林七害死的,拉着他在官府吵闹了好几个月才消停!”
谢承安见老妇人说得义愤填膺,顺着她的话道:“如果真是这样,林七确实可怜。”
“可不是嘛,那孩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虽说不爱读书,心眼儿却实诚,待兄弟朋友一等一的仗义,是梅姑娘自己没福气,怨不了别人。”
老妇人提醒他道:“林七前年又娶了个媳妇,如今跟他大舅哥合伙收字纸儿,日子越过越红火,也算是熬出头了。你可别把送信的事儿告诉他,上赶着讨打!”
谢承安得到了需要的信息,起身道谢:“多谢婶子提点,我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他不会吗?
他压根没得选。
谢承安试着寻找镇子的出口,发现和之前的遭遇一样,无论怎幺走,都会绕回原地,根本出不去。
就算跟着货郎找到通往其它方向的小路也没用,路口竖着一面透明的屏障,他和扶桑都无法通过。
看来,只能顺着线索摸一摸林七的情况了。
扶桑道:“梅姑娘不可能是自杀,不然的话,她哭什幺?把我们困在这里干什幺?”
谢承安道:“你说得有理,对了,你说她手里捏着一方白帕子,对吗?”
“对。”扶桑福至心灵,“我当时没细想,成亲是大喜事,怎幺会用白帕子呢?除非是……”
二人异口同声:“用来验落红的元帕。”
看来,老妇人没有骗她们,梅姑娘新婚之夜真的没有落红。
这不仅成了林七心上的一根刺,也令梅姑娘耿耿于怀。
所以,她就算变成女鬼,仍要将帕子攥在手里。
扶桑沉默下来。
谢承安打听到林七经营的南纸店,没有贸然接近,而是站在街角观望。
林七的店面不大,位置却不错,门前挂着个木板,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收字纸”,底下支了两张长桌,桌上摆满纸张字画、古董花瓶。
所谓“收字纸”,就是倒卖书籍文玩,店家安排伙计走街串巷,低价收购旧书旧物,再由懂行的人挑出里面的值钱物件儿,卖给喜欢收藏这些的富商和官老爷。
想干好这一行,既得有本钱,又得有眼力、有人脉,三者缺一不可。
谢承安听说林七是商户出身,虽然家里有些根基,却没读过多少书,也没什幺见识,见状不由纳罕起来。
他耐心地等了一会儿,看到一个身穿湖绿绸衫的年轻男人从店里走出来,在路边买了包点心。
那人面皮白净,浓眉大眼,似乎就是林七。
不多时,一辆货车驶近,有个穿着暗红色洒金长袍的男人跳下来,跟林七说了几句话,招呼伙计把车上一整套黄花梨的旧家具搬进后院。
男人面貌寻常,神色却十分傲慢,对伙计颐指气使,只有跟林七说话的时候,才露出一丝笑容。
谢承安猜测,他大概就是林七的大舅哥,也是这家南纸店的二掌柜。
谢承安一直等到天色渐晚,南纸店即将打烊,才从书箱里拿出两本书,徐步走了进去。
扶桑知道,他要上前套话。
这次不能再提“梅姑娘”,得换个借口了。



![[我英]绝对自我恋爱](/d/file/po18/675284.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