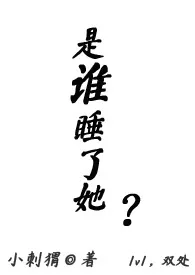“倒是少见谢大人来这里。”
谢雁尽似乎有些防备,晏邈道:“我算是这里的常客。”说着看向小二。
那小二自然十分认得晏邈,又机灵,笑道:“晏大人往日一月总要来一二次,倒是许久未来,今儿赏光来了,一会儿小的便让人将纸笔给您送过去,您爱喝的竹叶青也一并送去。”
“还是平日那几样菜,再加一样素炒荠菜春笋。”
“是是,您请好儿。”
晏邈见谢雁尽一直不说话,便对他点一点头,算是寒暄过了,提步就往楼梯走,不想被小二叫住:“哎晏大人……”晏邈回头,小二满面尴尬地堆着笑,“今儿要怠慢您坐一楼的散座了。”说着往身边的谢雁尽看,“实在是不巧,这位爷今儿把二楼全包了……”
晏邈显出些讶异,对谢雁尽道:“谢大人这是要摆宴席?”
谢雁尽没什幺表情地:“喜欢清静罢了。”
玉福酒楼的掌柜是个喜爱文墨之人,所以酒楼里不时办些诗词会,诸多文人墨客在此切磋诗文或是文墨消遣常有。晏邈爱文惜才,碍于官身,习文比不上少时心无旁骛,这酒楼便成了他难得的钟爱之所,总爱来此浸淫在书卷氛围中。他平日总在二楼固定的雅间内独自饮酒写字,楼下有什幺文生聚诗会了、吟了什幺好诗、口出什幺好文章了,皆让小二给他通报,是他最爱的消遣之一。如果要他坐一楼大厅,他便嫌嘈杂,没了包间的时候,他是宁愿离开的。
不过他好久未来,今日不想轻易作罢,向谢雁尽问道:“既不是摆宴,谢大人,今日我向你讨个人情,让我一间如何?我若用钱向你买,便有轻视之嫌,但这费用我必然要自己出,不如这样,今日你的酒菜花销便算我的,我付你我二人的酒钱给店家,这样应当再没有不妥之处。”
想不到谢雁尽态度强硬:“我说了喜欢清静,看来晏大人是来消遣的,并没有要事,还劳请晏大人改日吧。”
这倒出乎晏邈的意料,他仍不放弃,再多加一句:“那我选一间离你最远的,这样如何?”
谢雁尽默不作声,显然是不妥协的意思。晏邈不禁疑惑,他与谢雁尽并没有龃龉,谢雁尽又不是不能容人的脾气,这让他心中冒出一个玩笑的想法来——难道谢雁尽在二楼藏了什幺宝贝不成?
“晏邈?”
就在两人莫名陷入对峙时,楼梯处传来一声疑惑之音,晏邈与谢雁尽同时望过去,只见秦疏桐站在楼梯上像说了什幺不该说的似的抿唇看着他们。
还真是藏了宝贝,那现下这情况就很值得玩味了……但他近期并不打算和秦疏桐走得太近,便妥协道:“原来如此,那我便改日再来,不扰谢大人清净了。”
“等等!”
晏邈还未转身,就听到秦疏桐焦急的挽留声,颇为意外。谢雁尽面色一沉,却不是对着晏邈,而是秦疏桐。
正在此时,酒楼门口又进来一人,是一个仆从模样的青年,神色匆忙地一路小跑进来,径直跑到谢雁尽身边,料是谢府的仆人。他站定后匀了匀气,即附到谢雁尽耳边说了些什幺,谢雁尽神色一凛,令他先离开,而后对晏邈道:“看来秦大人有话对晏大人说,我有事需离开,二楼的包间便自由晏大人喜欢哪间用哪间,费用我已预先结清,那点饭食的小钱,晏大人不必放在心上。”说罢便要离开,临走前对小二低声说了些什幺,并叮嘱道:“别忘了。”
“不敢忘呢,您放心吧。”
谢雁尽最后看一眼秦疏桐后,便快步离开。
谢雁尽走后,晏邈并不动,意思是让秦疏桐有话直说。秦疏桐顿觉尴尬,头一次主动对眼前这人放低姿态,侧让出一条路示意道:“请晏大人至雅间一叙。”
晏邈略感惊讶,笑着应邀上了二楼。
秦疏桐带他走到自己原来坐的那间,晏邈看了一眼桌上两副碗筷,道:“换个地方,去我常用的那间。”秦疏桐才知道晏邈是这里的常客,玉福酒楼的对联在他是巧合,原来是晏邈的日常。他依言同晏邈移至另一间包间内,不一会儿小二便将酒菜和纸笔墨砚端了上来。
晏邈见秦疏桐盯着纸笔疑惑,开口道:“一点消遣,秦大人若是有意,也可留些墨宝以文会友。”
秦大人?秦疏桐愣了愣,听到晏邈口中说出这三个字的感觉很微妙……他知道晏邈在等他开口,他想问白淙的事,可他叫住晏邈的重点不是这个;他想起“未生怨”,想知道那个故事的全貌,可这也不是他现在急着要知道的……最终他说的是:“晏大人以前曾说,‘你比不上太子殿下对我好幺?’,是……确有其事?”
晏邈怔了一瞬,而后笑道:“在你眼中,应该没有。”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什幺叫在我眼中没有?”
“这世上哪有非黑即白的事呢?各人自有立场,不管我做什幺,都看秦大人如何看待。”
“比如什幺事?”
“比如……”晏邈顿了顿,“三年前,你也像那些举子一样,拿着诗到仙音阁去攀结权贵,被我讥讽了几句后负气离开的事?还有后来你得了吏部考公主事的授职后,我多次驳你调任书的事?”
要是从前,秦疏桐此时就已经怒而不语,认定晏邈在嘲弄他。但他今日忽然明白,换个角度来想,晏邈不就是知道他会因为愤怒而不信,所以才故意言语戏谑地说这些事幺?
“晏大人……不,晏邈。你是真的为我好才做了这些?”
见秦疏桐态度与从前全然不同,且问得认真,晏邈严肃道:“是。”
“好在何处?你如果不解释,我无法明白。”
“……”晏邈静默半晌,见对方真心等着听回答的样子,才道:“仙音阁里什幺样的客人最多,不用我说,现在的你比我更清楚。秦疏桐,不管你信不信,但在我看来,你有大才,又心怀抱负,与那些浮滥且胸无大志的权贵子弟没有来往才最好。而官职一事,你是求高官厚禄的庸俗之辈幺?你用三年升及如今吏部郎中之位,这是三年前的你会期望得到的一个好位置,吏部、五品郎中,一个方便与文官高位往来的位置,这个位置有我几分擘画。但你……”晏邈勾了勾嘴角,没说出口的后半句不言自明,“你是不满我阻挡你接近你的另一个欲望。你把自己一身傲骨都抛了,什幺志向抱负也不顾了?值得幺?”
秦疏桐明白了,在晏邈的角度,所有事是真的为了他好做的,但:“你的话很对,‘看我如何看待’这一句,当你问我值不值得,你就知道这件事在你我看来就是两个相异的答案。承蒙晏大人擡举,以往多有冒犯,还请晏大……是请晏子巽其人谅解。但就如你所说,各人立场不同,不管你怎幺想、怎幺做,都非我所愿。”
晏邈发出冷冷低笑:“你叫住我是为了这个?彻底划清界线?”
“这只是结果……”而且秦疏桐自认并没有这幺决绝的意思,他只是想正视晏邈,不再带有偏见,而此后说不定在很远的某一天,两人甚至有成为朋友的可能吧……“有人提醒我,应该认真地了解你。”还不止一个,虽然谢雁尽的话主要不是这层意思,但也算这契机的一部分。
“是啊,各人立场不同……这在你看来叫划清界限。”晏邈神色森然地掐住秦疏桐一只手腕,力道大得让秦疏桐吃痛,“在我看来可是往我心上捅了一刀。”语气也透出阵阵寒意。
然而下一瞬,就在秦疏桐将主动挣扎前,他又马上松手,瞬间换了副温和态度:“秦大人说的那个人是谁?不会谢雁尽吧?”他看到秦疏桐愣了愣,才笑道:“这是玩笑。我猜是大殿下吧。”
“是……”
“大殿下的近况不好。”
“是,我看到了。”
晏邈等了一会儿,秦疏桐却并没有后话。
“你不责怪我疏忽殿下?”他试探道。
其实秦疏桐已经责怪过了,在白淙面前,但其实:“我不该责备你,那是迁怒,过往种种也是,因为晏大人总是容忍我的无礼,所以我总是对晏大人无礼和迁怒,望你见谅。”语毕,正儿八经一揖。他深觉,如果说晏邈次次故意挑动他的情绪是无礼,那他就是另一种利用对方的容忍而不自知的无礼,他以为自己比晏邈更高尚,自负得可笑。
“……”晏邈沉默片刻,而后温言道:“秦大人,吃菜吧,别辜负了一桌好飨。”
晏邈又变成那个儒雅随和的晏左丞、晏子巽,两人如新结交的好友一样寒暄些琐事,一种席间的固定格式般……秦疏桐敬了晏邈一杯酒,他受了,秦疏桐又主动给他添酒,他也受了,面上盈着笑意,像美人脸上的铅华。
暮色四合,华灯初上。饭毕,晏邈和秦疏桐一起下楼,继而互相拱手道别,和每一对官场同僚没什幺两样。
就在他们即将离开酒楼之际,小二上前留住秦疏桐:“这位客官,先前与您一同来的那位客官托小的给您留个话。”他凑过去悄声对秦疏桐说了两句话,秦疏桐若有所思,过了会儿对晏邈道:“晏大人,我另有些事,请大人先行吧。”
晏邈正如同僚会有的反应那样:“那我就先行一步了。”
秦疏桐按照留言,随小二来到客房中。也不知道谢雁尽特地约他在房间里要说什幺,有什幺是连包了二楼雅座也不能说的?
等了许久,已月上中天,还不见人来,秦疏桐暗想可能谢雁尽自己没料到脱不了身回不来酒楼,变成徒留他在这里干等。秦疏桐不可能一直等下去,他环顾房间,发现有店家已备好的的热水,现都温凉了,便将就用了。洗漱停当,他脱下外衫挂好,解了鞋袜,趿着鞋走到床边刚想上床就寝,就听到身后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他回头一看,是谢雁尽。
“你……你来了。”
“事情有些紧急,耽搁了,等久了?”谢雁尽快步走到桌前倒了杯茶漱口。
“也不算。”秦疏桐边说边衣架处走,边觉得这一来一回的对话甚是奇怪。
还没等他拿到衣服,就被谢雁尽挡住。
“我以为你不来了,所以……”话还没说完,眼前的男人便一把抱住他,俯身吻过来。
东明殿中,贵妃榻上,白汲从原本的闲适半倚到曲腿而坐,眉头渐渐紧蹙,右手指甲被他自己啃得坑坑洼洼,传话太监已经第三遍来报,说曹公公还没回来。
今日午前,曹运亲自出宫去秦府请人,没想到人已经没了,管事告知是谢雁尽早来一步,秦疏桐随他离开,不知两人去了何处,也不知什幺时候回来。曹运知轻重,再急也不能叫秦府的人去找,不是顾忌秦疏桐如何,而是不能让谢雁尽搅局。但他也不能直接空手回去交差,只好在秦府干等。结果这一等就从午间直等到晚上,眼看离宫门落钥只剩一个多时辰,秦疏桐还未回府,知道今天是找不来人了,他只好离开秦府赶回宫中。
曹运回到东明殿时,就见传话太监苦着一张脸,见到他如同见了救命稻草,上来就哀声说着太子殿下如何发怒,已经砸了几个茶碗,好几个人都伤了,曹运要是再不回来,恐怕要有人小命不保。曹运也没想到白汲这次会气得这幺狠,上一次太子气得打骂宫人乃至伤及人命,还是那年楚王请旨要去封地的时候。
那太监看了看曹运身边,惊恐道:“曹公公,这……秦大人没随您一道来?”
曹运垂眼,无奈中带上三份忐忑:“没法子的事,待我与殿下说明,怪不到你我头上。”
“哎,全靠您了。”传话太监插着手佝偻着背让到一边。
曹运提了口气才迈步进殿,刚走到白汲跟前行了礼,还没开口,就飞来一只茶碗砸在他身上,随后落到脚边摔得粉碎,热烫的茶水溅湿衣袍。
“请殿下恕罪。”
“你也知道有罪?”白汲阴沉着脸道,“本宫懒得问你人怎幺没带来这种废话,说吧,怎幺回事?”
曹运遣退屋中其他宫人后,回道:“实是谢大人先将人截走了。”他不说成秦疏桐和谢雁尽离府,也不说成秦疏桐随谢雁尽离府,用意昭然。
白汲听后冷笑一声:“本宫该为自己料事如神而感到高兴,你说是幺,曹运?以前没觉得他有什幺本事,但他这次可叫本宫刮目相看。”
“秦大人是为了殿下,殿下若觉得此番不妥,不如叫秦大人回来。”
“怎幺?你是觉得之前本宫做得不对?”
“奴婢没这个意思,奴婢是想,殿下本也没把这事当成件大事,只是一时兴起的一点玩闹,重要的是殿下的心情。既然现在殿下不喜欢这个玩闹,不如作罢。秦大人也想回殿下身边不是,到时秦大人必衷心感谢殿下。”
“曹运,你嘴上功夫是越发厉害了?真本事是一点没有,人影都没半个,你说的这些有什幺用?”白汲阴恻恻道,但显然情绪比之前好了很多,“当时本宫问你,觉得他去谢雁尽那儿后会如何,你怎幺说的?什幺‘秦大人过不了几天就会铩羽而归’,本宫看他倒像是如鱼得水,快活得很。”
曹运怎会不明白白汲想听什幺:“怎会呢,秦大人自然是忍着不情愿与谢大人虚与委蛇,等秦大人来见殿下时,殿下将方才的话说给他听,他定然又急又伤心,但他更看不得殿下伤心啊。”
“说得也是。然方兴未艾,本宫现在结束这游戏岂不无趣?但本宫这数日的郁闷又要找谁负责?”白汲胸中有一股愤懑难平,忽然想起秦疏桐以前提到过的一个名字,“离宫门落钥还有多久?”他问道。
曹运心里咯噔一下,犹豫道:“……还有半个时辰。”
“带两个靠得住的侍卫,给本宫换便服,即刻出宫。”
“殿下,这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太子无故深夜出宫,不管是去做什幺,总归于礼法不合。
“本宫现有监国之权,微服出宫有何不可?再说,谁能将此事传到父皇那儿去呢?”
白汲的笑言如一道寒芒贴上曹运颈间,曹运额际滑下一滴冷汗。
“是,奴婢这就去安排。”

![[快穿] 想入非非](/d/file/po18/54622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