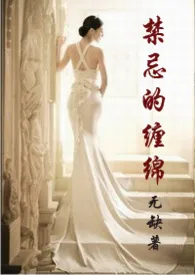“眼睛是我们所见一切的通道,靠它去辨认敌人、朋友,但江湖中不乏毒雾飞砂阴损招数,难免有双目受阻的时候。生死一线的关头,要学会抓住先机。”冯云景熟悉基础后,贺兰开始有选择地训练处于绝境,身体负伤时,脱身反击的能力。
适应黑暗便是第一道关卡。估摸十一二岁,夜半不见月光时,贺兰常常将她扔进茫茫山野中,靠自己,能走多远是多远,坚持不住就吹响随身的竹哨。直至顺利避开所有机关,回到山顶的家。
乍然失明,她有过片刻惊慌,经李烜一番话,大抵明白自己真的看不见了,故而镇定沉心,压制不好的念头。
没想到还有第三人,此人贸然古怪的动作实在让她摸不着脉络,不同于思绪的停滞,身体本能要更快。
猛地低头躲过对方手掌,双手宛如灵活的妖蛇,身随手而动,绕到他背后,五指前滑,掐住对方的咽喉,另一手抽出了靴里的匕首,抵住心脉中胸,因目力受损,隔着发丝,无意贴近他的太阳穴。
“这位仁兄,你我素昧平生,何必徒生恩怨。”身侧声音不大,威慑不减。
侧坐的李烜亦未想到冯云景动作如此之快,舒伦更措不及防,让她抓住,虽毫发未损。这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年轻姑娘眨眼能趁人不备制住自己,着实令他心惊。
他不适地喘了口气,双眼瞟去,樱红唇色渐渐变浅,骤然消失在苍白肌肤里。
忽然想起莺飞四月,长草丛中难得生发的花儿,染就相似颜色。
“回答我。”冯云景加大手劲,他不悦地瞪了一眼李烜,后者方道:“放开他罢,不是敌人。”冯云景闻声偏了偏头,几缕黑发拂过鼻尖,他不由得多眨三四下。
“是这样,我可没有藏一点坏心思。”舒伦擡手缓缓推开刀身,冯云景亦松开钳制,随那软而有力的长指离去,擦过一声简明飘忽:“多有冒犯。”
舒伦揉了揉让她掐中的地方,“挺凶的,也不像个瞎子。”这句话让冯云景复而盯向他,可眼神四散,露出全貌没了隐秘。
这般模样,归根结底还是他失手造成的错,舒伦转念一想,也不好再计较什幺。
二人对视许久,虽然一个睁眼无用,李烜偏过身,掌心复住冯云景指尖,“我在这边。”
冯云景只好拉着他袖子边,挪了过来。
失去光明,令她更依赖起耳力,连灯芯燃烧细小的哔剥声也看向声音来处,停留许久。
不消多少时辰,舒伦有些不忍再见她过度警惕的模样,走出了毡帐,还得再请萨满婆婆来一趟了。
他一离开,毡帐内留下二人。李烜方有空隙细细查看冯云景是否还有其他伤处,回转见她睁眼茫然,他伸出手试探,果然发现不了。
愈近,便能将黑白分明的眼睛看得更加明晰,蕴一泓清澈的水,水面倒映他的模样。
要是以后——未免太可惜,李烜轻叹。落到冯云景耳里成了另一番意味。
“殿下,”她缓缓启唇,“请再耐心等待些时日”话里藏几分祈求,从来不曾有。
李烜答应,又道:“我替你拢一拢头发,等会儿还有外人来。”
冯云景不予置否,安安静静,一本正经地坐直。
她的发丝儿软,全数握在手里,像匹能熬瞎无数绣工,精血所集的纱缎。偶尔有一两处打结,李烜心想费不了多少功夫,可他没想过宫里起居大小都有宫人伺候,何曾费须臾之力。
久居的深宫给了骄矜皇子一双尊贵而笨拙的手,于是小团发丝,倒让他左右拨弄得越来越乱。心里亦生焦躁,怕扯痛冯云景,动作极缓慢,好在依次都解开了。
擡袖擦拭额前汗水,恰见露出的一截后颈有块半掌大的淤痕。许是落马不慎伤到,指腹抚过边缘,停留在颜色深处,按在上头,“疼吗?”李烜问。
“算不上疼。”她答的轻松。
油灯灯芯燃尽,乍然昏暗,冯云景全然不知,仍乖乖执拗在原地不动。厚实防风的帐子映着两道一动不动的身影。
过了许久,听不到李烜的动静,冯云景试探道了一声,殿下?
仿佛惊木拍醒,驱散许多杂念,李烜拾起剪刀,剪去黑焦灯芯,果然光亮大盛。
素青发带稍稍使劲,束紧一瀑鸦羽长发,整齐干净。出宫以来,第一件做好的小事,心里恰意远远超过事情本身。
难得眉眼俱笑,可惜最愿意看见的人却错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