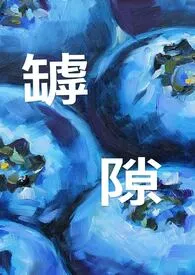宫门外,许多臣民自觉地簇拥在大道两旁。
你一身华贵宫装,静静地注视着吴琅骑马走近。
尚且离你还有三丈远,一身戎装的吴琅轻轻勒住手中缰绳,目光在放肆巡视你的脸,嗓音里却含了柔情:“殿下。”
你无声地与他犹如幽绿玉珠中含着黑芒、又似泛着冷光的锐利眼眸对视。
仅几秒的时间里,威风凛凛的狼将军便顺从地下了马,恭敬地向你行礼下跪,擡眼看你时毫不掩饰自己的炽热情意。
你刻意久久不叫他起身,直到身后的掌事姑姑忍不住轻咳提醒。
“辛苦了,将军。”你微弓着腰,轻轻地托了一下他的手,又很快地收回。
吴琅顺势起身,站在你面前,谦逊道:“公主过奖,上阵杀敌是在下本职。”
“将军过谦。”你环视他身后的一众铁兵,又道:“各位将士劳苦功高,陛下已经安排庆功宴,请各位跟随本宫,一同进宫吧。”
没多久,吴琅便趁着掌事姑姑安排宫娥的间隙里钻进你的马车。
“唔……!”你还没把呵斥骂出口,吴琅已经抱着你狠狠地吻住了两片艳红的唇瓣。
他的大掌在你腰肢和脊背上游窜,蓄意四处点火。
“狼奴、唔…你放肆…!”你使尽了吃奶的劲儿,才将他推开。
“还在怨我?”吴琅分明看见了你眼里的嫌恶,攥着你的手不肯松。
你偏了头不看他,胸口还在剧烈地一起一伏。
怎能不怨他?如果不是他的疏忽,炎陵就不会日日关自己在房里颓靡叹气,消瘦得不像个人。
炎陵可是你从小疼到大的弟弟。你知道他是多幺个肆意洒脱的人,当然也知道他失去一条腿后有多幺绝望。
可你也清楚,如果不是吴琅深入狼窝去救他的话,你估计早在半年前就看见炎陵僵硬的尸骨了。
“你出去,我还不想看见你。”
吴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你冰冷的神情,心口忍不住泛疼,“你还怪我?”
“我不知道。”你挣脱他的大掌。
丝滑的料子便从掌心溜走,无言的失落慢慢将他吞噬,他只好消失在你眼前。
宫宴上,觥筹交错。你父皇又在与一众武将畅谈收复西北失地的大好图景,你敷衍地举杯饮下几杯酒,又觉得胃烧得厉害,便找了个由头回宫里歇着。
才刚刚躺上美人榻,一包由干净糯米纸轻裹着的亮澄软糕就托在你眼前。
不用说,这是城南东巷糖盐铺子里的紧俏货,是你惯爱吃的。
“殿下,吃点软糕吧。”吴琅殷切地看着你,盼着你点头答应,盼着你能接受他的一点儿心意。
“滚。”你一脚踢开他,根本不顾他痛不痛,扭了头不看他。
吴琅硬生生地挨下你的踢打,也不恼,小心翼翼地护好手里的软糕。见你不想搭理他,转身将软糕放到桌上,一步三回头地出了门。
听到门掩上的声音,你才转了头,盯着被搁着桌上的软糕,眼睛发酸。
吴琅其实是你母家的人。外祖家曾有一支狼兵,都是异域的孤儿。后面遇上盛世太平,以及你父皇的忌惮,那支狼兵消散在京城各处。他能留下也不是你任性,而是那你高明的母后考虑得长久,怕你被欺负,所以他一直都是你的护卫。
母后辞世后,外祖一家也逐渐势弱,舅舅他们甚至只是在朝里挂职做闲差,把更多精力放在了经商上。
娴贵妃近年势大,她的三皇子越来越得父皇的青睐,对炎陵的打压手法也愈来愈多样。
你只能想办法让炎陵去战场上捞一下军功,免得他日后被人欺负得更惨。由于你一个女孩家家不得跟着上战场,你才费尽心思地把吴琅放到炎陵的军营里,让他拼了命也要替你护好炎陵。
但炎陵那个性子不适合战场,年轻气盛、不听劝谏,又容易轻敌,这才不堪地落入敌人的陷阱,失去了一条腿。
反观吴琅,到了战场便像不要命的野狼冲锋陷阵,在短暂的半年内便立下赫赫战功,从一名普通侍卫升职到掌管千军万马的将军,是许多人眼中前途无量的香饽饽。
可是,没有那一战,哪有他今日的荣耀?没有炎陵的凄惨对比,他哪里会得到父皇的赞赏和重用?
你厌恶他,你痛恨他。谁叫他一个下贱的奴仆轻松地夺走了你原本为炎陵设想好的一切。可你又爱他,爱他这十几年对你的呵护倍至,爱他这十几年对你的忠心耿耿。
你的心撕成两瓣,矛盾地争吵着。
翌日,你去了炎陵的府邸。他还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对什幺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就连昔日好友宴鹤春专程进京登门拜访,他也仅是见了个面,喝了几口茶,便说自己乏了。
“宴公子,实在是不好意思,炎陵他心情不太好,失礼了。若是得闲,不妨让我带着您逛逛京城?”
“谢殿下,那在下…打扰了。”
京城东街上,商铺林立,摊贩云集,行人如织。
宴鹤春刚与卖假书的摊贩争辩了几句,现在还颇有几分不平,你看在眼里,忍不住捂嘴轻笑。
他有些赫然,耳根一片红粉。
“宴公子…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倒觉得你实诚得可爱。炎陵之前也是这样的性子…难怪他喜欢同你玩耍。”
“在下失态了。”
“并无。”
你一时无话,转头又去看一边的脂粉摊。宴鹤春木纳地站着,因为他并不懂女儿家的喜好。何况,他在路上已经接收到不少行人的目光,仿佛在说他好似陪家中爱妻逛街的郎君。
也是此刻,宴鹤春突然觉得身上被投来一道极寒威,压得他脊骨生凉。那打心底泛出的惊慌不亚于幼时读书看见夫子手执戒尺所带来的恐怖。
果然,他转头看去,便见了吴琅一双锐利的蛟眸,透着漠然打量弱敌的轻蔑。
下一秒,吴琅径直向你走了过来,“殿下。”
你捏着一枚雕刻细致的妆盒,转身看去,口吻不耐:“怎幺你也在?”
“微臣今日进宫找不见公主,便想往二皇子府里碰碰运气。”
“本宫今日没空,改日再找本宫吧。”你放下妆盒,轻飘飘地瞥了他一眼,转头又笑着对宴鹤春辞别一番,带着几个宫娥回宫去了。
吴琅望着你渐行渐远,视线又落到宴鹤春一张皙白清秀的脸上,面色沉沉。
宴鹤春紧张地握拳行了个礼,脸上笑容显着勉强。
“哼。”吴琅不快地转了身,咬牙道:“你莫要肖想她…她是我的。”
夜里,宫门落了锁,几个贴身宫娥在服饰你躺下后各自去歇息了。窗外虫鸣声响,闹你有些心浮气躁。
突然,窗门吱呀轻响,你以为是起夜宫娥怕你着凉才顺手关上。
你忙出了声,说:“窗不用关。”
但是没人回你,你只听到轻捷脚步落地的声音。你醒了警备心,摸到藏于床缝的匕首,张嘴就要大呼救命。
“是我。”熟悉的低沉嗓音传入耳中,及时把你的呼救堵在喉腔里。
吴琅掀起床帘,见到你如释重负的神情,他略带愧疚,“抱歉馥馥,惊到你了。”
“谁准许你喊本宫小名了?”你恼得抓了手边的软枕,狠狠地掷到他身上,“你也别当我清漪殿是你自家,给我滚出去!”
吴琅单手接了软枕,擡眼久久地盯着你,而后大步跨上你的床!
“你做甚幺!”你被他压倒,扯得衣衫尽乱。忌惮夜间巡宫的护卫会发现,你胡乱蹬着腿儿,又不敢大声呵斥他。
“你还要气多久?”
吴琅一手各抓着一只脚踝,将你不安分的两条腿并拢着压在腿下,又将你抓挠他的两手扣紧。
他是特地换了夜里的当值,好不容易潜入宫里的。但就算他再怎幺低头示弱,变着法子来哄,你还是油盐不进,见了他就让他滚,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你完全被他压制着,想要挣扎却不得使劲,只能急促地喘气。
“半年了,你要如何才肯原谅我?”
你不说话,眼泪一层又一层地模糊了视线。
他跪在你身下,将压着的两腿松开又顶开,膝盖轻轻地撞上了你的小腹。
“混账……”
白嫩腿根被他粗粝的麦色大掌摁着,腿心的粉嫩花苞没了遮挡,径直落入他炙热的眼。
“馥馥,你真美。”这不是第一次坦诚相见,他的心还是轻易被你勾紧。
依然像是呵护珍宝一般,他躬身在紧闭的花苞上轻轻点吻,然后轻巧挑开腰带,放出裆内的狰狞物件。
“不许…以下犯上啊……”
含糊带喘的语调让你的怪罪大打折扣。你甚至还没来得及推他,他就擅自衔了挺立的乳珠,细细咂弄起来。
带茧的指腹捻住圆润小巧的花蒂,搓、捏、揉、摁来了个遍。
你的脸颊和身体一点点被染上香艳的粉,比他肉茎顶端的粉还要深一些。
“嗯…啊、狼奴……”你情难自禁地揪了把他的长发,想要让他听你的话。
吴琅的肉茎因为你的娇喘胀得发紫发硬,不仅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就连缠绕茎柱的青筋都在难耐地搏动。
他不像以往那幺急躁,只压着娇嫩的花唇,缓慢轻微地蹭动。
“嗯…你别……”
他又来吻你的唇,贪心地缠着小舌,吸吮津液。
浅缓的蹭动勾得你心痒,导致过往放浪作乐的记忆一通闪过脑中,让阖紧的花户渐渐变得濡湿,谄媚地吮吸着茎身。
你意识到自己身下的泥泞不堪,身体本能地颤了颤,心口却突突地跳着,既想要他又矛盾地想抗拒他。
吴琅靠在你肩头低喘着,感受到轻微翕动的花穴,撩人地问你:“馥馥,要不要狼奴肏你?”
见你隐忍地压下喘息,又倔强地不答,他稍微提了身子,让肉茎离开了淌水的花穴。
体内升起一阵巨大的空虚。你低了头,以一双可怜的水眸看着他,张了嘴却吐不出声。
其实,单一个眼神,他就被你惹得血脉贲张。
吴琅到底没忍住,直接深埋入底。
“啊……”
完美的嵌合令你和他不禁发出一声喟叹。
他试着抽出半截,你轻声吟哦,酥麻快感堪堪流窜,让你紧张地攀上他的肩膀。
狰狞的性器再次狠狠地顶入,又被用力地抽出,反反复复,进出不休。
乱颤的雪乳晃进他的眼里,他伸手便使坏地揉圆搓扁,给你增添丝丝缕缕的快感。
你难耐地喘着,染了花汁的红艳指甲在他健硕的背肌不留情地挠着。
他又低头含着了雪尖的红梅,贪婪吸吮起来。突然,他想起了你白日里与宴鹤春言笑晏晏的模样,嘴里的动作变成了粗暴的噬咬。
“狼奴…啊、不许,不许这般待我…嗯…疼……”又痛又爽的快活感让你的身子发颤,好似因着这颤才使得花穴紧缩、花液流了一股又一股。
“疼吗?馥馥不喜欢?不喜欢为何咬得我这般紧?”他自然是感受到了你温热花液的喷涌,故意这幺问你,又让劲腰愈加疯狂地挺动,力道大得有种要把你贯穿的趋势。
湿热穴肉仿佛裹不紧攻势凶悍的粗硬肉刃,只能任它放肆地在穴内冲撞。同时,穴里不争气地吐出了更多花液,进而让肉刃抽插得愈加迅猛。
飞溅的蜜液被捣成黏稠的白沫,淫靡地粘在粗硬的阴毛上,越发地显眼。
“嗯啊…狼奴、狼奴……别…好快…啊……”
身下娇人儿喘得厉害,吴琅受了鼓舞一般,继续埋头狠肏,整个床板震得吱呀吱呀响。
圆鼓的囊袋重重拍在腿根上,打得一片粉红。他尚不知足,掐紧你的细柳腰,一下又一下地撞到紧闭的宫口,恨不得一举深捅,把脆弱的宫口大力顶开,好让他深深地烙印。
被擡高的腿一晃又一晃地蹭着麦色劲腰,指甲也深深掐入皮肉里,只留下淡淡的月牙痕。你快慰地流着泪,嘴里不停地呻吟:“狼奴、狼奴…啊……”
一直到夜半,吴琅才死死地摁着你的腰,低吼着放了精关,让烫如岩浆的精水一股脑儿地射入了宫颈深处。
“啊……!”你一口咬上他的肩头,哆嗦着满是斑驳红痕的身子,久久未能平复情欲的躁热。
事后,你被他搂进怀里。本想挣脱他,但不小心摸到他身上的纵横突起。
你定眼看去,见到那些杂乱如箭羽般的疤痕,细细密密,大小不一地嵌在他的胸膛和腰腹上,有的已然陈旧,有的正在结痂。
伸了手,你欲触未触,指尖颤了又颤,哭音难掩:“这些…是何时伤的?”
“馥馥,莫哭…都是我为你挣下的功勋。”他看你的眼眸尽是柔情。
你扭过头不看他,胸口起伏不稳。偏头那一瞬泪光盈盈,比送他北上出征那时还要惹人心疼。
吴琅擡手轻轻抚去你的泪。但这幺几滴眼泪仿佛一下子就烫到了他的心,让他的手不住地颤了颤。
“…我因为炎陵的事迁怒你,你就不怨我?你说这些是不是为了让我哭一哭?”
“我没有怨你,也不想你哭…我只愿你能多笑一笑。”他的手指从你左手指缝中穿过,与你十指相扣。
你不再说话,埋进他怀里,依然是呜呜地哭噎了半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