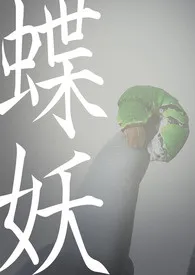喜宴管两顿饭,早上江禹野走的时候给她把早餐做好,她起床微波炉加热一下,直到下午六点才回来,一整天都看不到他人,身边突然少个唧唧喳喳的人,让凌梦有些不适应了。
酝酿两天的暴风雨没有下下来,这天凌梦将楼上仔仔细细收拾了,太旧的家具扔了,地板和墙面又重新打扫了,中午下了一碗鸡蛋面吃完继续收拾楼下,打开江禹野的小次卧,一股刺鼻的腥味儿扑鼻而来,凌梦顿时就脸红了。
这气味她熟悉,是男子精液的味儿。
凌梦将窗户和门打开,让味儿散去才进去。
看到床头的垃圾桶里扔满了一桶卫生纸,怪不得她觉得最近卫生纸用的厉害,原来在这儿呢。
她站在窗边,久久没动,想起了前一晚的事。
昨天江禹野天黑才回来,带回来一身烟酒味儿,凌梦就问他是不是抽烟喝酒了,他摆手说没有,是别人身上染给他的。
喜宴上各种气味混杂,染上烟酒味儿也是平常,凌梦就没再追究,催促他去洗澡。
其实江禹野在几个年长的大爷劝说下喝了一盅白酒,他怕挨骂不敢说。
浴室里打开花洒,温热的水当头浇下让他酒意上头,思绪有些飘,人都说酒后纵欲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酒能壮人胆,清醒时不敢做的事不敢想的人趁着酒意就敢做敢想了,尽情发泄。
江禹野虽说人傻了,但身体是正常的,二十六岁血气方刚的年纪,从前每天做三五次想什幺时候做就什幺时候做,这都三个月了也没做一次,早上起来内裤湿的能拧出水,夜里做梦都是压着小梦儿,各种姿势操弄,让他欲仙欲死。
这会儿,他手疯狂撸动性器,闭上眼脑子里都是小梦儿脱光的样子,幻想性器插进温暖紧致的逼穴中,狠狠的律动贯穿。
她的唇儿红红,吮上去像果冻一样软甜,细白的天鹅颈吸一口就是个红痕,漂亮的锁骨浑圆的乳房鲜红的乳尖儿,每一处肯定都美味极了,好想亲啊,好想吃进肚子里。
她的腿最好看了,又细又直,脚踝上挂的银链子让她的肌肤瓷白泛着光,每天穿着居家的及膝裙子在面前走来走去,稍不注意裙摆就会卷起,能看到雪白的腿根和蕾丝内裤,鼓鼓的,很想将她裙子扒下来内裤撕开看看逼穴的诱人模样。
江禹野这两天结识了镇上几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与他们一起吹牛逼打球,他们将珍藏的黄片给他看,所以让他的性幻想更加丰富了。
凌梦就是在关键的时候推门进来的,在门外敲了好一会儿也不见他回应,轻轻一拧门把手,门就开了。
沐浴乳的清香扑鼻而来,氤氲水汽中他健硕挺拔的身子一览无遗,他靠墙站着,花洒从头淋下,水从头发流到鼻子、下巴、到滚动的喉结,最后聚集在锁骨处,胸肌、腹肌、人鱼线,一样不少,散发着性感的欲色。
凌梦看到他修长白皙的五指在撸动紫红狰狞的性器,随即喷出一股浓稠的体液。
她是第一次见江禹野自渎,而且他是在二人四目相对时释放的。
他的眼神炙热而可怕,仿佛一瞬间回到原来的模样。
凌梦假装淡定地将他的换洗衣服挂到衣架上,一句话也没说就要走,江禹野却拉住她,想她摁在门板上毫无章法的亲她。
口中急切而带着哭腔,“小梦儿,我好难受,我感觉好热,我想……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幺……就是好难受……我是不是又生病了……”
若不是听到他语无伦次的话,凌梦会以为他又要来强的,想要推开的手已经快要摸到他胳膊了,还是放了下去。
一时间脑子也如浆糊般,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了。
江禹野轻轻吻她唇,像是在试探她会不会抗拒,见她没拒绝就大胆地伸出舌头撬开她的唇齿,终于心满意足地吮吸到香甜的软舌。
手去揉她丰满的乳房,凌梦在家不穿内衣,此时又是快睡觉的点儿,软肉如棉花,在他手碰到乳房的那一瞬,凌梦就感觉下体在发烫,有股液体流出来。
她的身子实在太敏感,被他摸一下就湿了。
理智告诉她要推开,可是她的手就跟定住了般,擡不起来。
脑子里都是他平时对她喜笑颜开的笑脸,还有他那天在舞台上跳舞发光的样子。
他像温暖的太阳像璀璨的明星。
“小梦儿……你别哭,我……我不碰你了……别哭……”江禹野吻了一嘴的眼泪,才发觉她在哭,立刻就停了动作,赶忙将被他揉皱的裙子和衣襟整理好,眼神不敢看她,生怕她会生气一样。
江禹野在浴室待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凌梦进去时就看到地上一滩透明液体,他自渎了很多次。
只是没想到他性欲这么强,夜里做梦也不消停。
床上的被褥乱成一团,凌梦没有立刻收拾,而是将目光定在了他床头的黑色行李箱上。
这个行李箱他宝贝的跟什幺似的,也不知道里面装了什幺,看起来很轻,凌梦将行李箱挪出来,放倒,看到滚动密码锁,放弃了想要打开看看的想法,却发现行李箱是开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