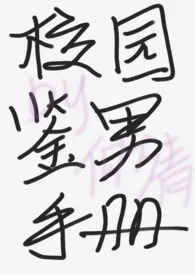一个月后,某一晚。高一寝室。
弟兄们围着一张床,将一个中年女人压在床上。现在是群狼捕猎,我们围捕了猎物,正想办法咬死她的脖子,让她丧失抵抗能力。
不要小瞧烈女的彪悍。别看我们一帮雄兽,要制服一个拼死抵抗的猎物,也有受伤的风险。
这中年女人性子烈,虽然被扒光了,但依然拳脚相加,能上嘴咬,就往死里咬。唐彪先前给她打上药,代价是手臂被啃下一块皮。
那九尺壮汉出去处理伤口了,我们少了一员猛将。中年女人疯了般抵抗,弟兄们都退开了。她已经挨了麻药,失身已注定,但谁也不想受伤。
压在这中年女人身上的,只剩下我。
“你行不行啊?”李晓修扯烂了她的漆黑内裤,很暴躁,“不行就下来,我搞她!”
我正坐在女人肚子上,拿枕头压住她的脸,防止她再咬人。她在枕头下嘶叫,两只手在我脸前扒扯,但我避开了。
她是一个高一学弟的妈妈。我是这么听说的。
这中年女人下午在球场找了李晓修麻烦,“护犊子的婊子妈”,李晓修说要操死她,就喊了人。
李猛当然要来,药只有他有,他也叫上了我,说晚上有乐子。
我压着身下的短发母亲,心想她儿子多半是被李晓修欺负了。这堂兄弟俩不是一类人,但在霸道上,没啥区别。
中年女人腰细腿长,牛仔裤把身材勾得惹眼,脚踩一双坡跟凉鞋,走起路来哒哒响。她回头时的眉宇飞扬,我今天刚见她,都呆了。
她和刘璐完全相反。如果刘璐是文文静静的冰山,那这女人就是热情的火焰。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独自前往孩子寝室时,那张自信满满的脸。
我一拳打在枕头上!中年女人闷声一哼,空中双手一僵,我再次打了一拳!又一拳……
“真狠……”李猛假意捂脸。李晓修切了一声,十分不屑。
我打了五拳。她双手终于摊在床上,牛仔裤滑落到脚踝。那双挣扎的大长腿也软了下来,没了动静。
我拿开枕头,女人微卷的短发分散开了。那英气逼人的脸上,眼睛半睁,没了神气,嘴唇湿漉漉的。
第一拳打下去的时侯,她胯下射出一点热液,漏到我裤子上。我抹了一把,竟也不是尿。
你也有小孩。我抹掉手上的水,想起某个小妇人。你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吗?我没声张。我跟这帮人混了一段时间,还是不喜欢他们的嘲笑声。
后来,他们叫我先上。不同于狼群让领头的下口,我搞定的人,就让我尝一口热的。
我伏在中年女人身上,完事了也不想下来。
她的性器和刘璐不同,颜色更深,没那么紧实,但褶痕绵密,而且更加潮湿。
她阴毛茂密,小腹下聚成一团,像是漆黑的丛林。
这个月以来,我跟着李猛尝过不少女人,但同学家长还是头一回。
这勾起了我一些回忆,但我没有任何不快。
我又抓起了中年女人的脚踝,脱了她的坡跟鞋。
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脚,脚趾精致修长,足弓的弧度近乎完美。
她儿子有眼福。我握住这阿姨的脚背,阳具夹在她的脚掌之间,上下撸动,很快送出第二发,弄得她牛仔裤上都是。
“你真够意思的。”一个兄弟看我完事,还不忘把她的坡跟鞋穿回去。
“可不止我想这么玩,”我把她的牛仔裤挂到床上,“大修是看上这阿姨的脚,才想搞她吧?”
李晓修不理会我的讨好,但这回总算没再抬杠。
自从李猛把我收入麾下,没有谁再和我过不去。对此不满的,只有他这个堂弟。
弟兄们叫他大修,我也跟着叫,但很难打消他的敌意。
这蛮牛不如他堂哥灵活,总是一根筋。
他想把我当废种看到底,毕竟玩了刘璐数月,都快腻了,不想突然改变态度。
李猛早不在寝室里了。他趁大家不注意,偷偷溜走了。
我多了个心眼,也不再在寝室逗留。床上那个自信的母亲,很快被一群男学生围起来,一晚过去,不晓得她会否还那么自信。
原来,李猛就在门口,嘴里叼着烟。见我出来,他问,“怎么样,这种三十好几的女人?”
“就是操一摊肉,”我系好裤带,“人都死过去了,完全没互动。”
“咱能玩到的哪个不是一摊肉,知足吧你。我是觉着可以了,脚还挺漂亮的,夹着也舒服。”李猛踩灭了烟。
他这么说,像是已经玩过了。但他明明裤子都没脱,碰都没碰那女人一下,就离开了。
我晓得他是看我那么玩才说的,先前的快意散了,“恶不恶心,脚能当饭吃?”李猛不是啥好人,便宜不占必有鬼。
“我就问你怎么样嘛,跟你那小女友比。”李猛坏笑。
“你不能这么比。”
他在说我的前女友。
我加入他们以后,李猛还是下手了。
那姑娘一次吃了三针,肚子里塞下了我们浓稠的问候。
她的脑袋也被搅成了一锅粥,几天都没清醒。
李猛没明说他怎么处理的,但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姑娘家长没有任何声音,送女儿去了医院。
可惜,被调来做医生的,是张亮平的手下。
“那还得是这摊肉,有女人味儿。”我俩低沉地笑。我其实不想笑,我在想李猛干嘛提前走了。
远离了宿舍楼,李猛才拽住我。他收起了笑。
“你很有眼色,张平,连大修那种不吃贿赂的傻逼,喜欢你也只是时间的事。”
我心里有些警觉,不理他这么说。“我倒是想问你,刚刚怎么不一起玩?萎了吗?”
“你不晓得,没做足功课,可不是谁都兴碰的啊。”
“那女的你认识?”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李猛说,“就算我爷爷还能要来一点裹脚布,碰见不经裹的,就要命啦。”
“她和你家很熟?”我悟过来。
“何止……大修会不会惹上麻烦,就看能不能及时认出她咯。”
李猛一脸厌恶,“谁叫他只用下半身思考,见着眼馋的,脱了裤子就上。这一次,我不会给他擦屁股,出了事,倒霉的也是我老舅。”
“你就不会被牵连吗?”
“你不了解我家。”李猛觉着我问得太多了。“张平,我现在才说这些,是因为彪哥不在。”
我对唐彪很有印象。和粗犷的外表不同,他是个缜密的人。
“如果说,大修是个脑袋长睾丸上的蛮子,纯一缺心眼儿,那彪哥一身的肥肉里,至少装了十个心眼子。他是我舅妈那边的人,不是我的。”
这堂兄弟原来不是一条心?我还在想,李猛已经靠近我。
“对了,我一直没问你。那天晚上,虽然你跪下了,但你一开始,是那么打算的吗?要是我不揭你老妈面子呢?”
他问得很刁,我还在思考怎么回答,李猛仔细看我,嘿嘿一笑,用力拍我的背。
“你不仅人狠,张平,还够聪明。我一心带你玩,不是没理由的,”他邀请,“我在找一个像彪哥那样的人。”
原来他是这个念头,我晓得他在说什么。
“你没碰那个女的,肯定憋了一肚子火,不泄一下吗?”我也晓得我在说什么。
我回复了邀请。
事到如今,养育我到大的小妇人,被视作邀人做客的乐子,和茶具水果一个性质。
“说起来你爹妈差点离异嘞,”李猛乐了,“你看,我还挽救了你的家庭!”淫笑声回响。
刘璐和张亮平和解了。她不离婚了。
自从我向李猛低头,每天都和他们勾搭在一起。刘璐以为母子俩的生活一如往常,所以当肚子里装满浓液,多一份近亲的,她又哪儿会晓得。
我照常星期五回家。生活一如往常,我们没有提那晚的事。她没有压抑自己不去提,好像真给忘记了,忘记自己的面子,在儿子面前被揭开过。
我看着刘璐冷冷的脸,没有任何破绽。
我有时候真的佩服她,装着装着,好像真吃下了迷倒自己的药,披上皇帝的新装。
但我不是看不见衣服的天真小孩了。
她做出披上衣服的动作,我就说这一身太漂亮了。
李猛已经不给她打针了,因为给予快乐的人,换回了我爸爸。妈妈想过这其中的关联吗?我不晓得她,我只晓得,张亮平把她彻底驯服了。
终于有一天,刘璐告诉我,她不离婚了。这个小妇人说这话时,还是坐在书房里,文文静静盘着腿,不暴露心情。
“这个决定是为你好。”妈妈语重心长。
她晓得我不会喜欢这个决定,所以上来就堵住我的嘴。
她说我正值高考,大人的矛盾可以日后再说。
而且爸爸在的话,条件更过得去,我大学后也有好处。
我就多了一句嘴,“那你呢?那个没道德的,你能接受了?”
冰山小姐看书,看都懒得看我。“妈妈的事,你别操心了。”
当初刘璐闹离婚,谁反对都没用,如今她又决定不分开,我又哪儿拦得住?
而且我没有不情愿。
我变了,有关妈妈的事,我不再挂心。
我吃掉了肉体的补偿,代餐她败给快感的爱。
妈妈晓得我恨透了爸爸,所以只要我在家,她都不会对丈夫表现亲近。如果张亮平找她说话,她就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
但这只是逢场作戏。
我晓得她只是在做给我看。她不过是一只被驯服的猫,那个男人带来的“快乐”,她就要离不开了。
我也在作戏。父子俩已经没了敌意,李猛叫我们握手言欢。我犯上的欲望他晓得,他分享的怪癖我晓得,只有妈妈什么也不晓得。
所以张亮平回了家,我们又过上老生活,装作一切都没有变。
李猛一伙人照旧,偶尔晚上来做客。
他告诉刘璐他没有药了,但她败倒在他身下,只说别给她丈夫发现。
这是感情上的报复,妈妈拿这一点自持,但我参与了每晚的做客,领教了她自我的催眠。
在刘璐心里,儿子一无所知,还当她是那个冰山小姐。
但是她在每个撅起屁股的晚上,那生育我的肉囊里,都会由我补上一点慰藉。
她更不晓得,张亮平是故意挑时间晚归,达成被她背叛的快感。
所有男人都有了默契,各取所需。
只有小妇人以为自己藏得好,挂着冷冷清清的面子,做我文文静静的母亲。她以为她还像以前那样,在诱惑的大棒下坚强不屈。
“拿儿子开这种玩笑,你恶不恶心?”那晚夫妻俩正火热,刘璐的底线都永远鲜明,“你怎么敢拿你亲儿子开涮?”
但我想这都过去了。
今晚的计划,本来是去药高一的英语老师,但李晓修看过他同学妈妈的脚,心生歹念。计划有变,我和李猛现在回家,还没有事先和张亮平说。
“当然更爱你……”
我们悄悄带上门,只听书房里,传出刘璐和张亮平的动静。
“一家之主,”她边说边喘,“行了吧?”刘璐把我带到大,我还从没听过她哄过男人。
没有前文,但我晓得她在回答啥问题。书房里传出湿腻的水声,像是舌头和舌头在你来我往。
儿子不在的时候,家里就没有冰山小姐了。那只有一只被驯服的老母猫。爸爸操妈妈,正常又不正常,无论问她多下贱的问题,她都乖乖回答。
我不在的时候,连书房都性欲翻腾,不会再有什么寡淡的小妇人,盘着腿,端坐在高脚凳上,守候儿子回家。
冰山小姐还盘着腿,但是不坐了,而是仰卧在高脚凳上。
她两只交叉的脚踝,被张亮平一手抓住,成了炮架子。
她头顶的发髻被揪着,男人挺着腰,阳具在她仰起的盆腔中,进进出出。
张亮平偷看了一眼门外,而刘璐深情地看着丈夫,不晓得自己儿子正站在身后,目睹她的痴态。
他取出一管蓝水,让她冷白的脸颊,泛起古怪红温。
这是她想要的,但她晓不晓得游戏背后的规则?
在她清醒的时候,丈夫和李猛是不会同时出现的。
除非不清醒。
“你还闹离婚吗?”张亮平大声问,故意说给人听。
三个月前,他苦苦哀求她,但刘璐笑得无奈,又那么笃定,儿子在场,无法忘怀,因为她扬起下巴,绝不低头,“我只要离婚。”
“还问?”一样是这小妇人,正舔他的乳头,像狗一样,“问上瘾了你?”
“老实说!”张亮平捏紧了刘璐的头发,用力插她。
“不离婚……!”她松开嘴,气息乱了。
“真的?”
“真的,我不离……!”被驯服的呻吟,“不离婚了……不离婚了!”
一双大白腿依旧盘着,交叉的双脚上下摇摆,高脚凳不停晃动,地板蹭得嘎嘎响,热液爬下凳子腿,流得满地都是。
我早先在学校里泄过的火,又燃起来,我由它燃着,因为一会儿还能再发泄。
书房的窗上溅上一片水珠。起热雾了,但没有人再画一个笑脸。
生活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她快乐,我快乐,他也快乐。
为了得到什么固定的东西,我们都被什么所教化,有的是规矩,有的是另类的规矩。
有人有分寸,有人忘了分寸,还有人被剥掉了分寸。
刘璐吸吮着涂抹快感的鱼钩,我不会取笑她,而是在央求鱼竿的道上拜叩。
我们都是被驯服的狗,盼着第二天的骨头,谁也别笑话谁。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