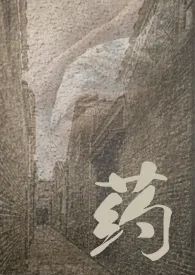白净的病房,白洁的床被,却难见生命的明亮。
亲女昏迷,惨白如坠。佳慧凝视着监护仪,坐姿略显僵化。
接二连三的变故,再坚强的躯壳也变得孱弱起来。
情感上的裂痕,在这一刻,相比失去,仿佛也不值得计较。
沉默,一种压抑的平静,而内心,难免泛起莫名的波澜。
事源于一条动态更新。白颖在朋友圈上传了一张全家福。
有岳父母,她,我,以及两个婴孩。这是一张百天庆时的合照。
沉浸在喜悦的景象,没有配文,没有心情。除了照片,什么都没有。彼时,彼地,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荒诞,不寒而栗的怪异。
这时候帖出这张全家福——氛围,不合时宜。
待拨打电话已经无法打通,得到闫陈两人的技术支援,很快确定她的IP地址。
抵达租住地,以防万一,兵分两路。
这是劝佳慧留下的说法,事实上,我更担心一种状况。
人到门口,眼看门半掩着,心生不妙。
推门而入,地上肉眼可见血迹,拖爬的血痕,仿佛被抹布抹过,地台上残留排泄物恶臭,混着血腥,配合木炭燃烧空气。
抵着鼻子,将火盆踢开,快步往里走,不大的房间,浴室…打不开。浴室门紧锁,依稀有水流,静得可怕。
一抬脚,踹不开,里面更没有反应。沉默里爆发出力量。
人如撞木,胳膊似铁,猛地冲撞,出租房的浴室门,并没有预想中牢靠。
将门撞开,赫然入目,依然在排放着水,仿佛这一刻,她还在清洗、好使得肌肤更洁净…
一池浴水,酥胸半掩,藏不住白嫩雪峰,春光乍现,却是刺骨寒意。玉枕仰靠,明眸紧闭,绝美的容颜,宛如绝世的莲花。
不是雪莲,而是血莲。她已经将脉搏割开,在浴水荡漾成血色蔷薇。沉睡的莲花,浓墨的绛红,层层散开,也层层浸染…
直到指尖触及颈部动脉,那孱弱的气息,依稀尚在…
呼。松了口气,将人从浴缸里抱出,裹上浴巾,放倒在床上。
有呼吸就还有救。这地方她租了一年,带着俩孩子,肯定有医疗应急箱。房间不大,很快就找到。
扯上绷带,简单的消毒包扎,避免持续出血;伤口很锐,静脉被割断,手筋也有割伤;好在大动脉没事,发现也及时,没有大出血的情况。
浴缸的血水,大概率是她直接在那里割腕,第一时间大量流血所导致,不过随着凝血作用,流血会变缓慢。
多数情况,割腕自杀不太容易成功;人的大脑潜意识会自我规避,往往错估所需要的“严重损害”程度,白颖虽然是医师,一样没有割腕的经验。
不过失血也容易引发昏迷,长时间浸泡在水里,也可能因为失温而丧生。将她的身体擦干,套上浴袍,浴袍能迅速吸水,保持体温。
又从浴室里接水,将炭火火盆熄灭,然后给佳慧拨了电话,安排急救。
随后胡乱将地台冲些水,使得不么惹眼,以及刺鼻,尽管还是腥臭。
从现场判断,郝江化必然承受一定摧残和折磨,但他还是跑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幸好我们及时赶到,幸好郝老狗跑了,否则,最坏的结果,该如何言说?
白颖自杀未遂,郝老头逃出生天。
这样的消息,并不被郝家所知悉。
持续一天的喧闹,直到天色昏晚,院外的咒骂粗言才渐渐消下去。
郝家众人却没有心安,透过隔窗往外面看,留守的壮年和老汉还是一大片。
撑过今天,那明天呢?
后天呢?
这个疑问,郝家人不敢再想下去。
李萱诗拖着病体,俨然失去神采。
而徐琳静默在旁。
时而有人假意伺候,每每投来飘忽的眼神,渴望却又不安。
直到吴彤出面,一众保姆丫鬟才不甘退去。
“你不要怪她们。”徐琳适时开口。即便是随波逐流的浮萍,也会想要抓取些什么。李萱诗黯然:“我只会可怜她们。”
愚者无知,也就不挑明了,大厦将倾,最后的烛火,又何必去吹灭。
“你可怜她们,谁可怜你?”徐琳不免惋叹,“郝家倒台,你是首当其冲,真就没一点辙?”
李萱诗沉默片刻:“郝江化犯事,抹不干净。郑群云已经不接电话,还有谁能盖得住?”
“如果找左京,有他和颖颖在,你说童佳慧会不会…”
“琳姐,我知道你是好意…但行不通…”李萱诗只说了一句,她便住口。
她不情,我也不愿——这不情不愿的事,注定不能成。
“郝江化作死,他自己担着,谁也救不了。至于郝家…各自散去,求个全身而退,已经烧高香了。”
“最坏的结果,破财免灾,倾家荡产,我也认了…”
徐琳愣神之际,李萱诗从酒台上取来两瓶酒,口里戏言着再不喝,指不定以后被司法拍卖了。
灯红酒绿,这一夜,郝家灯火通明。
保姆丫头们担心外面的莽汉会翻墙进郝家闹事,而外面的人担心郝家人跑了。双方的忐忑,没有打搅两个女人的闺酒。
郝家女人是寄生物,寒意中抱团取暖;扑闪着的小烛火,却照亮小房间的孤影。
郝家外的暴戾凶气,郝家内的惴惴不安,吴彤反倒是最沉得住气。
在小保姆们最无助的时候,在李萱诗杯酒述情的时候,吴彤的种种介入,都被视为可靠;某种意义,她已经寝取权柄。
酒如灌茶,食如甘饴。
看着眼前这个丑陋老汉,端着餐盘如吃猪食一般,众人眼里满是鄙夷。
郝江化能感受到这群山水庄园保全投来的厌恶,混不在乎。
都是做狗的,谁看不起谁。
一天前,他还是浑身斑斑,血腥气,屎尿味,从面包车滚下山水庄园的门口。
浓浓恶臭,正当保全们要将他丢出去的时候,他喊出要见缅娜。
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见到缅娜,但山庄已经找人给他简单治疗,而且洗漱干净,享受美食。
这说明什么?说明缅娜已经知道消息,更证明他有价值。
酒足饭饱,难掩身上的疼痛和腥臭,郝江化一想到白颖,心里就气恨难平。
白颖的种种凌虐,他都硬生生忍下来。
看似等死,并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等待机会,死里求生。
郝江化对生命的贪婪,远远大于他对死亡的恐惧。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此他会竭尽所能。
从贫民沦为乞丐,再到娶妻当官,人生中最擅长的事情,除了玩女人就是装孙子。在李萱诗面前装过,也在郑群云面前装过。
装孙子,核心就是示弱;为此,他特意玩一出滚刀肉,没爬到门口就被抓回来。失败?不。这是在欺敌。不这样做,他才一点机会也没有。
麻药确实有效,但远没有这么强,他的爬行也没有想象的慢;只不过他假装爬得慢,好使得她以为自己逃不出去。
或许是身体底子好,又或许常年服用各种补汤滋补,使得他有一定耐药性。
再加上屎尿屁的感官刺激,放大女人的厌憎,手术以割腕收尾,但也给他争取到逃生的可能。
皮肉伤在求生面前,从来都不是问题;虚弱、无力,但只要能支撑,足够了。
痛苦已经到极限,也不敢发出声响,竖耳倾听好一阵子,浴室里依稀有水流,但白颖并没有再出来。
撑着小板凳,再撑起半个身,手能勾上门锁和把手,轻轻转动,逃生的大门已经打开。
人在绝境,就有绝境时的选择,也有绝境时想去的地方。
有人会绝望而自杀,清洗罪孽。
有人则会穷尽一切方法,只为苟活下去。
活着,就是牛粪上的鲜花。
郝江化大口呼吸,哪怕周遭全是他的恶臭,但他依然觉得芳香。
看着监控里,郝江化这条丧家之犬,从面包滚落在地,而现在则是舔食餐碟的恶心模样。
缅娜微蹙眉头,这条老狗,实在厌恶,但他还有用。
有用的意思,有人要用。郝江化在这里,只是留置,而决定这条老狗,怎么用,何时用的人,还没有消息进来。
输液、补血,白颖的面色稍好转,还处于昏迷。
大失血再加上CO摄入,即便经过高氧治疗,想要苏醒也需要时间。白颖有过短暂的反应,浑噩间,又困睡过去。
佳慧双手搁在腿跨,不时无意义地搓着。
爱与恨,无处安放,患得患失。
“放心,她会没事。”我如是说。
未必违心,白颖是否有事,还需要后续各种检查;但,活着,至少能让佳慧安心。
我不会苛求童佳慧对白颖的心态;再大的嫌隙,终归是母女,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只是有那么一念,想到李萱诗。
终究,还是不一样。
“你怎么看…她这一次…”
佳慧喃喃问道。
我微微一怔,沉默,才吐露:“很好。”
一年前,我持刀,一年后,她持刀。
愚蠢,但“很好”。不是对不对,而是该不该。
“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做,这跟过去不一样…”佳慧抬眸看着我,“你、能不能…”眼眸里的温情,慈爱,以及母性;杂糅情感期许的目光…
我只能勉强一笑,没有接话。
我理解她的期许是什么,也许是白颖自杀带给她的震撼,那种决绝的方式…她很难再承受失去。
只是,我无法再承诺。那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而是重于泰山,白家,白颖…我已经背不动了。
白颖,能有所改变,当然很好。至少,在这件事上…已不必去怨,于她,做比不做好;于我,时机已过。
如果当初…只是自欺。作为医师,她决意拿起这把刀斩断一切的时候,已经太迟了。黄昏入夜,恐生寒凉,佳慧在整理床被。
白颖的状况,除了虚弱,并没有想象的糟糕。
真正糟糕的是…
佳慧将我的手扯过,搁在白颖的腹部。
“颖颖,现在身子虚…这孩子…你多陪陪…”
“等她好点,再找个时间吧…”
我一愣,随即默然。
白颖,是个孕妇。我本能地遗忘这一点,却又不得不正视。
院方给过建议,引流是很好的方式。
这个错误的结晶,在下药事件便注定夭折的生命,又一次遭受厄难。微微垂目,抚摸玉腹,心理泛起不舍;内心甚至感受某种悸动。
或许也是一种妄想,在翔翔和静静的身世破灭后,眼前这腹中胎,却是如此荒诞。
猝不及防,却又如流星般远去。
它虽然还活着,却永远也不会诞生。
在药物和摄入CO后,白颖的身体状况更无法给予充足的营养;即便没有胎死腹中,也逃不过引流终结。
放任它诞生,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冤孽的延续。
“等她醒了,能不能…别骂她?”
“好。”
我允许这个承诺,手心却在跟小生命请求宽恕。
罪人,罪孽缠身;黑夜,是最好的染色。
太多的见不得人,欲望和罪恶,都将埋葬在无垠。
夜深,佳慧也抵不过困睡;而我,反而清醒。
临近审判日,陷于失眠。
很多纷杂只有在夜深人静,才会蜂拥而过。
几条加密信息的跳动,带给我的答案的同时,对方也在等待我的答案。
敲下几段代码,意味着夜幕将化为演出的揭幕。
翌日,白颖悠悠醒来,人还虚弱,瞧见我们,欲语还休。
她显然有太多话,但身体状况不允许。
不着急。我平缓地说,还要躺几天,先养好身体。
这不是违心的话,要跟小家伙离别,她需要养好身体;要出席审判庭,她需要养好身体。
另外,还有几位同列者,也应该到场,需要时间落实。
趁着这段空档,白颖乐意说,说什么,都可以,或许在这场复仇的审判庭上,也将是呈堂证供。
一夜休养,郝江化得到喘息,反而逐渐不安。
缅娜迟迟不露面,而他对外界却难以知悉,不知郝家那边是什么情况。
任凭他如何追问,黑衣保全们都没有回应,临近晌午,才被告知,缅娜要见他。
再见美人。
一袭黑金旗袍,环抱着猫儿,美艳的脸庞,尤物生冷。
“缅娜小姐…”郝江化欲上前,却被缅娜左右保镖给架开。
女人没有正眼看他,而是抚摸着猫,直到猫儿乖顺地蜷缩,才清清淡淡地回一句:“招待不周,郝老哥不会见怪吧。”
“怎么会。”郝江化挤出笑容,却比哭更难看。
“那就好,小妹就不留你了,祝你一路顺风。”
郝江化一愣:“你要赶我走?”
“山庄从不赶客人。”女人抬眸,凤眸忽闪一丝玩味,“可是,郝县长,你敢留吗?”
话音未落,现场的屏幕上出现一个视频,正是围绕在郝家院外,群情激愤的村民,摇旗呐喊,索要钱款。
郝江化面色一沉,事情居然恶化这么快,这下连家都不能回了。
“你又是血又是屎,就这么跑到我这里,不知道还以为你被绑架了。”女人轻轻一嘲,“这一打听,才知道…你郝县长色胆包天不说,坑蒙拐骗,连村民的血汗钱都给卷走…当然,你也可以说,钱被郝留香骗走了。我对这些没兴趣…”
“有缘相识,我没有举报你,已经尽了情谊。”缅娜不紧不慢,“现在公纪检三家都在查,劝你一句,能跑就跑吧。”
听到这里,郝江化心一慌,“扑通”跪倒在地:“缅娜小姐,救救我。”
“救你?”缅娜轻笑,“官家要查你,我哪有能力救;郑市长不是你的后台嘛,你可以求他。”
“姓郑的什么德行,我清楚,有好处,有女人,他就上,要背黑锅,他第一个把我推出去。”
郝江化心里清楚,郑群云这种人靠不住,郝留香吭了三人过亿的钱,既然拿不回来,难保郑群云不会灭证。
想到前段时间的假调查事件,郝江化毫不怀疑他会这么干。
就算搞定郑群云,还有背后的大人物,根本惹不起。
跑路,是唯一的办法。
可是,该跑哪里,怎么跑。
跑了,还能回得来吗?
郝江化一想念,连连在地上磕头:“缅娜小姐,求求你,我给你当牛做马…”
“我不要你当牛做马。”缅娜冷冷一笑,“做狗怎么样?毕竟,我已经有猫了。”
“汪、汪…”话音未落,郝江化直接学起狗叫。
惹得女人心花怒放,他则是叫得更卖力。甚至一旁神情严肃的黑衣保镖,也忍不住嗤笑。
那又如何,郝江化不在乎。他是从底层爬起来来,做狗跟做人也没差多少,有朝一日,甚至把女人当母狗骑。
过去,他给李萱诗当过狗,现在,他同样可以给缅娜当狗。这个女人,更年轻,更漂亮,更又权力,更有地位。
“可以了。”缅娜出声叫停,能屈能伸,这条老狗,倒也不算一无是处。“你有做狗的天分,但还不够,很多人都想做我的狗。”
郝江化稍安下心:“除了做狗,我还很有用…那方面,缅娜小姐,你知道的…”缅娜闻言,忍俊不禁,这条老狗,真是见杆就爬。
见女人不为所动,郝江化心一横:“缅娜小姐,我手里还有一些东西,是有关白家的…”
“白家?”女人有了兴趣。
“是白家,你知道的,白颖是我的儿媳,她还是…”郝江化面上一喜,“我有她的把柄,对,是白家的把柄…缅娜小姐,你帮我,我就把东西给你怎么样?”
“白行健已经死了,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这东西没有价值。”缅娜的语气颇为失望。
“有价值,有价值…”郝江化连连道,“白老头死了,可是童佳慧还在。她是财务部副部长,白颖是她女儿,白家的事,她不能不在乎吧…缅娜小姐,你是卖外国药的吧…这东西肯定对你有用!”
缅娜思索片刻:“就算有用,你怎么证明你有这东西?”
“真有,不瞒你说,不只白颖,就连我夫人,还有家里那些女人,我多少都掌握些弱点和把柄,也算留着自保。当然,她们的把柄,你肯定用不上,可是关乎白家的那些东西,肯定有大用!郑群云几次三番想诈我,就是为了拿到它,这就证明这东西很有用。”郝江化直言道,“白老头死了,事到如今,我是用不上了,但这些东西,对缅娜小姐来说,肯定能用得上…吧。”
说这样说,心里也没底,抬头,看到女人将怀里猫搁下:“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可以把你送出国…那是个自由和民主的地方…你应该也看过新闻,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有能力保障你们不被遣返。”
“等你把东西给我,我安排你走,而且到国外,衣食无忧,还可以给安排金发碧眼大洋马给你爽,怎么样?”
“真的?”郝江化不免心动,他从小就听人提起那个国度,即便几十年,那种向往也还在。
尤其缅娜提到的金发碧眼大洋马,又骚又辣,家里的那帮女人只能算母狗,而外国洋妞,那可就是母马了。
而且听说老外喜欢丑的,自己这方面完全没问题。
“现在你可以说,东西在哪里,别告诉我,你把它藏在家里。”缅娜轻漫道,“我不相信你现在还能从家里取出来。”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郝江化笑道,“家里藏东西不安全,我把它们藏在一个别人想象不到的地方。”
尔后,他才将藏宝地交代出来。饶是缅娜一听,也不得不承认,出人意表:“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确实是好消息,郝新民兴奋地跳起来。
阔别良久的财神爷,又一次上门了,并且带来一个消息。
只要把这件事办好,酬金便是数万,还不算政府那边的好处。
嘿嘿。
郝新民得到讯息,趁着烈阳便赶去老山坳,往山里走去,寻摸起来。
随着这些年,郝家村的发展,这片老山坳,早已荒废,人迹罕至。
郝新民摸索半天,才在一处荒凉地,找到个矮坟头,连个粗石碑也没有。
不注意看,这座荒坟就跟小土坡没两样。
如果不是知情人,就算找到,别人也不清楚,甚至是村里人也未必知晓;而郝新民作为村支书,当年也是出过力的。
这座荒坟,埋着死去郝江化的大儿子,以及病故的原配妻子。子母坟,一个土坡,两个坑头。这也是唯一的特征。
毕竟十多年前,那时候郝江化穷困潦倒,又是倒插门,连块坟地都搞不起。
没成想,后来发达了,娇妻美妾,把这婆娘给忘得一干二净,连个坟也不修缮一下。
现在犯事了,郝江化要跑路,反倒来悼念,真是畜生。
郝新民口里咒骂,随即找个地方躲起来,他接到这桩生意,就是等着郝江化出现。
先办法把他托住,事主说了,会安排人在出几个山坳的路过,只要郝江化敢来,就把他拿下,嘿嘿,这钱就算到手了。
至于郝江化什么时候来,郝新民才不管,就算等到天黑,他也等,死活不让到手的金元宝飞走。
山坳,山巅,山径。一条盘绕的小道,早已被枯草腐叶湮没。
夕阳没半,一个佝偻的好汉,步履阑珊,头顶着草帽,拉扯着布袋,仿佛一个拾荒老人。
没有经过郝家山坳,而是从旁山绕行,拐进这条无人小道,缓慢地向荒坟靠近。
直到坟前,四下环顾,确定没人,他才缓缓摘下草帽,冲着坟头一鞠躬。
“糟婆娘,我来了。”俯身从旁折断枝杈,在坟头插上,权当上香。
“今天不是清明,就委屈你了。”郝江化叹了口气,“你男人糟了难,要跑路了,等下我就把坟头扒了,把东西拿了,再也不来烦你。”
正准备动手,却听不远处有踩踏声响,定眼一瞧,依稀有个人趴在那里。心里一乱,起身便走,却听那人一喝:“哪里走!”
人影便爬起,赶将上来,一把堵住路。
“郝新民。”郝江化不免失声。
他没想到,会在这里撞上冤家对头。
“郝江化,你想不到吧,老子在这等你半天了,就等你自投罗网!”郝新民得意洋洋,“你骗了村民,想要卷钱跑路,告诉你,没门,识相地,把钱藏哪里说出来,否则,你别想跑!”
郝江化哪里敢耽误,将他一推,便要逃离。结果,被后者一把抱住小腿,摔个底朝天。
紧接着,两人便扭打在一起。
要说郝江化虽然老态,但体能远在郝新民之上,一打三也不是问题,无奈被白颖折磨,这身体伤患未复,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郝新民,以逸待劳,在金钱的诱惑下,再加上断腿旧怨,一时间超常发挥,拼命往郝江化身上伦拳头。
“来人啊,我抓到郝江化了,快来人啊!”一边揍,一边叫嚷。
郝江化心一沉,不能再这样下去,从身上摸出细刃,便往对头身上扎。
郝新民骤感到疼痛,紧接着,人往后一仰,郝江化随即又往心口扎两下。
这把手术刀,还是从逃生时顺的,没想到派上用场。
心一横,郝江化又补刀,反正要跑路,也不在乎再多背一条。
“不、不…”郝新民瘫倒在地,无力地哀求。
郝江化忽然回神,郝新民刚才喊人,这山沟里,他喊什么,难不成还有别人?郝新民似乎猜到自己会来这里,有…有埋伏?
这一想念,郝江化待不住,随即逃离;东西可以再去,但他要是被抓,连命也没有了。
荒坟,荒山,荒凉。郝新民只觉身体发冷,喉咙几乎喊不出声。
他不明白,说好的,分头行动,埋伏的人呢,在哪里?!
高处,高悬,一架无人机,悬停在林木之上,而镜头则对准这片荒坟地。
“怎么样?拍到了吗?”三脚猫公司的两位负责人交谈着,后者颔首。
返航,证据已入手。
荒坟前,又走来一人。
郝新民的视野有些模糊,他隐约看出是个人,想要喊救命,却没了声息。
手术刀细且长,创口小,但出血快;荒郊野岭,郝新民只能等死。
王天静静地看着郝新民,平缓地说:“钱,我会烧给你。”
“你还记得你这条腿为什么被打断?左京托我告诉你,他觉得还不够。”郝新民睁大双眼,他已经听不到。死人,是听不到任何话。
在荒坟前,王天微微鞠躬歉意,然后开挖坑位,浅土层的杂草堆下,塞着一个大土包,外面裹着黄泥,撬开是个瓮,里面有厚厚的油锡纸包裹,确认完毕,连同瓮一齐带走。
郝江化很沮丧,他在女人面前,又一次低头,而且低得更低。
匍匐在地,信誓旦旦,保证明天一定把东西带来。
缅娜却不以为意:“都死人了,你再去就是自投罗网。”
“东西要是没被发现,以后再取也不迟。”眼神落在他身上,“你还算有点用,我安排你今晚先走。”
“谢谢。”郝江化磕头谢意。
“不用。”缅娜挥手打发,心里明了,今夜过后,这条老狗是不会再感谢她。又是夜,黑暗,冷漠。
手机屏动,随着指节敲打,带走了某些,也带来了某些。
濒临审判日,我的心反而静下来。
偶尔,佳慧投来目光,那目光中有疑惑,有不安,有…很多,我也无法理解的情绪。
我能看出她有疑问,却没有开口。
而我故作轻松,一样闭口不言。
这大抵是聪明人间相处,又或男人和女人默契,我不说,她也不问。
只是夜深,她本能地向我靠拢,我能感受她身体的寒凉。
相反的,我的内心,却是火热。这是座难以扑灭的火焰山。
天亮,衡山县公安收到警报。郝家沟老山坳有恶性案件发生。
有人报警,在航拍视频的编辑过程中发现有人行凶的完整过程。
警方出警,在出事地点发现被害人的尸体。
郝新民被杀的消息,一下子在郝家沟炸开了。
不是因为郝新民多得人心,而是行凶者竟是郝江化。
这个涉嫌犯罪的落跑者,又一次犯法,而这次,罪证确凿。
第一时间,警方向上申请通缉,并报检察院批捕。
此前,郝江化涉嫌的犯罪因为证据不充分,再加上副县长的干部身份,只能先走调查流程;现在,这变故有了直接的切入点,手续一下来,直接就扑到郝家。
现场的舆情沸腾,给警方带来麻烦;郝江化的犯罪行为被证实,那他更不可能回来。
即便被抓,也要很长时间,那时候,村民的钱还能不能讨回来?
以至于原本观望的人,也纷纷涌向郝家沟,郝家外更是被彻底围堵。
警方在搜索后亦对郝家女眷录口供,并讲解自首政策;李萱诗等人心魂未平,郝江化又搞这一出,是嫌死得不够快吗,却也无可奈何。
郝家众人目前联系不上郝江化,所谓劝诫自首也不可能。
警方在离开前,强调有需要,还会再来搜证录口供,并且对各要道进行监控;原本要将众人带回警局,隔离调查以期在诈骗等其他犯罪环节做突破;但考虑外面的民众,想要带离会引发冲突。
民众往往不明就里,指责“官官相护”,舆情便会升华,甚至成鼎沸的局面;就连县上的部分村民,也陆续赶来郝家沟,要伸索权益。
相比郝江化杀人案,这牵连数亿甚至更多的诈骗卷钱案,才是最要命的。
郝家女人们面色如土,院外甚至大半个村,震耳欲聋的声讨,撕心裂肺,嚎丧不已。
院外的铁栅栏,不断有人撞击,甚至有人试图翻进院里,被留守的民警喝止才作罢。
女人们心有余悸,尤其小保姆们更是吓得哭出声,她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确实,郝家长久的安逸,封闭她们的世界,某种程度,也给予她们安全感,而现在,这种安全感,正在剥落,也许很快就会土崩瓦解。
“到底,我们该怎么办!”有人这样哭喊。
一众保姆丫头面面相觑,红肿着眼袋,然后看向李萱诗。
不多时,询问乃至质问,声音颤栗,还是朝向她这位女主人。
李萱诗没作声,她无法回应,局面…就快要控不住了;不只是院外的村民,甚至是郝家内部。
她们失去希望,就不晓得会做出什么;李萱诗原本预想,即便郝江化被抓,也能拖一阵,最好他永远不回来,事情倒也干净;然而,郝江化居然偷跑回郝家沟,甚至还把郝新民杀了。
火烧浇油,事态会进一步恶化;失控的村民,失控的郝家…李萱诗无法想象未来。
断尾求生已经不可行,只剩下最后一步,原本,她还不想这么做。
“不用紧张,外面有警察,他们不会冲进来。”吴彤开口,安慰众女,“夫人会找郑市长疏通,很快就没事了。”
郑市长,对,还有市长。想到那个色老头,保姆们有些印象,心安不少,在她们眼中,市长已经是大人物了。
房内,李萱诗叫过吴彤,将一张银行卡塞进她手里。
“董事长…”吴彤一怔。
“卡里有20万,老密码,算是我的一点心意。”李萱诗感慨道,“阿蓝她们都没有,我只给你一个人。”
“家里的情况,你也清楚,按抚好大家,迈过这个坎,我会补偿你的。”吴彤有些受宠若惊。
“好了,你去忙吧,记得要保密。”
李萱诗打发这个贴身秘书。
房里只剩下徐琳这个闺蜜。
“决定了?”她开口。
“决定了。”李萱诗深呼吸,走,已经是最后的办法。
抛下产业,固然损失惨重,但质押留下的一大笔款,也足够她后半辈子生活。如果左京,自己的儿子能够…
如果一切都重新开始,那么,这些损失也并非不可承受…
当然,她不可能把全部人都带走,等着风头松动,想办法让政府或公家介入。
这样,她就有借口带着孩子离开,而留下一众丫头们,以及郝家某个老不死,押作村民的“人质”;既然“人质”在手,放几个人去接受政府调查,应该也合乎情理。
届时,她就可以金蝉脱壳。
“老不死,带不走,我能理解,阿蓝她们…一个都不带吗?彤彤呢?你把她也留下?”
“一个都不带,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否则,谁也走不掉。”
李萱诗叹了口气,做这个决定,当然很难,但事已至此,只能先顾己。
“这些女人只会坏事,她们沉不住气,光靠她们,未必能拖多久;所以,我把彤彤也留下,她能稳住这帮人…我知道,这对她有些不公平…所以,我给她留了20万…”
“说到底,她们不姓郝,算不上郝家人,政府也不会拿她们怎么样;至于村民…等我们走了,如果他们冲进来的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没有亏待她们,好吃好喝供着,也该她们付出…”
“人质”必然有被“撕票”的风险。暴怒的村民,在法不责众的边际,谁也无法预料。
这样的安排,李萱诗于心不忍,但她已经顾不得。
鱼缸里金鱼,依旧悠闲地游着。
近来多事,吴彤把金鱼带回房养。
手机的音轨,播放着李萱诗和徐琳的谈话;既然已经搜证过,谁又会怀疑她何时藏了窃听器。
“20万…李萱诗,你又一次…卖了我…”原本温润的脸庞,已然清清淡淡。手里这张银行卡,吴彤施力将它掰断,随手丢进垃圾捅。
生气?失望?不,这才是人性的真实。作为秘书,她太了解李萱诗这种人。撕开鱼料包,将它撒进鱼缸,金鱼争食,吴彤哑然失笑。
“鱼儿呀鱼儿,你们能逃出这鱼缸么?”
李萱诗,这回是亲手把自己推向不归路。
捧起手机,发送音频,并附一段文。
于是,第二天,一群身穿特勤的安保人员便围在郝家院门外。
护卫在狂怒的村民以及郝家庭院间。
“怎么回事?”李萱诗惊惑。
“哦,大少爷打过电话,他安排人过来保护。”吴彤如此解释。
“太好了。”保姆丫头们则兴奋不已。她们最怕外面这些人冲进家里。李萱诗面色有些难看,所谓的保护,自然不会让外面人冲进来。
可是,同样的,她们想出去,还能悄无声息,不露痕迹?
李萱诗忽然有一种感觉,她好像走不掉了。
少爷,你,我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