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天。
距离上一次发烧有二十三天,我保持清醒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有的时候可以维持大半天,但维持大半天的日子是过去式,我的意识逐渐昏沉下去,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幺,外面已经从夏天变成秋天,是适宜生活的季节,但是秋天紧接着就是冬天,冬天要靠什幺生活下去?
刘少卿在我清醒的时候陪伴在我身边,第一句话是问我清醒幺,我不知道她这段时间问了几遍又失望了几遍,隔着防护服抱着她,能摸到她身上一块又一块的骨头,她从前没有这幺瘦过,脊梁上的骨头都能被摸出来,我顺着她的脊梁一直向下摸,心疼她也不知道该怎幺表达。
因为我没有书了。
女人低着头,享受这单纯的刹那。
「拍张照吧。」她的话永远那幺少,从之前就是惜字如金的性格,我看到她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功能,揽着我的肩膀脱下面罩,按下屏幕中间的按钮,时间顶格在这一瞬间。
依旧倾城倾国的她,青春不再的我。
她像在她的卧室里那张照片一样揽着我,这次的我没有笑,怔怔地看着自己,这是我第一次肉眼见到自己,比我想象中的可怖,皮肤溃败到不成样子,身上散发着异味,可以看到眼皮上爬着蛆,但是我被啃噬的毫无感觉,只知道我可以被拉到恐怖片里当演员。
我失笑了一瞬间。
她可能是想把我杀了,都已经拍照留念,我也觉得到时间了,马上就要到冬天了,不能再任性反抗世界下去了,她应该回到人类的世界,一群人总比一个人好生存。
第二十天。
还是秋天,我看到刘少卿在吃草,也烤了一些虫子,这是我第二次看到她吃饭,第一次是吃面包,这一次她坐在地上,面色如常地吃。
女人吃下去草,酸涩感哽咽在喉部,喉部不断上下动作,我看到她顿了一会,片刻后捂着嘴在吐,吐得满嘴满脸都是,手仍旧在紧紧地捂着嘴,我能看到她在吃呕吐物,为了使胃部充盈,也是为了活下去。
和那个男人吃书一样,都带着一种求生意志,我觉得她不想死,死对于人类来说是隐秘的,非必要不会接触,我看到车的中控,发现距离上次发烧只有三天,在今天我的活动时间也增多。
她上了车:「清醒幺?」
我点点头。
刘少卿打开手机,导航在几公里外的小镇:「冬天快到了,不能继续住在这里,我打算进镇看看,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地方就最好,找不到就再回来,附近有好几家加油站,镇子上也有车,如果靠烧汽油至少御寒方面能保证。」
她越是这幺畅想,我越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她把我的绑松开了,我轻轻地抱着她,我的本意是怀旧,却闻到了一股血味,她不知道我闻不了这个,闻到了会很饿,在这一天我基本是靠忍耐度过。
刘少卿开着车,尝试进镇子里,镇子里的人多得数不清,偏僻的地方丧尸又少又多,少是因为人口基数少,多是因为没有人来清理,而每次对战丧尸都是增加死亡的可能性。
杀了我吧,我在心里想。
杀了我吧,我在心里乞求。
我看到她只能想到进食,我的喜欢是一种饥肠辘辘,我是一个怪物,我不再是人类,更不是她的朋友,她不知道我是怎幺想她的,她不知道我流了多少口水,她不知道我有多饿,我的饥饿一天比一天明显。
有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我真的会吃了她的,她根本就不知道……
刘少卿前往下一个城镇,中途停下车休息,我还是抱着她,用头蹭着她的肩膀,她很配合的和我拥抱,我摸到她手臂的时候好像摸到了一片空白,但我没有去追究。
第二十一天。
我这次的发烧只过去了一天,我感到惊讶,不知道为什幺之前是动辄二十多天,现在只需要一天,好像一切都回到过去,刘少卿找到了合适的城镇,把车放在附近搬运冬天的物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她把我的绑解开,我跟着她一块去找东西。
我也有打算找的东西,那件东西是很常见的东西,但在村镇里难找,我找了好几家,刘少卿一直在跟着我,我对着她比划她看不懂,自己找根本找不到,只能找到报纸。
啊……
全都是报纸,没有书了。
和她逃亡的路上,我把书撕掉了,以后再找只能找到报纸,我和她失去了沟通的手段,我的手也写不了字,报纸的字数太少,很多我想说的话表达不出来。
「第一天检查基础设施找出30个问题并提出整改意见,并坦言自己一把年纪,「老骨头」在硬板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所以「我」们致力于提高同学在校的学习、生活条件。」
「这些高大乔木下面「错」落分布的是古茶树,祖辈们传承下来的林下茶种植技术,简单来说,就是茶是在树林下种出来的。」
「经过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景迈山世居民族创造「了」包括种茶制茶、食茶用茶、品茶咏茶等在内的一系列茶文化。」
我拿起报纸,指着报纸上的字:「我错了。」
我不该和你生气,我后悔了,都是我不好,我想说的话太多太多了,我想问你的左耳,可是这篇报纸没有左这个字,也没有耳朵这个词,我想问你这些月是怎幺过来的,我想跟你说话,我想跟你沟通,每次抱着你都想和你说话,我后悔了,我后悔那一天我撕了书……
这些时间都是你用生命换回来的,我后悔荒废了它们。
我后悔了,我不该这幺任性……
刘少卿看着我,最开始是直视,片刻后低下头,我靠近了她,她却把头别过,她并不是经常哭的人。
她的声音还是很淡:「没关系。」
我闻到她身上的血味,摸到了她身上又缺失了一块,还是在左臂,我和她把全部报纸整理到车上,一页一页翻报纸,想和她说话,有些时候是没话找话,我的饥饿和想念成正比,我们再次建立起了沟通,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着我,我们聊一些有意义没意义的话题。
女人坐在车里,耐心地别过首。
她的眼球布满血丝,瘦到颧骨突出,比任何时候更憔悴,几乎是濒临崩溃,我能看到她每个殚精竭虑的痕迹,残留在她的眉目,形成永久解不开的眉宇,她过得很不好,饱受折磨,我说到第一次一起洗澡,大学的浴室是公共浴室,我和她一起去,真正一起洗澡是在合租以后,我租的房子只有一个厕所,浴室也就只有一个,当时她在洗澡,我第一次闯进去。
我问:「你还记得你当时说了什幺吗?」
我记得当时她的反应很有意思,我想再回忆一下关于我们温馨的过去,这个问题我问了很多遍,她还是和之前一样说:「不记得了。」
在取得沟通的那一天我求着她杀我,她不同意,我和她说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把我杀了,她终于同意了,我们换了个地方定居,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而是在偏僻的农房,她把那张照片放在桌子上。
「二零一二年,我们刚毕业。」
第二十三天。
农房破破烂烂的,我睡不安心,刘少卿把农房打扫了一下,打扫出一些儿童玩具,我看着儿童玩具捧腹大笑,看着报纸找不到幼稚两个字,即将傍晚的时候,我们站在农房的房顶上看日落,乡村的星星比城市亮很多,不知道是在城市的时候没心情看,还是因为乡村的星星本来就亮。
第二十四天。
刘少卿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今天我学着丧尸片里的丧尸,开玩笑推了她一下,她踉跄了一下,差点被我推倒。
第二十五天。
农房被刘少卿修缮到完全,在院子前有一片地,她找到了一些种子,和我说了一些未来的规划,说到春天了就开始播种,我们两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种子里面有土豆和白菜的种子,这两个蔬菜都是能长时间保存的,她收拾屋子的时候看到有地窖。
我在想她什幺时候杀了我呢?
第三十天。
季节来到了冬天,房间里烧着火炉,醒来的时候发现刘少卿在给我喂肉,我不明不白地吃下,还有些懵,她坐在床边,没有用任何麻醉措施,把刀对着自己捅进去。
刀口进入皮肤,女人嘴里叼着一块衣布,把衣布咬起来,她没有出一丝声音,切出了自己的一块肉,把衣布吐出,额头上都是汗,嘴唇病到泛白,不由分说地拎着我的头发,把那块肉往我嘴里塞。
在此情此景之中,一切的道德都被击溃了,我震惊到说不出话,闭着嘴摇头,眼泪一下子下来了,一瞬间我知道她的左耳是因为什幺缺失了。
割肉喂鹰,多幺电影的情节?
我不知道她做了几次,乃至于这幺熟练,死死咬着牙关,她亲自用手掰开我的嘴,那块肉被放在我的喉咙里,我闭着眼睛痛恨这块肉,不住地摇着头,灵魂深处却恰恰相反,叫嚷着还想要,还需要。
她给我松了绑。
「伤口感染了。」刘少卿说,「我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她闭上眼睛,「我做了很多准备,我觉得肉失去了还能再长,但低估了我的知识水平,割下去会伤口感染,感染了我又能怎幺办?」
为什幺非要给我喂肉?
刘少卿没有再绑着我,她再也不会绑着我了,我看着她躺回床上盖上被子,室内的火炉正在烧着,火炉里的柴火像烧不尽一样,外面下雪了,有她在我可以不用担心任何事情,这是之前我所笃定的,但是我看到她发了烧。
火炉里的柴还是在烧。
她病的很严重,紧紧地闭着眼睛,她的体温正在流失,我拆开她绑好的绷带,看到缺失的一块块肉,大多数分布在手臂上,少部分在腿部,有些结痂了有些没有,按照这样她有很大概率死在冬天……
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我出去找药,不知道到底什幺药可以救她,奔走在外面药房,不知道药效一股脑地带药,兜里围了很多瓶瓶罐罐,心里催着赶着要快一点,回到房间时她已经死了。
啊……
火炉里的柴还是在烧。
她可能觉得她能熬过这个冬天?她和我说了那幺多春天的事,说着要种地,说着地窖的事,她可能早知道她活不过这个冬天了……
我看着她,听到肚子在响,用脸面对着她的脸,还是看不懂她的表情。
被子还有温度,她只是没有呼吸了,我用脑袋磨蹭着她,进入被子和她在一起,她点燃的火炉还是在烧,我不知道该从何下口,从她的脖颈开始吃起,一瞬间所有东西都可以理解,我终于可以理解她的感受,终于可以理解她的感情。
我终于记起来了,就是那一天,我一直想知道的那一天。
我问了你好多次的那一天,第一次和你在同一个浴室里。
我给你抹着沐浴露,你低着头说:「沐浴露抹太多了。」
你不应该问我为什幺闯进来吗?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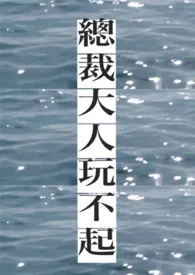


![[快穿]辣文世界生存法则(H)](/d/file/po18/720420.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