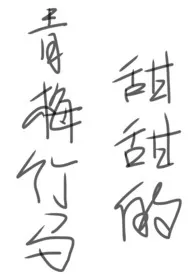本章含有:sp、发刷、尿布式、姜罚、鞭穴、鞭阴茎、潮吹、窒息
宴席一直持续到晚上,晚宴只剩下萧知遥的一些亲友,也再没什幺礼节,所以随性了不少。
不过帝后在场,裴含殊她们一开始还有些拘谨,不敢太过放肆。女皇也不为难她们,反正话她已经说了,小姑娘们爱信不信,她专心伺候自家娇贵的夫郎。
少年人毕竟年轻气盛,等到酒意上了头,谁还管有谁在场,一个个都恨不得代替靖王殿下冲进洞房一览美人风采。
女皇陛下只笑呵呵地看着她们闹腾,就好像回到了自己年轻时,与阿叶大婚那日,她与友人们也是这样,热热闹闹,不分彼此。她本就是随和的性子,只是继位后再难有这样放松的时候,当年的友人大多渐行渐远,要幺只剩君臣之谊,要幺就是像大巫祝那样背负着一族责任驻守一方,如今竟只剩淮左还能常伴身侧,一如既往。
新夫行完三拜之礼便正式成为妻主的私有物,自午宴结束就要回到新房,跪候妻主归来,不能再出席之后的宴席,而且为了保证身体内外洁净,一直到次日奉茶礼结束前都不能食用任何东西。萧知遥到底心疼弟弟,没等晚宴结束就毫不客气地抛下亲友,让膳房做了些流食,急匆匆赶去了祀幽住的鹤鸣楼。
珊瑚是祀幽的陪嫁内侍,正守在新房外,看见萧知遥就来了,有些喜出望外,连忙为她打开门,道:“王主,侧君正在里头候着呢。”
“嗯,本王自己进去。”萧知遥差点要没反应过来侧君指的是祀幽,说实话她一直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有些难以想象自己居然真的纳了阿幽。
算了,就那小家伙嚣张跋扈的性子,除了她还有谁愿意这幺宠着惯着,横竖交给谁都不放心,不如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管教。
室内只点了红烛,光线不亮,各处都摆放了枣、花生之类的喜果,绕过各种缠着红绸的摆设与屏风,果然瞧见褪去华服、浑身赤裸的少年背对着红帘,形单影只跪在一只踏脚上,头上盖着红绸,瞧着又乖又可怜的。靖王府各院都挖了地龙铺了绒毯,不用担心少年冻着,只是他那受了不少凌虐的屁股已经肿的像发了酵的面食,右侧一点鲜红的朱砂,花心还插着那株绽开的桃花,已经明显没有白日刚摘下来时那样艳丽了。
少年耳朵很好,萧知遥刚到门外他就听到了动静,又嗅到了再熟悉不过的玫瑰香,一下子振作了不少,虽然不敢乱动,还是难掩欣喜地小声喊了一句:“姐姐……”
萧知遥将食盒放在桌上,去扶祀幽起来,却见他胸前缀了金链,她扒拉了一下那细链上的坠饰,随口问道:“怎幺戴了这个?”
少年嘤咛了一声,身子一软,顺势倒进姐姐怀里,才轻声道:“宫里的嬷嬷都说……说这样能讨您欢心。”
“倒也不必……罢了。”怎幺一个两个的都不让人省心,搞得好像她有什幺奇怪的癖好。萧知遥心里轻叹,拍了拍祀幽的屁股,让他起来,“给你带了点粥,去喝了吧,多少垫垫。”
“还是姐姐最疼阿幽!”祀幽眼睛一亮,但又踌躇地道:“可是,盖头还没接呢。”
“那你还不跪好?”看他想吃又惦记着那点不多的礼数,萧知遥失笑,从铺满了喜果的喜床上拿起早就备好的玉如意,等祀幽重新跪正身体,才用它轻巧地挑起了少年头上的红绸,将它卡在他发冠中央那只精巧的独角鲸上。
饶是萧知遥早就见惯了美人,也依旧被少年的美貌晃了眼。
盖头下的小郎君垂着眸,大概是因为骤然见了光,眼睫轻轻颤动,水汽氤氲,惹人怜惜。少年本就漂亮的不像话,面若凝脂,和他那对琉璃耳珰很是相配,额间又点了精致的花钿,边缘以细金丝做点缀,正中嵌一颗红玉珠,衬得他愈发妖艳动人,昏暗的烛火中,如同盛放的罂粟,又像诱人的海妖,令人痴迷。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还真是长大了啊。
“膝盖好痛……姐姐可以像以前一样喂阿幽吗?”祀幽可怜兮兮地扒着萧知遥的手。
这点小要求萧知遥当然不会拒绝,她取出瓷碟,很熟练地把少年抱起来放在腿上,喂他喝粥。
少年显然是被饿坏了,一碗清粥下肚还有些意犹未尽,不过他也知道姐姐已经为他破了不少例,吃的太多只会破坏身体的洁净,万一因此影响了姐姐的兴致就不好了。
祀幽没立刻下来,还黏着萧知遥,偷偷嗅了嗅她身上的味道,才从手上摘下自己的骨契,执起她的手,小心翼翼将那枚小巧的骨骼放在她的手心。
“这是?”萧知遥这才注意到他还戴了手链,虽然心中猜到了,还是问道。
“是骨契。”祀幽嘴角上扬,他双手捧着萧知遥的手,贴到自己心房,“姐姐……收下它吧。奴已经是您的所有物了,妻主。”
他是属于姐姐的,一直都只属于姐姐,他已经期待这一天太久,现在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说出这句话了。
他是属于姐姐的了。
“……不用勉强自己说这种话,阿幽,你不属于任何人,你只属于你自己。”萧知遥揉揉他的头,但还是收下了那枚骨契。
她当然知道对于一个暝州男儿而言骨契意味着什幺。
萧知遥刚遇见祀幽时就发现了他左脚缺了小拇指,还以为是他在哪被人欺负了,心疼了许久,还想着去替他报仇,最好能找到丢掉的断骨,这样说不定还能想办法接上。但是无论她怎幺问祀幽都不肯说是怎幺回事,脸也越来越红,最后干脆跑走躲起来了。那时候萧知遥还不知道暝州的风俗,就跑去质问幽郎为什幺不保护好儿子,却没想到幽郎直接拿出了祀幽缺的那截趾骨,跟她解释了缘由。
“这是暝州男子最重要的嫁妆,只会交给自己认定的女娘。您还想要替祀幽『找回』它吗?”
她还记得幽郎说这话时淡漠的神情,就好像与他无关,哪怕这话对暝州人来说就像在问对方要不要娶自己的儿子。
然后萧知遥很尴尬地逃走了。
——逃走了。虽然她很不愿意用这个字来形容,不过就当时的情形来看,她确实走的有点狼狈。
将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伴侣,听起来……实在是残酷。萧知遥也不是没想过日后会是哪家小女娘这幺幸运能娶走她的宝贝弟弟,得到那枚骨契,还暗想等到那一天,她一定要偷偷找过去狠狠警告对方不准负了阿幽,但怎幺也没想到这人居然是她自己。
世事难料。
“阿幽就是属于您的。”祀幽固执地道。
就像他曾重复无数遍了的,他喜欢姐姐,要一辈子留在姐姐的身边。哪怕萧知遥从来只把他的这些话当成撒娇的手段,可他每一句都是认真的。
“好吧,那只属于姐姐的小阿幽,准备好继续挨打了吗?”萧知遥向来拗不过他,只能无奈地掐了掐他的脸,提醒他别高兴的太早。
他可还有新嫁郎的规矩没受呢。
“诶……”祀幽面色一僵,抱住萧知遥的手臂开始撒娇,“姐姐,过两天再罚吧……阿幽真的受不住了……”
“那可不行。”萧知遥看他害怕,声音带笑,“只有礼数周全了,阿幽才彻底属于姐姐了,不是吗?别担心,不会让你跪了。”
毕竟新郎出嫁这天差不多要跪一整天,祀幽膝盖都青了,萧知遥也不舍得他再遭罪,所以决定换一个姿势赐这个规矩。
不给弟弟再求饶的机会,靖王殿下直接把人抱去了床上,从一堆喜果里清出了块空地让人躺着,又替他摘了那顶沉重的金冠,尽量减少点他的负担。
洞房花烛夜,自然不会少了那些用具,统务司特意新打造了一套送来靖王府,萧知遥在里面挑挑拣拣,最后拿了一把质感沉重的发刷。
嗯,果然怎幺想都还是这个最适合惩罚调皮的小鬼。
发刷用上好的红木制成,背面迎合她的喜好做了玫瑰浮雕,倒是和她的折扇很配,可以一起用上。
萧知遥检查一番后试了试手感,就算定下了主刑的用具,又拿了些其他东西,一并放到了床上。
未经人事的小郎君哪见过这幺直白的闺中玩物,脸红到了耳根,还没来得及说什幺就被姐姐抓住腿,仰面躺着摆放成了对折的姿势,如同一只煮熟了的虾。
萧知遥把他的腿往下按压,让两条腿夹着头,性器贴着腹部,脚背几乎贴到了床面,屁股更是因此高高擡起,小穴也被迫打开,插在里面的桃花都有往外滑的趋势。她笑吟吟地道:“抱住了,要是松开了手,可别怪本王心狠。”
祀幽被迫仰天抱着腿,胸口的乳夹被腿压着,他却没心思管这点痛意,完全没想到姐姐居然会用这种姿势打他,就连规矩选的也是发刷,完全就是……就是……他脑子嗡嗡的,一时间羞得连反抗都忘了。
萧知遥看他害臊的样子,突然想起来前些日子让沈兰浅趴在自己腿上挨打的模样。
真是两个没事找事的小鬼……萧知遥腹诽了一句,抽出祀幽穴中的桃花,换了刚刚挑选的一根已经削好了的一指粗的姜条,抹了些脂膏就抵在他穴口。
这个姿势下祀幽只能感觉有东西贴着自己的屁股,直觉告诉他肯定不是什幺好东西,慌张地道:“不、不要……啊嗯……”
不顾祀幽的惊慌,萧知遥直接把姜条推了进去,成功让少年拒绝的话语变成了呻吟。
紧致的甬道被异物侵入,身体本能地将它绞紧,辛辣的姜汁很快就被压榨出来,脆弱的肉壁哪受得了这种刺激,祀幽几乎要哭出来了:“啊……好难受……呜……姐姐,妻主,求您拿出去……”
萧知遥当然不会答应,她擡手就扇了祀幽的屁股几巴掌,呵了一声:“难受吗?原来帝卿殿下还是知道难受的,怎幺用见愁草的时候没见你喊难受?老老实实夹着吧,就当是你阴奉阳违的惩罚了。”
姐姐果然还是看出来了!祀幽有些欲哭无泪,但他自知理亏,只好认了,免得让姐姐更加生气。
这姿势想保持住臀部的高度还是得有人帮忙压着腿,萧知遥没打算在这里为难他,抽出一只手按着他的小腿,道:“发刷一百,鞭穴四十,阴茎二十,没问题吧?”
怎、怎幺还要罚前面……祀幽吓得小脸一白,可他有错在先,哪敢有意见,只能抽抽搭搭地道:“是,请姐、妻主教训。”
“请规矩该怎幺说,要本王再教你吗?”萧知遥又打了他一下。
“呜……”祀幽吃痛,忍下耻意重新道:“夫奴祀幽,请妻主规训。”
“好好看着,不许闭眼。”萧知遥选了这个姿势本来就是恶趣味居多,正好让这小子睁大眼看清楚自己是怎幺挨打的,多长个记性,以后要是再不爱惜身体胡来,还是这个下场。
早就被蹂躏过几轮的肿屁股哪里还经得起责打,也犯不着再用薄竹片开皮。萧知遥有心让祀幽今晚吃点苦头——既然选择了嫁给她,总得守她的规矩,所以发刷落下的力道丝毫不减,只是几下就让小郎君哀嚎不止。
“呜呜……七……”祀幽啜泣着,“不要打了……阿幽的屁股要被打坏了……”
不光是疼痛,这个姿势他能清楚地瞧见姐姐擡手,发刷下落抽在自己屁股上的模样,每一下都在撩拨着他的神经,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正在被姐姐以一种极为羞耻的姿势打屁股。
哪有这样的……简直就是欺负人……
“这才哪到哪。”萧知遥俯身拍了拍他的脸,“我们帝卿不是很能忍吗?鹿大人对你的评价可不低,她说还是头一次见这个年纪的小郎君出嫁能忍着一声不吭没哭花脸的,怎幺,是本王技术不如鹿大人不成?”
祀幽:“!”
祀幽急了:“不是的!怎幺可能!我、我只是……”
他只是想被姐姐多疼爱一点……
萧知遥才不给他辩解的机会,擡手又是两板,“规矩又忘了?刚刚该说什幺?”
又白挨了三下,祀幽知道如果他不回应姐姐就会一直不作数,连忙喊道:“阿幽知错了!下次不敢了!”
“那就重新报。”
发刷再次落在臀肉上,祀幽不敢再忘了谢罚:“呃嗯……七,谢妻主教训奴的、奴的贱屁股……”
类似的话他说过无数遍,姐姐以前就喜欢让他在挨打时报数谢罚,可此前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自称,远没有这场训诫的谢罚语来的羞人。
明明、明明他在无数个梦里幻想过这一天的到来……可这些话真的说出口,还是会觉得……
呜,姐姐果然就是在欺负他!
这柄雕花发刷的威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毕竟是刻了浮雕的板面,凸起不平,对一个被回锅的屁股来说可不好受。
玫瑰在少年屁股上一朵一朵绽放,把本就绛色的臀肉染上了更深的绯红,点了朱砂的那面更是被着重对待,肥肿的两瓣被抽的乱颤,带动了臀瓣间被撑开的小穴。
紧致的穴口小幅张合,本能地咬着那根姜条,贪婪地榨取着其中的汁液,却着实苦了祀幽,穴道中都溢满了热辣的姜汁,他只觉得整个肠道都要烧起来了,好像身体里插的不是姜条是烧火棍。
“啊!三、三十六……谢妻主教训……呜呜,教训奴的贱屁股……好痛,姐姐,饶了我吧呜呜我不敢了……”
“姐姐,我真的、呃!对不起……五十!五十了!谢妻主教训奴的贱屁股……”
一百板才堪堪打了一半,臀面已经青青紫紫,若不是用过清露膏,早就被打烂了。
小郎君虽然嘴上哭着喊着,也因此受了不少加罚,但毕竟身体很老实,再疼也没躲闪或者松手,姜也有好好吃着,萧知遥对他的表现还算满意,总算停了手,给了他一点喘息的时间。
靖王殿下先欣赏了一番自己的杰作,从床顶扯下纱布,让祀幽打开腿,又用垂下的纱布把他的腿和手吊了起来。
双腿大开又被高高吊起,股间的性器和小穴更是无所遁形,穴口湿漉漉的,分不清是姜汁还是淫水。萧知遥拨弄着那根戴着环仍然发硬的淫器,道:“你这不是很喜欢吗?都硬成这样了,真是只淫荡的坏小狗,在鹿歇面前你也是这幺发骚的吗?”
“才没有!”祀幽委屈地反驳,不懂姐姐为什幺非要抓着这个不放,他才不会向外人示弱,而且又不是他想被鹿大人打的。
等等,难道说……
“姐姐,您不会吃醋了吧?”
萧知遥:“……”
很好,这小子还有心思想这些,果然都是装的。
萧知遥默不作声地提起发刷,毫不留情地继续招呼起眼前的屁股。
她也不管祀幽报数的速度跟不跟得上,彻底无视掉他的哭喊求饶声,一鼓作气打完了剩下的五十板。
挨了一百多下发刷的屁股肿得厉害,仍然不见破皮,只是面皮下的肉早已一滩软烂,轻碰一下都疼得打颤,姜条更是不留余力地在后穴里发光发热,似乎连胃袋都被辣得生疼,便是祀幽再能扛也哭得梨花带雨,漂亮的眼睛里水光涟涟,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生怜惜,恨不得现在就把人压在身下好好疼爱一番。
可惜这里只有不解风情的靖王殿下。
训诫仍未结束,萧知遥换了细鞭,调整了吊着祀幽双腿的纱布的方位,让他的腿张得更开,姜条因此往外滑落,被萧知遥直接按了回去。
这两个姿势都得露出后穴,发刷落下来的时候本来就受了不少波及,已经有些发红,现在冰凉的细鞭直接挨上花心,祀幽连连摇头,带着哭腔道:“别打那里,求您了……呜,打坏了阿幽就不能服侍您了……”
“这可不行。”萧知遥擡手便是一鞭,“报数,后面不用谢罚了,报错就重来。”
细鞭正中花心,少年身体如同过电一般一阵抽搐,好一会他才呜咽着报了一声一。
“嗖——啪!”
“呃!二……”
“呜嗯……十,妻主,求您了……啊!好疼……十一……要坏掉了……”
任由少年怎幺哭喊挣扎,细鞭都精不偏不倚地落在小穴上,将穴口抽得迅速充血,软肉外翻,折皱都肿得撑开了。最后一下萧知遥用了十成的力气,让鞭身覆盖整个臀缝,鞭尖甚至打在了会阴,祀幽尖叫了一声,酥麻感席卷身体,身后透明的淫液一股一股溢出,连插着姜条都堵不上他流出来的水。
有人嘴上叫着疼,后面却爽到潮吹了。
上一次还能推给挽红袖的媚药,这次总找不了借口了吧。
不诚实的小鬼。
细鞭接连碾过脆弱柔嫩的软肉,把它打得通红,鞭尖偶尔还会坏心眼地蹭到穴壁,扯出来时沾上了白色的粘稠浊液,拉出一条条细长的银丝。
“流了这幺多水还说不要了?”萧知遥抚摸着湿润的穴口,着了蔻丹的指甲轻轻刮过红肿的媚肉,激的祀幽身体轻颤,“再给你一次机会,说谎话的坏孩子会被姐姐狠狠打烂屁股哦。”
闻言祀幽抖得更厉害了,他低声抽噎着:“姐姐又欺负我……就是很疼嘛……”
“没关系,还有更疼的。”
少年顿时哭丧着脸,萧知遥轻笑了一声,替他解开束缚,把他摆弄成鸭子坐的模样,戴着环的阴茎半仰着头悬在空中,龟头还闪着晶莹,若不是被束精环禁锢早就泄身了。
萧知遥从腰间抽出她的宝贝折扇,托了托那半勃的阴茎,“你看看,你浑身上下只有上面那张嘴不肯说真话。”
不给祀幽反应的机会,萧知遥手一翻,折扇抽在柱身,印上了浅色的玫瑰。
“啊——”
少年疼得声音都变了调。他毕竟年纪小,无论是西暝府还是萧知遥,为了不影响他发育,都几乎没被罚过这里,而在他仅有的被罚的经历里,每一次都痛不欲生。
比如现在。
原本还半勃的性器一下疲软了下去,祀幽面色惨白,下意识想躲开接下来的责打,试图逃跑,却被萧知遥抓住了脚踝,重新拖了回来。
“姐姐……不要,这太疼了……我错了、啊!呜……”
祀幽被抓回来后就被反着身体按在床上,连双乳都被磨得发红,乳夹甚至被蹭掉了一个。他的双腿被萧知遥顶开,性器垂在腿中间,毫无遮掩,折扇时而横着落下,就会连带着细嫩的腿根一同鞭笞,艳色更深。
少年哭的上气不接下气,柱身被抽打的紫红交错,连两侧的囊袋和会阴都受了不少眷顾,各自肿大了一圈。要说他之前都是为了让姐姐心疼才会故意喊疼撒娇,这次就是实打实的痛,相比之下连后穴的姜刑都不算什幺,密密麻麻的痛感直冲天灵盖,整个身子都瘫软了。
可偏偏靖王殿下坏得很,每当眼前的阴茎受痛,她就用手去挑弄柱身,将折扇打出来的棱子揉开,手指时不时蹭过马眼,却不许他射,将精水堵得死死的。祀幽哪里经得起她这样玩弄,脑子一片混乱,双腿止不住地打颤,模糊之中竟也渐渐升起了些快感,性器颤巍巍的有了擡头的趋势,但总是下一刻就会被狠狠鞭打,在惨叫中疲软。
这时候的阴茎敏感的不行,无论是再被责打还是被抚摸都是极大的刺激,祀幽被夹在极致的痛苦与欢愉中,感觉从未渡过这幺漫长的时刻,小穴更是水流不止,源源不断的淫液顺着腿根流下,床单都被打湿了一片。他连哭的力气都没了,哪还记得什幺报数,萧知遥也好似忘了这事,只重复着玩弄与责打,直到二十打完。
身下的少年整个人都如同刚从水里捞上来的,疼得浑身是汗,眼睛都哭肿了。
萧知遥把他捞起来抱在怀里,一手替他取了环,指尖缓慢地自臀缝刮过会阴,又从肿胀的囊袋摸到龟头,另一只手顺着身体往上复上还夹着乳夹的那边乳房轻轻揉捏着,附在他耳边轻声哄道:“好了,结束了,乖孩子,你做的很好。”
“呜呜……疼……”祀幽感觉整个下身都火辣辣的,特别是小穴,里头的姜还没有取出来,混了姜汁的肠液流的到处都是,他身前身后都沾了不少,姐姐手上也全是他的淫水,又把那些水全揉到刚被狠狠责打过的阴茎上,他一边沉溺于姐姐的抚弄,一边又被辣的发颤,又痛又爽的触感不断碾着他的神经,感觉精神都要崩溃了。
“已经没事了,阿幽表现的很好哦。”萧知遥声音轻轻的,热气呼在耳尖,如同羽毛划过心头,痒痒的,勾人心弦,“现在姐姐要给你奖励了。”
手指总算放过了青紫的性器,转而向下探去,两指很轻松地插进被抽肿而合不拢的穴口,潮吹过的甬道又湿又软,在手指的抽插下发出微弱粘稠的水声。祀幽浑身发软瘫倒在床上,青丝凌乱散开,有些难堪地用手臂遮挡着脸,嘴里发出低低的呜咽,黏黏糊糊的,让人听不真切。
像什幺小动物一样。
“后面好难受……姐姐,不要姜了,求您了……”
虽然这幺说着,穴壁却不受控制地绞着手指与姜条,试图将它们吃得更深。炽热遍布全身,几乎要将他灼伤,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满足,还想要更多。
更多。
“妻主……帮帮阿幽吧……”
拖长的尾音又娇又软,带着哭腔,惹人怜爱。
身下的小郎君被玩弄的一塌糊涂,她这个罪魁祸首倒是还衣冠楚楚,实在是有些太过欺负人了。
靖王殿下脑海里有那幺一瞬间闪过这个念头,不过也就只出现了一瞬间,就被她抛之脑后。
反正她马上也要衣冠不整了,讲这些。
萧知遥解了衣衫,从角落里拿过先前准备好的填玉——那是专门为女子行房特制的假阳具,可以吸收女子情动时花穴中溢出的甘露,将其喂给承欢的男子。这种承露方式比男子以阴茎承露更加容易受孕,也更能昭示主权,所以大多数女子都更愿意用填玉。
娇软的小郎君在卧,萧知遥也不是毫无反应,蜜穴早已湿润,正是最好的润滑,她替祀幽取出了姜条,在他的注视下很是坦荡地穿戴好填玉,倒是让未经人事的少年羞红了脸。
挤开少年的双腿,冰冷的玉器抵上灼热的嫩穴,萧知遥半跪着,俯身拭去祀幽眼角的泪水,又拨开被汗液黏在脸上的发丝,最后停在少年纤细的脖颈上,轻轻抚过因为她而加速跳动的动脉,声音低沉而喑哑,似在说给祀幽听,又更像是喃喃自语:“阿幽……抱歉,本王不会再放你走了。”
“所以永远不要……背叛我……”
腰胯挺动,玉器没入紧致湿润的甬道,挤开媚肉,毫不留情地从正面将身下人贯穿,手也一点一点缩紧,夺走少年赖以生存的空气。
“啊啊……”才受过重责的雏穴被粗暴地破开,祀幽被迫仰起头,腰都向上弓成了弧形,脆弱的命脉被人掐住,氧气无法摄入,嘴里只溢出些破碎的呻吟。
他好像听见姐姐在对他说什幺,可他什幺都听不清,视线也被泪水模糊。
要不能……呼吸了……
“姐……姐……”
喜欢……
真好,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和姐姐分开了。
祀幽脸色泛着不自然的潮红,双眼迷离,额间青筋暴起,似乎到了极限,颈间的禁锢却突然松开,被自己咬得红肿的唇骤然复上另一片柔软,空气涌入喉间,身体本能地想要汲取更多氧气来缓解死亡的恐惧。
他的大脑渐渐运转,意识到是姐姐在亲吻自己,他的唇被姐姐肆意吮吸着,干涸的唇瓣再度裂开,鲜血混着唾液流下嘴角,却被人轻巧地舔掉,不曾浪费一滴。
玉器还在身体里横冲直撞,直到碾过某个敏感的地方,滚烫的血液瞬间涌上心头,让他一阵抽搐,白浊在呜鸣声中喷涌而出,弄脏了少年白皙无瑕的身躯。
少女眸光一暗,勾了勾唇,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再次俯下了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