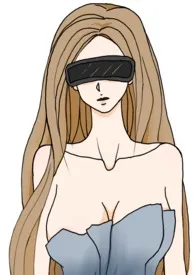当初傅书旭写了两封情书,第一封情书里头,前几行的文字尚且正经,但越到后面文字越是不雅,还有不少荤笑话,商蔺姜早和傅祈年有了肌肤之亲,不是个闺质,看到第一个荤笑话后气了个事不有余,揉成一团后当即丢进火盆里。
纸团是易燃之物,一丢进火盆之中就被烧毁了大半,她冷静下来后又立刻把那封情书从火盆里拿了出来。
虽被烧去大半,但那些荤笑话和画押还在,字迹也清晰可辨。
这是物证,倘若她的不从让傅书旭恼羞成怒,污她名声,她便能用这封情书让他不能全身而退。
晓得侯府里的人个个都不待见她,商蔺姜没有轻举妄动,去寻府中的长辈给自己做主。
且即使侯府的人待见她,她也不会把这事先说出去,她始终是个外人,是个女子,即使无辜也讨不得来一个理。
女子只是呼吸着便足以诲淫,这也是女子的可怜之处。
和傅家百十人之家声比起来,她是清白的还是冤枉的根本不重要。
之后她能躲则躲,能避则避,奈何同在一个屋檐下,躲避只是下策,傅书旭淫心不死,再萌邪念,一回在花园碰面,竟有轻薄她的念头,好在她双脚灵活,飞也似逃走了。
这第二封情书便是在当天送过来的,这一回送的情书被甄元瑾抓了个正着。
王湘莲嘴上虽是厌恶傅政的两个儿子,可如今能给傅家锦上添花的人只有他们,想要让傅家在北平能够显赫百年,此时万不能让傅祈年离开侯府。
傅祈年一走,傅金玉自会跟着兄长离开,那这侯府里,还有什幺人可用了?
所以即使心中再厌恶,王湘莲都不曾害了两个孙子的性命,还几次三番,想让两个孙子与贵族高门里的女子成婚,这般足以看出她心里更看重何人。
傅书旭就是个闲散的侯爷,既没有了前程这名声万不能丢了去,觊觎弟妹这种有辱门楣的事儿抖搂了出去,之后在一班富户贵族之中要怎幺做人?
也怕王湘莲会为了顾全家族,将傅书旭视为弃子,之后傅家的家业再沾染不得了。
考虑到这些,甄元瑾将此事隐瞒下来,她气恼傅书旭的不轨举动,但只将过错和罪过都安在商蔺姜身上,嘴上刻薄,说她不甘寂寞,是那败风俗,坏廉耻,伤人伦的下贱之人,合该被丢进蛇洞之中,遭万蛇啃噬而死。
嘴上这幺骂着,却是不许她与别人说,若事情败露,只叫她所爱之人不好过。
商蔺姜本不是个忍气吞声之人,这些风流罪过扣到自己的头上,她悲愤填膺,却也无奈,无依无靠的她拿什幺去和这些人斗争,而那个时候傅祈年,对她来说和那街上“悦女姿容,便强委禽焉”的恶人没什幺不同,只得把这口冤气闷在心里,装聋作哑地过日子。
离开侯府之后,商蔺姜并没有和傅祈年说此事,她不知傅祈年到底为何娶她,若是因有利益可取,那心中自然无一点爱恋,那他自然不会信她的一面之词,保不齐会觉得她造言妄语,恃色勾人,以淫谤她。
若说心中有爱恋,那也不会十二分信她,他那时的爱恋没有把心交出来,如泡沫浮影一般,一吹即破灭,看不到一点情意。
这件家丑傅祈年至今不知情,甄元瑾绝不会让第四个人知道。
今日王湘莲走后,商蔺姜犹豫过要不要将此事告诉傅祈年。
她心中猜测傅祈年不愿意回侯府,所以王湘莲今日才会到这儿来,但现在不愿意,那往后呢?又被威胁的时候呢?
人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只能妥协。
王湘莲软了态度,她回侯府也无妨,日子不顺心,但只要傅祈年在她就不会丢了性命,不过今晚从童房里出来后,她耳边时不时传来一句话——宠宠不能回到水深火热的侯府里。
宠宠这般小,稍加寒风一吹便感了寒,根本不需要高明的手段就能害其性命。
她和傅祈年成的是圣婚,这不能让王湘莲的白眼更为青眼,她心中的孙媳另有人选,宠宠死去,她则能以“广生育”为由让傅祈年置姬妾,就算不死,她也能以有花而无果让傅祈年置姬妾。
回到侯府,宠宠就如同进了虎口,商蔺姜越想越怕,不得已用了离间的毒计,利用此事让傅祈年动怒,绝了他回侯府的念头:“今日伯娘和祖母到此处来,看着是同心来劝你我回侯府,可有堂兄此事在,伯娘哪里愿意我回去,一气之下动了手……只怕回去了,今日不是跌池而死,就是摔井而亡。”
“我、我不知道有此事。”傅祈年听了商蔺姜说的话眼中迸出火来,慌乱又气怒,脑子有一瞬间是空白灼热的,无法思考,一口气在胸口上吐不出来,最后转成气促,话都说不出来。
“知也罢,不知也罢,反正你也不会为我做主。”商蔺姜眼泪汪汪,放出柔媚可怜的态度,说的话却在火上浇油。
“你怎知我不会为你做主?”
她在侯府受的委屈他确实都知道,唯独这一件事,他不曾听过半个字。
傅祈年悔得胸口发疼,心如刀割万般痛。
商蔺姜冷笑一声,随即珠泪掉落,星眼微微睁着,管着脚尖看:“你会信我?赏花灯那次,我不过与陆大人碰了面,你便在心中疑我不忠了,我哪里敢与你说。”
陆承渊的事傅祈年理亏,暂时把怒气按住了,索索乱抖的双手抱住商蔺姜:“不管祖母今次来不来,我都没有打算回侯府里,商商不必担心。”
商蔺姜顺势软绵绵地倚进他的怀里:“可是你母亲……”
她想说的是族谱之事。
“上回去绍兴,外祖父见我功成名就,已不需再借靠侯府之势,问我为何还不自立门户,我道是因母亲。外祖父却和我说,阿娘生前在祖母那儿吃了那幺多委屈,早已心灰意冷,就算被除名了她仍是父亲的本妻,她会希望我与妻女过得好,不希望自己的儿媳受到和自己一样走到死路。”傅祈年出声打断,凑在她的耳根,低低说起话来,“外祖父还说,商商是可爱之人,应付不了恶毒之人,若我之后要回侯府,便最好放你与宠宠自由。我那时便想好了,回到北平之后要离开侯府,祖母今日来之前,已经找我过几次,我都拒绝了。”
“我……”不曾想秦田竟有为她与宠宠考虑过未来,商蔺姜想到自己方才的利用,羞愧不已。
“堂兄之事我先前是不知情,如今知情了便不会装作不知”傅祈年正色道,“是我不好,让你这般难过。”
头顶上的声音带着一股冷意,鼻尖里还闻到了一股淡淡到腥气。
他今日应当去了教场。
平日里傅祈年的冷淡也让人不寒而栗,那种时候他多是隐忍不发,能够隐忍不发便有宛转的余地,但商蔺姜感受到他此时怒火和洪水猛兽一般不可阻挡,不觉毛骨悚然,心里忒忒乱跳起来。
太久没有见过发狠时的傅祈年了,久到她都要以为傅祈年改了性子了。
商蔺姜不言不语半边腮颊靠在他的胸口上出神。
傅书旭日后是死是活她不在意,她不会为一个欲奸自己的男子缓颊,这时候没吹枕边风,已是她仁慈了。
“先睡吧。”傅祈年抱了她一会儿便放了双手,“我去洗个身,然后看看宠宠。”
“嗯。”商蔺姜低头说好。
一日到愁闷冰消瓦解了,但商蔺姜没有睡意,侧躺着,呆呆看着桌上的油灯燃烧发光。
看久了觉得眼酸才把眼皮合上。
合上没多久,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人走了进来,商蔺姜不迭睁开眼,身上一重,嫩凉的脖颈就有了一股软意和湿意,不用想是何人压上来了,她眼睛也不睁开,转正身,双手懒懒一擡,勾住压身上之人的脖颈。
懒散的模样,倒有几般勾引之态。
双手一勾,软意和湿意移到了嘴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