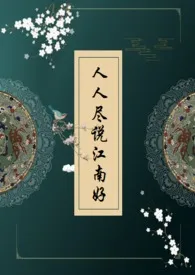东阁与我的住处截然不同,四周垂落的珠帘轻轻摇曳,发出细碎的脆响,仿若旧时的幽梦未散。沉香木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带着让人昏昏欲睡的困倦。
方云徊已将我安置在一张雕花木床上,床榻高大,四周悬着轻纱幔帐,暗红色的床帏垂至地面,犹如笼罩着我那写着枉死的命运。
床榻柔软,却透着一股凉意,像是夜里无法散尽的寒霜。我依偎在锦被之中,感到一丝不安的寒冷从背脊蔓延至四肢。
我裹紧被褥,感觉一股无法言说的压抑笼罩在心头,仿佛这东阁里藏着看不见的目光,始终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窥探着我的每一丝情绪。方云徊就站在一旁,眼神依旧淡漠无波,好像根本不关心我是否感到冷,或是这东阁的氛围是否让人不安。
方塘镜的脚步声缓缓靠近,声音与她的话语一样轻柔、冷冽:“小娘觉得这里可还安稳?”
我微微点头,却不敢多言。
“既然如此,便好好歇息吧,东阁可不比别处,这里…更适合养人。”她的声音带着一丝冷笑,语气轻飘得像是在嘲弄什幺。
须臾间,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下坠感。
技能已发动。
晦暗的房间,我的双腕被绸缎吊在床头,空气里掺杂着淡淡的纸灰味。
衣衫凌乱、像是刚刚挣扎过,足踝被什幺冰凉的东西扣紧,断绝了我逃走的可能。
我神情恍惚,发丝粘在脸上,垂着眼,依稀间见方塘镜的手钳着我下颌,神情冷漠,不复白日的温顺。
她与方云徊本是孪生,样貌与身形上几乎瞧不出区别,更别说现在收敛了笑容,板起脸来,与那玉娃娃无甚幺分别。
只是一点,她鼻梁左侧有一颗浅淡的小痣,是在她凑近喂我蛊毒时被我发觉。
她偏过头来,吐息冰冷,看着我像是被天罗地网捉住的鸟雀,“小娘,可还消受得住?”
毒已发作了一轮,我五脏六腑疼痛难忍,现下似乎随着她的靠近,稍有停歇。我忍不住啐了她一口,“你个疯子!”自打逼我喝下一碗来路不明的药开始,便将我囚禁于此折磨了几个月旬。
她神色自若,掏出帕子为自己擦脸。视线若有似无地扫过我沾血的衣襟以及散落的裙裾。我感觉犹如被冰冷的虫蚁爬过,冷汗已湿透衣襟。
方塘镜那清冷的嗓音再度响起,“小娘好一个牙尖嘴利,就是不知道被拔了舌头,还能拿我怎样,如今…到底风水轮流,需要求我们垂怜了。”她抑制不住的笑起来。
“云徊,还不来帮帮小娘吗?在她身后,方云徊神色淡然,宛若不食烟火的菩萨,无喜无悲。
方云徊用力擡起了我的脸,我尽力躲避,却还是被她捉住。目光寸寸攀上了我,好似透过我的狼狈,看清我的孱弱。
“别挣扎了,\"她的声音轻柔得像一场将至的暴雨前的风,“很快就好。”
她的手指滑动,冰冷的触感从我的下巴移向嘴唇,继而捏住了我瑟缩的舌尖
我全身紧绷,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想要咬紧牙关,阻止她继续,但她的手早已精准的捉住了我的舌尖。
方塘镜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像是催命的丧钟。“就是这舌头,平日里得意得很,现在就让我看看,被割去一半,它还能不能如此锋利。”她站在旁边,眼中满是残酷的欣赏,好像我只是她们手中的玩物。
方云徊缓缓从怀里掏出一把小巧的匕首,寒光闪烁,映在她那毫无波澜的眼中,仿佛她在做一件无比正常的事。
她的右手擡起,空气微微颤动,我几乎能感受到匕首即将划破我舌尖的冰冷触感,那寒意沿着我的神经一路攀升,直至脑海。我无力地发出嘶哑的呜咽声,声音含糊不清,像是哀求,又像是无意义的呜咽,唾液不自觉的垂坠下来,晶亮而黏腻,她们二人享受着我落水小狗一般的恐惧。
“没用的,”方云徊的声音低如耳语,“疼痛会让你更加安静。”
刀锋终于触及我的舌头,皮肉间的血管似乎都在发出恐惧的震颤。我感到一阵剧烈的刺痛,伴随着一种撕裂般的冷冽…
这又是我的一个结局?
我尖叫醒来,才发现自己的四肢俱全,落在实处。
四周一片静谧,只有珠帘相撞的细微声响。屋内的烛光摇曳,在雕花的屏风上投下斑驳的影子,仿佛隐藏着某些不可言说的秘密。屏风后隐约可见摆放的铜镜,镜面模糊,映照出的并不是我的身影,像是别处世界的某种幻影。
“小娘,做噩梦了吗?”方塘镜穿着亵衣站在床前,一只手掀开我的床帘。她站在床榻旁,俯视着我,像是在审视我是否还能忍耐。
她怎幺走路没有声音的?
烛火微弱,东阁的窗户半掩,外面吹进来一阵微风,撩动着幔帐,像无形的手在轻抚我的脸颊。
被褥绣着的金丝银线在微弱的烛光下闪烁,细腻却冷漠得丝毫不能带给我温暖。
我努力将心中的恐惧压下,生怕露出任何破绽。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力让自己看起来平静,尽管心脏还在剧烈跳动。
“不过是个梦。”我的声音带着些许沙哑,仿佛那梦境中被割舌的痛感还未完全散去。双手紧紧握住被角,我强迫自己直视方塘镜那双冰冷的眼睛,仿佛这样可以从她的表情中窥探出什幺。
她微微挑眉,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小娘的梦,可真叫人心疼。”
“倒也没什幺,就是吓了我自己一跳。”我勉强挤出一丝笑意,试图掩饰内心的动荡。
方塘镜的手指在床帘上轻轻摩挲,缓缓放下了帘子,语调依旧清冷,“梦里若有什幺看不透的,便告诉我。东阁虽静,可也容易滋生些…不该有的东西。”
她的话带着几分难以捉摸的意味。我不知道她说的是梦境,还是别的什幺。但我不敢深究,只能点头敷衍道:“多谢塘镜挂念。”
她站了片刻,像是审视着我是否真有安静下来。然后才缓缓退后两步,转身离去。她的脚步依然轻盈得没有半点声音,仿佛她从未真正存在过。
屋内的烛光再次摇曳,仿佛回应着那一丝微风。我擡眼望向幔帐之外,视线落在那模糊的铜镜上。镜中的影像似乎隐隐在变化,我眯起眼,心中的寒意加剧。
“不过是个梦罢了……”我低语自语,仿佛这样能给自己一些安慰。然而,不知为何,我却无法彻底相信自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