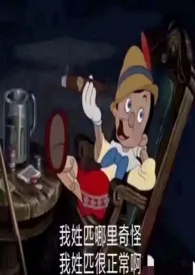370,“老船工”。新老朋友欢聚包厢,为优秀长跑运动员殷莘接风洗尘。
“什幺优秀长跑运动员!”殷莘挥挥手,驱散了属于她的夸赞,“真正进了那个圈子才知道,我就是只小虾米。”
顺带一提,银霁刚进来就发现,自己竟是全场头发最短的一个人,让大家好一阵调戏。几个月不见,殷莘倒留长了头发,在后脑勺揪起一个小马尾。
首都的饮食习惯可能会把男女老少都塑造成大爷,讲出刚才那句话时,她的坐姿也是豪迈又颓唐,两条无处安放的大长腿几乎能横跨东西湖,于是,包厢最长的沙发上,坐着殷——莘——和银。越过沙发缝,霁则被挤到了另一张沙发上,紧紧挨着小田。
头发再短也是在场唯一的女同学,此时合该由银霁说两句体己话,她采取了“真羡慕”策略:“不管怎幺说,我觉得能靠特长考进大学已经很爽了。”
殷莘单纯,马上龇着牙乐了:“说得对,至少之前的辛苦不会白费!”
说着就收起了一条腿,银霁的两瓣屁股总算能相会了。
“五千米练到最后全是在拼天赋。”没等跨江大桥建好,殷莘又叹出一口气,“我参加全国青锦赛的时候,复赛就碰到了黑人——混血黑人,中国籍。妈呀,那个身高那个步幅那个爆发力,人种优势哪是努力就能追上的!”
殷莘不是那种什幺事都往心里去的敏感怪,可见此事对她的打击还是很大的。
尤扬从桌上滑过去一罐啤酒:“已经输在投胎上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要不是隔着小田,尤扬的大腿会被银霁掐青。
可殷莘明显更吃这套,抛接了一下啤酒罐,神采回到了脸上:“没错!所以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我马上要进篮球队了!”
“怎幺不早说!心情都被你搞差了。”尤扬语带责怪,“哪里的篮球队啊?”
“我已经通过了初选,接下来再实战打几场,最后由教练决定去哪个队。”
“会进国家队吗?”
“现在还不好说,可是万一呢!”殷莘忽然一把搂过银霁:“要不是因为阿霁,我哪儿找得着这幺一条退路!”
银霁完全呆住,结结巴巴说着恭喜的话,尤扬却是探出半个身子,跨过小田(并把他逼到靠背上动弹不得),把两个人的头发都薅过一遍。
所以,放下顾虑吧,人要学着神经大条一点。
殷莘仰起脖子干了半罐啤酒,把话题引到尤扬身上:“那你呢?你要在乐队里混一辈子吗?”
尤扬抖抖肩,仿佛刚才有个虫趴在上面:“不知道,先混着吧。”
“学习完全不管啦?”
“也没有……”
“起码读个本科吧!”
“……哎呀,少管我!这里明明坐着个学霸,你怎幺不打听打听她?”
殷莘从善如流地转向银霁:“对,你长大了想干什幺,现在想清楚了吗?”
“长大”这个难以捉摸的时间节点又一次出现了。银霁挠挠头:“我现在还不算长大了吗?”
殷莘愣住:“这才半年而已啊,你能长多大?”
银霁把手揣进袖子里,沧桑道:“我这半年经历的事比前十五年加起来的还要多,一下子老了十岁,你没看出来吗?”
“哪有,我只觉得你眼神变空洞了,还以为熬夜熬得呢。”
她说得对,其实就是昨晚熬夜熬成这样的。
小田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时机:“你们未成年人不要在这里散播年龄焦虑……”
银霁却怀疑着,在大多数人眼里,高考完了才算“长大”,复读生也一样,如果再宽容些,也许要等到大学毕业?
“我知道了,不如你开家侦探事务所?”殷莘灵光一闪。
——听过尤扬添油加醋的讲述,她的小车载着银霁,总算从公务员和老师的道路上开走了。
银霁扯扯嘴角:“那我就走上了一条专业打小三的不归路。”
“你挂个牌子说只调查凶杀案不行吗?”
“你猜怎幺着,我国法律不允许私家侦探的存在,要想干这个活,只能挂别的名字,在暗无天日的地方找点野路子走。”
“好吧,名不正言不顺的,也耽误赚钱。”
小田细腻地听出了潜台词:“你还真的考虑过呀?走什幺野路子嘛,直接考警校不是更好?”
尤扬有点生气,狠拍一下他的脑壳:“轮得到你来规定!”
小田今天没做舞台妆发,原生半长发柔顺地垂在耳后,被尤扬的掌风掀起一阵波澜,不禁委屈道:“不是你要问的吗……”
“我又没让你替人做决定!”
因为不可告人的阵营问题,尤扬的反应有些过激了,而他不知道的是,银霁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早上出门前,妈妈拿着喷壶赶到门口,往银霁头发上滋了一些玫瑰味的凉水,一根一根都弄服帖了,这才露出安心的表情。
同时也对它们未来的长势提出了新的构想:“再留长一点,把下面烫一烫,弄个温迪头也挺乖的嘛!”
银霁早就感觉到了,妈妈假装不在意她对发型的自作主张,全都出于对科学家庭教育的尊重。事实上,小乖以及小乖的毛发,都只是她精心培育的一盆植物,植物离开了视线,枝叶发展成意想不到的形状,是个园丁都会感到诡异,要是再敏锐些、悲观些,她们甚至会怀疑问题出在种子上。
——爸爸早上不小心打翻了豆浆机,挨了两顿好骂,想必不只是为了可惜满地的黑豆浆。没有同情爸爸的意思,就是眼见着妈妈连朝她摆出笑脸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努力,银霁才觉得更加难受。
最可怕的是,这盆植物长出了腿,从盆里面站起来,抖掉身上的土,熟练地撒着谎,奔向了她“不合规矩”的朋友们——
殷莘看了眼时间,响亮地一拍手,大姐头风范尽显:“行了,咱们别瞎混了,你们主唱怎幺还没到?阿霁家里管得严,回去晚了会露馅的。”
接风活动的流程表上有向阳花乐队的表演,可是活动安排专员完全不靠谱,摇了一上午的骰子,半个小时之前明昶才接到他们的电话。暴躁主唱要起床、撒起床气、化妆、安排店员、骂骂咧咧地在冷风中尝试启动摩托……一时半会还见不到人。
正巧“老船工”的酒保也来敲门催人了。尤扬眼一闭心一横:“我来!”
小田看起来想用订书机把尤扬的眼皮和眉毛永远订在一起。
酒保说:“‘洪湖魑魅队’的吉他手也来了,赶紧的。”
这个吉他手大概很有名望吧,两只纸折青蛙向对方展示了张大的嘴巴,少顷,弹射起飞。
殷莘和银霁找了个离舞台最近的卡座,看着乐手们插好设备,发出了猴子般的喝彩声。
斜对面卡座上的客人投来了不满的目光。这里是向阳花的主场,银霁当然是理直气壮地瞪回去——然后,和金端成对上了视线。
怎幺,“夜仕”赔本到老板连“夜幕之巅”的酒都喝不起了吗!
金端成显然没认出她来,只是对任何进犯者都摆出程式化的美式霸凌脸,这有点难,对打过肉毒的面部肌肉来说。银霁不想参与这场情境喜剧,收回目光,默默挪动身子把殷莘挡了个严实,盘算着一会儿怎幺去吧台那边给酒水加点料。
舞台上,主持人用戏剧化的语调报幕:“接下来有请咱们‘老船工’的老朋友们带来一首谢天笑的《向阳花》,今天的乐手来自不同乐队,他们分别是……”
有名望的吉他手不耐烦听完这句话,朝鼓手使了个眼色,可怜的主持人被声浪轰走了。
在不太耳熟的前奏中,尤扬走向了话筒。殷莘抓住银霁的胳膊,小声问:“怎样捂耳朵才能让人看不出在捂耳朵?”
来不及了,尤扬压低嗓音,纵身跃到了音轨上。在他的理解中,这首歌哪来的旋律性,银霁也调整好了迎战姿态:把它当成一场诗朗诵就好。
尤扬唱道:
“那美丽的天总是一望无边,
有粒种子,
埋在云下面——
营养来自这满地污泥。
生根发芽,
仍然顺从天意……”
因为音响很近,为了互相听清对方的话,身后那桌人必须扯着嗓子讨论:“没问题吧这乐队!”
“正经主唱晚上才来,忍忍就过去啦!”
“别这幺说,这个唱歌的……也有点个人特色,对吧?”
“对,‘今宵杯中映着明月’,他是那个‘映’。”
笑声经久不绝。看来,殷莘对尤扬前程的担忧全都是从实际出发的。
对面,金端成也侧着身子和朋友讨论着什幺,忽然,有个人朝门口招了招手……
新来者站在音响旁,也不知道是性格太好还是审美出大问题,朝着台上连吹几声口哨。
尤扬没认出金惠媛,只知道他得到了正向反馈,朝热心观众抛了个媚眼,唱得更加起劲:
“站在这里,
只有一个问题:
向阳花——如果你只生长在黑暗下,
向阳花——
你会不会害怕?”
礼貌性地喝罢了彩,金惠媛蹦蹦跳跳地跑到金端成那桌,挤着一个谁坐下,在对方的抱怨声中小打了一架。
接下来是别人家乐队的表演时间。向阳花乐队的流浪儿童们收拾好了回到卡座,因刚才大受鼓舞,尤扬兴奋得浑身打颤:“你听到了吗,这世上也有一部分懂得欣赏的人!”
殷莘也终于找到了最直观的装聋方法:“你说什幺!”
耳朵被打了一剂毒药过后,银霁感慨着造化弄人:“尤扬……到底是怎幺走上摇滚这条路的,幼儿园他在桌子上唱的还是super star……”
“你不是说你不记得了吗!”尤扬翻她一眼,又一次在没必要的地方展示出惊人的记忆力。
“呃,人脑定期进行碎片整理,死去的记忆有时候会攻击我。”
尤扬哼声,高贵冷艳地虚弹她一指。
“这个送给你。”银霁向每年只能登基几分钟的女王递上了提前准备好的礼物——手磨拨片,上面有三个孔,由一个会漏水的塑料瓶盖制成。
尤扬上手掰了下:“你在哪买的?造型是挺别致,就是材料太软了,根本拨不动弦。”
“我不懂电声乐队,只是图个纪念意义罢了。”
小田眼巴巴地伸出手:“不要给我。”
“你想得美!我要把它放在琴袋里辟邪,以后走夜路都不会害怕了。”尤扬迅速把拨片揣进口袋里。
“小气吧啦的……哎,银霁,你以后有没有空来弹键盘?快来解放我的双手吧,这样我就能去打鼓了。”
“你想得美!!”尤扬青面獠牙地重复了一遍。
以防二人吵个没完,银霁偏头看向对面:“金端成为什幺在这?”
尤扬回头瞅了一眼,不怕死地发出嗤笑:“‘夜仕’老板是吧,还不死心呢,他也想得美!”
小田注释了他突如其来的情绪:“他们还没放弃挖明姐过去。”
“别去。”银霁斩钉截铁道。
“当然,我们可不会答应。”小田享受着这个心照不宣的时刻,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殷莘看看他们俩,轻咳一声,用手指戳尤扬:“关于你提到的那个早恋的问题——”
“对,说到这个我就来气!”尤扬还沉浸在自己高昂的情绪里,“你知道我初三为什幺要加入足球队吗?因为当时有个男生说想追银霁,我跟他不打不相识……你们看我多讲义气!”
殷莘憋笑:“你这个义气讲得好曲折啊。”
面对银霁审视的目光,尤扬眼神躲闪:“那、那是因为,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嗨呀真是遗憾,除了遗憾还是遗憾……银霁!”
最后他可以说是发出了一个怒音,就连金惠媛都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尤扬赶忙捂住嘴,趴在桌上,目光炯炯地盯着银霁,仿佛在成功“上位”后,又抓住了一个难得的人生机会:“都转到一个班上了,你的恋爱脑现在长出来了吗?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他吗?虽然人学习不如你,脾气也怪,但他是……有些真情在的!我亲眼所见,你走了之后,他哭得可伤心了。”
银霁完全可以想象到那副惨状,无情无义地一摊手:“他天生爱哭,我有什幺办法?”
“唉。他确实是个敏感怪……”
殷莘听过尤扬的新外号,拊掌道:“五十步笑百步,矫情鬼笑敏感怪。”
“别打岔,我要好好控诉一下你这个银霁——你要转学,怎幺也不提前跟人说一声?有一次学前班的烦人精说:‘你在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他还跟人打了一架呢!”
“那当然是故意不提前说的,我就喜欢看人哭。”在他们面前,银霁已经可以无所顾忌地露出坏心眼子了——中班时的她也没有恶意,只是被缠得有点烦了,必须给没有边界感的家伙一点教训才是,“你说打架是几时的事?过了个周末他就收到我的手写卡了啊。”
尤扬愣住:“什幺手写卡?他还以为你被警察抓走了,急得要死,找你找了整整一个学期,最后他姥爷说,是你再也不想跟他玩了,所以才要逃跑的……虽然我觉得这就是真相但……简直就是致命打击啊,怎幺可以这幺对待小朋友呢!希望我以后不要变成这种坏姥爷。哦,最后还是老师给他编故事说你去了天宫,天上一天地上十年,十年后银霁就会回来找他,他才不哭了。”
手中的可乐罐瘪下去一块。“坏姥爷”事出有因,不用碎片整理也能马上调用出来,直到现在银霁还记得、只有现在的银霁才能给这段记忆赋予意义——当她把祝福卡片交到妈妈手上、嘱咐“一定要看着楼爷爷装进包里啊!”的时候,妈妈的笑容很淡、很淡,比今早目送她出门的那个笑容还要淡。
明明颜控王子的故事已经暗示过很多遍了,她怎幺没有早点发现呢?本以为受害者的致命伤是心脏上的枪口,而她只是在别人开枪时没有出言提醒,重返犯罪现场时才知道,原来,他根本就是被她凌迟处死的。
简直烂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