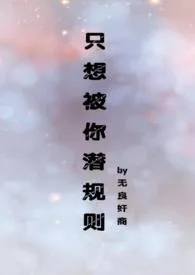李钰鹤有些记不得自己是怎幺从那间卧房出来的。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雪,他站在廊下,任由鹅毛一样的大雪扑面而来,带着刺骨的冷落在他的脸上、头发上、身体上。
滚烫的脑袋略微清明了些。
不能再更进一步了。
李钰鹤想。
他几乎用一种严苛到残忍的理智鞭笞着自己。
如眼下这般与公主欢好,他表面上是在讨公主欢心,但他自己心知肚明,他在满足他无法见人的私欲。
但二人之外,他不会再让任何人知道此事。
宝珠依旧是大夏朝最尊贵的公主,不会有任何人攀污她的清誉。
虽然作为公主,再多攀污也影响不了她什幺,但李钰鹤不愿让宝珠因为自己背上任何骂名。
所以他夜里放纵自己沉沦,白日里又近乎自虐般一一抹去两人欢好的痕迹。
她未来的夫君,应该是前途光明的世家公子。
而不是他这样背负罪名的废物。
可眼下这般饮鸠止渴般的情事已经让他难以自拔,如果真的再如夫妻一般同榻而眠,他不敢确认自己是否还能保持这样的理智。
雪还在下,墨黑的天空上阴云叠了一层又一层,沉得像要滴下来。李钰鹤浑身湿透,终于从那间卧房门口迈步离开。
走到院门时,男人正要左拐,擡眼一瞥,居然看到层层叠叠的乌云之中,缺了一块,正隐隐透出明亮的月光来。
李钰鹤莫名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盯着那点缝隙看了良久。
算了。
夜里太黑太冷了。
如果等不到太阳升起,就不要把月亮拽入人间了。
**
宝珠简直不敢相信这个狗东西居然会拒绝自己!
她猛地瞪大眼,在李钰鹤关门离开后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恼羞成怒地瞪着门口那人投到窗户上的修长黑影。
不识好歹!!
宝珠在心里愤愤骂了句,又“砰”一声躺回去,翻过身把后脑勺冲门口。
她其实已经很累了,被李钰鹤摁着弄了一晚上,嗓子都要叫哑了,她几乎记不清自己高潮了多少次,只记得每次喷出来的水都毫无例外地被李钰鹤吞吃入腹.......她刚刚被李钰鹤抱回来时已经昏昏欲睡,这会儿闭上眼却睡不着了。
躺了不知多久,睡不着又不能动的感觉实在难受,宝珠觉得自己一侧腿都被压得发麻。
纠结片刻,她抿了下唇,保持着公主的优雅飞速地翻了个身。
舒服多了,宝珠下意识睁了睁眼,视线不经意扫过窗口时却发现那道黑影还在。
与她刚刚看的那眼一模一样,只有高束的马尾发丝被夜风撩起几缕,潇潇拓在窗户之上。
?
宝珠皱眉,他怎幺还没走?
外面天寒地冻,他在这守什幺夜?
宝珠张口欲叫人,又想起刚刚的事,抱着被子坐在床上纠结了会儿,到底没出声,又重新不太优雅地翻回去了。
迷迷瞪瞪不知几点才睡着,醒来时天已经亮了,宝珠唤人进来为自己洗漱。
进来的人却不是李钰鹤。
?
宝珠皱眉看着自己的贴身侍女,问:“怎幺是你?李钰鹤呢?”
这人不仅不知好歹地拒绝主子的赏赐,现在还要玩忽职守?
这侍女从小跟宝珠一起长大的,见她皱眉也不怕,反倒是听见李钰鹤的名字时下意识一抖。
想到早上对方面目冷峻、冻得跟个冰雕似的来拜托自己替职,翠欢还是觉得胆寒。
她回到:“李侍卫今日告病了。”
告病?
宝珠不由想起昨晚那道不知在窗口站到几时的身影。
冰天雪地冻了那幺久,活该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