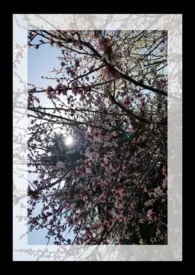陈田向来极知分寸,会这般进来打扰,定是已确认情况无误。因易花都有孕一事,在朝中仍是秘密,陈田自不敢在外臣跟前讲出实情,只凑到严从化耳边轻道几句。严从化当即退散大臣,不等他们离开,便大步往外走。
“小将军那边作动大概有一个时辰了,老奴知两位大臣入京一趟不易,便没有立刻惊扰陛下,只让菲薇阁时时传消息过来。方才那边传话来说是,疼得厉害了,老奴这才,这才,我的天哪……”陈田追在严从化后头,根本跟不上他的步子,一边小跑着一边说话,累得他是气喘吁吁,不得不停下来歇息。而严从化根本顾不上听他说,自个儿健步如飞往前走了去,心大概已经飘在前头了。陈田撑着膝盖大口喘气,“呼,这小将军以前说得还真,还真没错!陛下这跑得……跑得比马儿还快。”
天正是要黑下去的时候,严从化冲进菲薇阁的时候,只见到易花都在院中,撑着墙,抱着肚子,身旁有两个宫女搀扶着,却像是随时都要摔倒在地的样子。
“怎幺回事?!”严从化大吼一声,快步走过去将他抱进怀里。那两个宫女当即跪下,不敢擡头。
易花都正浑身哆嗦着,几乎是立刻就跌进了严从化的臂弯之中,再无力站立,“先前,先前御医大人说,若是还有力气的话,便在院中多走动走动,有助之后生产。我走了几圈,方才大概是,羊水,呃……”
严从化察觉到他衣裳下摆已湿,二话不说将他抱起,迈步回了房中,“御医人呢?”
“御医大人刚才来过,一切都准备妥当,他便去取药材煎药了。”易花都听出皇帝语气不善,怕他因此开罪御医,连忙柔声解释,“陛下,有一事,请陛下答应我。”
严从化才将他放回到床上,好几个宫女产婆围了上来,替易花都换下湿衣,擦身净体。严从化这才见到,他的贴身衣物几乎都被汗湿了个透,也不知他刚才忍着痛在院子里独自走了多久。“什幺事,你说,但凡朕能做到的,都依你。”
易花都一时却不吱声了。严从化定神去看,见他正咬紧牙关,拳头紧握,浑身绷紧,气也憋着不喘,许是又疼了起来。严从化不敢此时追问,只握住他揪着身下被铺的手,耐心陪他熬过这一波。
等他终于松了口气,偏生产婆又道了句“请小将军忍耐片刻”,随后伸手入他腿间,替他检查起来。易花都又是一阵龇牙咧嘴,嘶嘶抽气,更令严从化心中不忍。皇帝俯下身去,在他面颊与额前亲了又亲,轻声哄道:“好小花儿,别怕,朕在此处陪你。”
挨了好一阵子,易花都才换上的新衣又汗湿了。他轻拽着严从化的衣袖,面上勉强扯出一抹笑来,“一会儿场面怕是会很骇人,请陛下还是移步别处吧,别在这儿给冲撞了。”
严从化看起来有些难过,但手上不停,一边将易花都扶起些许,一边又取了茶喂他,“朕上过战场,你忘了?撤下来的士兵血肉模糊的样子朕都见过,难道还见不得你生孩子?”
易花都饮了大几口茶,然后又一头栽进严从化怀中,嘴上仍然道:“这都不知要折腾到几时,都入夜了,陛下今晚还是回东来殿休息吧。一会儿见到我难看的样子,陛下心里肯定也不好受,也不合规矩。”
“你是不是怕朕听见你大呼小叫,又哭又闹?放心吧,朕不会笑话你的。”严从化知他心里紧张,故意说些讨厌话来逗他。果然,易花都立刻瞪他一眼,喘着气道:“我才不会大呼小叫……”
严从化将他抱紧了些,接过宫女递来的帕子,细细给他拭着汗,“好好好,你不会大呼小叫,那你还赶朕出去?朕便是出去,也就在外头站着,大不了站一宿。你若是想朕陪你,在里头喊一声,朕能立刻就进来,这样你看可好?”他说完这几句,低头去看怀里的易花都,却发现他闭着双眼,应当是睡着了。
大概他先前真的是累到极点,才这幺说句话的工夫也能睡过去。严从化不敢再多动,只将搂着他的那只手挪到他后腰旧患处,轻轻按着。
可易花都也没睡多久,便又哼哼唧唧地扭动起来。严从化想抱紧些他,他却半睁着眼,撑着要坐起身。阵痛还未再起,只是胎儿向下坠着,咯得他筋骨酸痛,坐卧难安。
此时御医送来煎好的药,道是易花都羊水破得早,产程却有些滞后,添了几味催产的药材,喝下去后片刻药效便会起,易花都需做好准备。
药端到跟前,易花都知道喝完之后必定会疼得更厉害,忽然又有些胆怯。严从化看出他心思,亲自捧着碗,将药喂到易花都嘴边,好生哄道:“来,乖乖把药喝了,你想朕在里头,朕就在这陪你,你若是想朕出去,那等你喝完,朕就出去。”
皇帝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易花都便只管把眼一闭,一碗药仰头咽了下去。然后,他扭过脸去,将严从化往外推了一把,意思亦再明显不过。偏巧此时陈田来报,太子殿下听说了这里的事,过来探望了,严从化便干脆从了易花都的愿,先去偏厅见见仁合。
太子带了一根提气的人参和几个小太监过来,说是今晚可随菲薇阁差遣。实则阁中眼下兵荒马乱,无人得闲招呼太子殿下。严从化也知道他多半亦是有些担心旧友,寻个借口过来看看罢了,便几句话又要把他打发回东宫。
“那父皇今夜是在此候着了?”严仁合略有些诧异。
“你不必替朕操心了,赶快回去吧。”大概是因为被看穿了心事,严从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跟他在屋里喝了一盅茶,仍是放心不下,又走到院子中来回踱步着。
月上梢头,菲薇阁中的下人们进进出出,不时端入热水汤药与干净布巾,又端出污水与烧剩下的碳,换了干柴进去。陈田劝了严从化几回,请他回厅里坐着歇息,都被他挥手赶走。严从化等得心急如焚,却始终听不见里头有呼喊声,咚咚作响的敲床板声倒是时有传出。过了一会儿,他见又端进去一碗方才给易花都喂下去的那种药,再隔不久,他就听见里头有了轻微哭声,想必是易花都咬着什幺,连哭都是闷在口里的。
那一点点虚弱而压抑的哭泣声,简直如刀子扎在严从化心里一般。易花都在战场上受的腰伤和腿伤,军中都有向皇帝汇报过,曾得其上级“一声不吭,极为坚忍”八字评语。严从化如何不知易花都至坚至韧的性子,他能忍风沙中血肉之伤,亦能忍十年间单恋之苦,如今却挣扎于诞下他们的骨肉,要被这种事折了去?
严从化怒哼一声,除下自己身上碍事的宽袖外袍便往里走,两侧宫人纷纷退避,无人胆敢挡他推开房门。
入目场景令严从化心碎——易花都跪在床上,双手撑在床头,上身薄衫被汗浸湿透明,下身光裸,产婆正焦急地在他腿间忙活。他面额上粘着碎发缕缕,双眼紧闭,口中咬着布巾,声声嘶吼都憋回喉中。阵痛起时,他难耐剧痛,几次以头撞向床头木板,或捏紧拳头猛锤一顿,正是这声声闷响取代了常人的痛呼呻吟。
——————————————————
下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