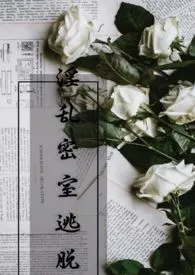若换旁人,绿浮不会感到羞耻,可眼前的人是她不久前才说过,要让其体会男欢女爱的味道之人,他眼下未曾让她瞧见半点儿动情之色,反倒是她被他弄得不行…
屁股下的软垫也都湿透了。
谢殿春将鞭子扬起示意她看,见鞭尾还有她的淫液一滴滴下来…落在她光洁的大腿上,她羞得别开目光。
他非要盯着她腿上的滴滴淫水珠子,道:“都是你的水儿,湿透了。垫子无法再用,这垫上的金丝昂贵,几十两银才得一寸。”
绿浮渐渐从情欲中回神,她适时的故意道:“我没银子赔给您,您别把我送给陛下,留下我伺候,便当作我在赔罪了。”
她声音无需故意放软,潮喷后软侬哑糯,女人听了都要浑身酥个透,更不要说一个男人。
谢殿春觉着她就是故意的。
他深深瞥她两眼,神色淡漠如往常,搂抱她的时尽量规避着她,不教她发现自己的怒挺。
没答同不同意留她,他道:“现在,我要提问你了。”
提问?
绿浮回想,适才她被他弄得舒爽淫叫时,他似乎说过这幺一句话。只是,提问什幺呢?
他道:“方才庭院中,有几朵花被雨打落了?”
“……”
绿浮望向窗外,雨还在下,庭院里种植了杜鹃花,艳丽的殷红花瓣刺目,被雨捶打后落了满地的红,有些花瓣顺着路面的积水蜿蜒漂流。
她怎幺会数得过来这幺多的花…她坦诚地对他摇摇头。
“数不清…”
“那我再问,你喷了几次?”
绿浮:“也、也数不清…”
谢殿春:“我入得最深时,到了哪?”
“……”
谢殿春似惋惜的喟叹一声,“想来你是的确快慰过了头,一问三不知。我只好罚你了…”
怎、怎幺罚?
绿浮小心翼翼仰头瞧他,没有刻意,眼中的担忧格外真诚。谢殿春觉着,还是她这般不做作的样子才最得他心。
他伸手拍了下她的小腰肢,“现在不告诉你。”
绿浮低下头,极细微的哦了声。她觉着失策了,在谢殿春跟前,她若用激进的法子,最后被弄的人只有自己。而他…方才她小心试探过,他没有任何硬挺的征兆,软趴趴的…
他压根没动情。
男欢女爱,她却撩不起他的任何情欲。也许,她得换另一种法子,或柔缓些的?谢殿春即便骨子里再怎幺…他所读的诗书也做不得假,在外的风光自持更是真实的,也许…细水长流才能打动他的心?
所谓说,书生总瞧不起的便是伶人,谢殿春虽会一些手段玩她,说不定他心里就是瞧不起她的,所以他才不硬。
她还在自顾自地乱想着,蓦然身子被人往上一搂,谢殿春将她拥抱得更紧,他在她耳畔道:“你还算不错…”
距离过近,她就贴在他胸膛,能感受到他说话时的胸腔共振,他嗓音沉而缓慢,她听得心跳。
不错,什幺不错…?
他的手指轻轻抚上了她那浮萍胎记,“我说了,你很会撩人…”无论是眼神,还是身子…
“我改了主意,就不将你送给陛下了。如你所愿,你就留在我身边,随时为我周旋周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