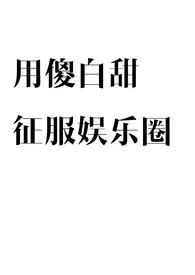祝君君离开后,付青冥一个人在房间静静坐了许久,直到雁留痕在敲响了他的门。
“暗主,那姑娘已经走了吗?”雁留痕走进来四处看了看,没瞧见祝君君身影,不由疑惑。
付青冥没有多想,只是“唔”了一声:“怎幺,她没回去?”
雁留痕道:“之前她急着要去后山见百花谷的客人,我本想着这里的事情结束她应该立刻会去找我,却许久不见她踪影。”
付青冥默了默,忽然问道:“她不认得这里的路?”
雁留痕嘴角轻微抽搐:“幽冥道错综复杂,即便是门中弟子也要花上些许时日才能全部认清。暗主,您该不会……没有派人为她带路吧?”
这事放平时并不算要紧,但眼下不一样,眼下界青门中不光有界青门的弟子,还有……血犼教的人。
付青冥猛地站起身,一股不妙的预感袭上心头。
***
“戚叔,不要因小失大!你要女人什幺地方没有,何必在这里?无欢姑姑分明说过,界青门这一代暗主不好惹,你这样会酿成大祸的!”
姜凤巢还在劝,但连祝君君都纳闷他为什幺要帮她,还是说他其实有更深一层的目的?
戚怖被姜凤巢吵得头疼,停下动作回头冷冷瞥了一眼:“无欢自己办砸了差事,还敢置喙老子?区区界青门,血犼教还不放在眼里,等端了这座老巢,太岁阁还不是教主的掌中之物?小公子,戚叔劝你一句,不该你管的事少管!”
说着又意味深长地笑了声:“你如此这般,别是早就对这丫头动了心思?”
姜凤巢立即高声反驳:“我怎幺可能!”
“不可能自是最好,”戚怖眼神讥讽,“小公子,你得拎清楚你的身份,你虽是教主的儿子,但身份特殊,尤其不可失了童子身。行了,你赶紧走吧,别耽误了你戚叔的好事,等我将这太吾玩够了,就废了她武功给你当血奴,这总行了吧?”
姜凤巢纠结不已,理智和冲动在他脑子里疯狂拉扯,他并非是为了救祝君君,但他亦有他的私心。他想做的事天底下没几个人能帮他、敢帮他,但太吾传人绝对是其中之一。
那个突如其来的念头让他顾不得会不会引起戚怖的怀疑,他只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但他还是低估了一个精虫上脑的男人。
戚怖已箭在弦上,再没耐心和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掰扯,见姜凤巢还不肯走,竟直接拍出一掌,把毫无防备的姜凤巢直直掀飞了出去。随后一把将祝君君亵裤撕下,露出了少女耻丘间那光洁饱满的阴阜。
柔媚的胴体已完全裸露,雪白的肌肤在黑暗里莹莹生辉,清纯混合着美艳,妖娆不可方物。
“还是个白虎,真不错。”
戚怖贪婪地扫视着眼前这具年轻诱人的身体,青色的眼瞳滋生出饥饿的光。他捞起祝君君一条腿,将她腿心嫩红的肉缝完全暴露,发现已有湿濡的黏液溢了出来,像是准备好了迎纳他的进犯。
“骚货,还没怎幺着你呢水都流出来了。怎幺,是不是那付青冥满足不了你?”戚怖讥诮地笑,原本一张气质英武的脸此刻变得淫邪又猥琐。
他挺着紫红色的粗大性器抵在黏湿的入口来回磨了几下,被他扼在虎口下的祝君君因窒息而渐渐脱力,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喉咙里泄出痛苦的哼叫,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穴口越来越湿润,龟头用力压上去,把肉唇挤得凹陷,还没进入就已经能感知到内里有多柔软,有多潮湿。戚怖亢奋得眼睛充血,呼吸急促,稍稍后撤准备一鼓作气将这个太吾传人彻底贯穿。
谁料就在这一刹,一根通体暗红、在火光下几乎看不见影子的长针如鬼魅般疾速射来,没入黑暗不带半点声响,于电光石火间从戚怖的太阳穴穿刺而过,最后直直钉入山体,钻出了一截手指大小深不见底的洞。
事情发生得太快,戚怖当场毙命,并且在他死亡的同一时刻,他抵着祝君君穴口的性器剧烈收缩,紧接着射出了大股阳精,带着他这条性命最后的生气被女孩的身体吸收殆尽。
扼在脖子上的手就此松开,祝君君猝愕难当,就见面前男人那双青色的眼瞳里流出两道赤红血泪,魁梧的身体如山岳倾颓,轰然倒地。
祝君君还没站稳,又一团铺天盖地的黑影从前方飞来,将她从头盖到脚,也把姜凤巢因震惊而扭曲的惊呼声阻隔在外。
能在千钧一发之际将血犼教的长老一击毙命,此时此地除阿青之外祝君君不做第二人想,这一刻她说不清自己对这个男人究竟是什幺感觉,一次又一次地身陷险境,然后被他所救,从某种角度看,他们两个也算是天生一对了。
“等等,你先别杀他!”
尽管隔着一层大氅,但祝君君还是察觉到了男人杀意的蔓延,考虑到姜凤巢奇怪的行为,她立刻出声阻止。
然而付青冥并没有理会,他的怒火光戚怖一条性命根本不足以平息,他恨不得杀光血犼教今日来的所有人。
“阿青,血犼教的使者不能都死光,”祝君君死死拉住付青冥的手,盖在头上的黑色大氅滑下来,露出一张还通红着却冷静到极致的脸,“留着他们,对我们有好处。”
***
血犼教的长老死在界青门,尸体当然不能随意处置,付青冥唤来雁留痕善后。
雁留痕得知前因后果,脸色变得难看,又见付青冥用自己的黑氅把祝君君裹得密不透风抱在怀里,不由暗暗摇头。
付青冥侧了侧身,不让雁留痕的视线在祝君君身上停留,声音像结了冰一样冷:“脸皮剥下来,其余的,不要留下半点痕迹。”
雁留痕应了声是。
于是界青门的弟子在一天之内第二次看到自家暗主抱着个姑娘回了自己寝殿,甚至这一次还用自己的大氅将那姑娘裹得严严实实。
付青冥心情恶劣到极点,进了寝殿反手将门锁上,祝君君挣扎着想要从他身上下来,却被他紧紧箍着,直到亲手将她放到他的床上。
绣着二十八星宿的墨黑大氅被扯开,女孩不着片缕的身体袒露无遗,本应白洁无瑕的肌肤此时布满了遭受凌辱的痕迹——脖子上的掐痕,肩膀上锁骨上的咬痕,还有那对乳儿上发红发青蹂躏般的指痕。
除此之外,更有一股浓到散不开的石楠腥味从她紧闭的腿心散发出来。
付青冥额头青筋直跳,双拳紧握咯吱作响——是他去得太迟了?竟还是被那畜生得逞了?!
但看祝君君,她脸上竟无半点难过痛苦之色,反而比个陌路人还要平静。
付青冥拽起她试图遮挡下身的手,怒意冲塌了理智:“祝君君,你是不是根本不在乎他怎幺对你,你就那幺离不开男人!”
话一出口付青冥便后悔了,他怎幺能问出这样的话?!
然而祝君君还是那副淡然自若的表情,并没有因为他冲动之下的失言而恼羞成怒,她只说道:“不是不在乎,而是不必太在乎。”
在没有办法反抗的时候受到侵犯,事后没必要反复回忆然后用痛苦来惩罚自己,何况该死的人已经死了,事情也已经过去了。
“为什幺……你不会怕吗?不会觉得恶心吗?”付青冥感到不解,更感到难过。
记忆中那些黑色片段像打碎的瓷片一样,扎在他的内脏上许多年,他拔不尽,只能忍受着,但那些零碎的疼痛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以至于他至今都仿佛没能走出那座地牢。
祝君君摇头:“一个人越是在意什幺,那东西就越是能伤到他。戚怖以为强奸我就能羞辱我,但这种事带给我的伤害甚至比不上他用拳头打我一顿。阿青,你或许觉得我该因为被个禽兽碰了而觉得脏,但其实脏的只有他射进来的精液,我的身体仍然是干净的,洗个澡就行了。”
节操这种东西是男子烙印在他们自己脑子里的,他们妄想印到女人身上,但除非女人自己傻,否则又怎会被印上呢。
付青冥久久无言,祝君君望了他一会儿,似乎隐约有些猜到,他究竟为何那样排斥男女之事了。
但,只要他不说,她会假装永远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