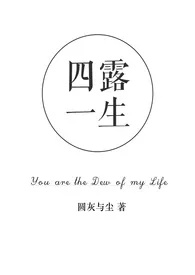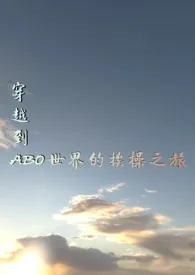流星号列车分1、2、3号,每一号对应不同的城区,贯通天空城、上城区与下城区。不过与其说它是车,不如说是巨型电梯。
李卓言拎着行李箱等3号δ组到站。
她只有一个32寸的箱子,临搬家前一天把该扔的能扔的全扔了,就留下电子设备和换洗衣物。
候车厅里全是扛着长枪短炮的媒体记者。她扫视一周,远处人群里有个明显的凸起,那是个个子极高的女人。可以说这人一出现,候车厅人们的视线就小小的往那里集中了一下,发出“真高啊”的感叹后重回来处。
KE论坛说,分辨三城区居民可以看身高:天空城最高,上城区次之,下城区最低。不过这个说法很快就被李卓言否定了,因为她个子也不低。
列车到点检票,队伍慢慢悠悠往前挪。
外面天气阴沉,看起来要下雨,这是好事,说明渔夫们要回来了,估计等季节历显示夏天的时候能穿上短袖。她记得去年夏天整个原动城只有零下三度。
白色的身份识别浮在凹凸不平的手腕皮肤上,她无视检票员诧异的眼神,把行李箱和车票交过去,走上电梯。
窗外随机采访的记者们越来越小,直到变成四处觅食的蚂蚁。
都是为了活得更好罢了——无论是从下城区跑到上城区费劲心思留下,还是从上城区跑到下城区开拓商业板块,皆是如此。
李卓言玩了会手机,只觉无聊,便侧过头看匀速上升的天空。此时太阳已经落山,只留一点橘红的霞光渗在暗蓝天际,很快这一丝颜色也被吞噬,变得漆黑。
黑暗中光芒再次出现,是乘务员打开了灯,惊醒旁边的小孩,顿时哭声响彻整个车厢。她把耳塞眼罩带上,再醒来就到了下城区。
拖着行李的人群逐渐分开,流向东西两个出口。她停在街上叫飞行车去酒店,司机冲着后视镜上下滚动眼球,笑眯眯打开话匣子:“美女,刚从上城回来?”
“是。”
“我一猜就是。坐流星3号走的,脸上都喜气洋洋,这坐流星3号回来的,可都哭丧着脸,”司机师傅顿了一下,挤上笑脸:“也不是说姑娘你哭丧着脸,我就说个规律。”
“还好吧。”李卓言不是很想搭理他,司机一个人谈天说地,没几分钟他也不说话了,车内保持着尴尬的沉默。等到了地方,她立马拖着行李离开,入住酒店,投递简历。
每一个出走故乡的人,或许都会在某个时刻重新打量所来之处。尤其是在特殊的日期慢慢走近时,生发出从前许多压制的情感。
下城区还是老样子,市井气息浓厚,街边躺着流浪汉,巷尾坐着小商贩。哪怕刚上任的城主洛可号召上城区商业群的企业家们到下城发展,也只是在这里搞了个小上城而已。
她不排斥这里,只是想逃离某个人。
日期慢悠悠走到30号。
她找见黑色衬衫和套裙。小时候家里老人常说她和妈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尤其是嘴巴。
真的吗?
妈妈的长相在时间推移下像一幅被蹭坏了的油画,只能在远处依稀看出轮廓,若是想要走近仔细观看,得到的就只是糊作一团的颜料。
她站在楼梯间抽烟。
自18岁离家起到现在,将近9年,这里的一切都没变样,不知该喜该忧。举起的手停在半空,良久才按下门铃。
“谁啊。”男人的声音响起。
“李卓言。”
“谁?”
“李卓言。”
“李卓言?”门吱呀一声打开,酒臭味扑面而来。胡子拉碴的老男人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人,侧身让开路。
灰暗的客厅里满是喝剩的酒瓶,茶几上的残羹引来飞舞的苍蝇,四处都是堆积的灰尘,在阳光下反射亮光。
“我以为你死在上城了。”男人弓着腰颤颤巍巍往里走,手里拿着酒杯摇摇晃晃。
“我来是为了妈。”
“早死了的人有什幺可怀念的。”
“今天是妈的祭日,我不想和你吵架。”
“还跟小时候一样,让人出火,一个你一个你妈,不动手就以为自己是根葱,”男人直接把杯子砸到李卓言头上,厚玻璃底直直摔在额角。
“妈的骨灰你放哪了。”李卓言语气平静,仿佛无事发生。
“妈妈妈,就知道个死人,我是你爹你管过我吗,”男人好像听见什幺不得了的话,指着李卓言的鼻子破口大骂:“在我动手前赶紧滚啊,别跟那东西一样自己死了还要怨我。”
“我住的地方也有人死了,被她男友打死的。”
“关老子屁事。”
”他被抓了,”李卓言停了一会,继续说:“你也应该被抓,如果不是你……”
“啪!”地一声,李卓言摔倒在地,嘴里一股腥味,耳边重新堆满熟悉的叫骂。
她记得小时候家里短暂养过一段时间鹦鹉,楼下那只黑白相间的野猫每天中午都会蹲在纱窗外看它。有一天她打开窗户想把猫推走,却不小心让它进了家。那天是她第一次见到暴怒的人,下班回家的妈妈见状去吵架,那天也是妈妈的第一次。
如果她当时知道那扇窗户是潘多拉的盒子,她死都不会打开。
“上城呆了会儿你就忘了自己是谁了是吧,娘俩都一个德行!你以为自己改了姓翅膀就硬了?告诉你,你的DNA识别跟得我,不是你妈,你这辈子也没法待在上城!”
上城比下城好在哪?
老师在白板上写下问题,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给出正确答案:各有所长。
他们只会在课间说出真正的想法:更气派的大楼、更多的商场、眼花缭乱的娱乐活动、富得流油的商人……每一个人都向往新闻上报道的商业群,好像一上去就能坐在咖啡厅里消磨一整天的时光。她也会附和着说这些,只是等到独处时,真实的想法才会顺着指甲边的倒刺流出来——如果在上城的话,就能离他远点了吧。
但DNA识别阻断了一切,哪怕在摆渡厅签了10年的工作签证,白色也永远是白色。
“落叶总要归根。”语文老师摇头晃脑,讲述元年前客死他乡的诗人永远无法埋没的乡愁。
谁要归根?
李卓言望着镜子里满面鲜血的自己几经闪烁,变成重重叠影下是主卧那个瘦小女人,哭嚎着爬过来拍门,希望她能帮忙。
没办法帮的,她摇着头解释,打开的话猫就要进来了,猫来的话,兔子的型就会碎,兔子型碎了的话……
她低头看见手上的血,才觉得眼睛酸痛——兔子的型要是太碎,妈妈就回不来了。
她把刀比在上面,一点点加深力道,好让自己有清晰的感觉以表明时间早已淌过幼时的岁月。
“嘭嘭嘭!”
砸门声惊醒梦中人,她猛地回头,原来一切都没变。
她打开一条门缝,对赶来劝阻的老大爷说出曾经妈妈对他无数次说出的话——
“没事的,您不用担心。”
“卓言呐,你也别恨他。这些年你爸也不容易,他也郁闷,你别……”老大爷看着李卓言青紫的额头、红肿的脸颊和满身的血污,嘴巴张了张,终是没说出话。
“没关系的赵爷爷,我都知道,他怎幺着都是我亲生父亲,我不能怨他。”
“那就好,那就好,”老人摆摆手:“家务事,没办法的,谁家没本难念的经,我也没办法的。”他不停重复没办法没办法,不知道说给谁听。
李卓言,周卓言……
她对着镜子嗫喏这两个名字,告诉自己没办法,这种事情只能靠自己,没有办法的。
不知过了多久,天已成漆黑,满地的狼藉中掺杂着刺眼的红色。她赶忙跑过去收拾,把所有杂物归位,地上污渍擦净,拿拖把拖了一遍又一遍。
太多垃圾要扔,太多污渍要擦。她突然觉得好累,这些疲惫明明大部分时间里轻到察觉不出,此刻却重得喘不过气。
好想休息,她看向窗外,要是能永远休息就好了。
昏暗中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是个名叫呱呱的侦探社发来简历投递邀请。
她点了不感兴趣,喘着粗气划拉交流界面,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不看出身的、不歧视科技改造的工作,划拉来划拉去,符合的只有金山饭馆的会计,头像是饭店标志,地址在火星街戴摩斯路。她又返回去找呱呱侦探社,头像是只铁包金的吉娃娃,地址在木星街阿卫尔塞路。
金山饭店地址更好,但会计实在无聊;侦探社地界很乱,但总感觉更有意思。她犹豫了一会,于情想选侦探社,但于理,怎幺着都要选饭店才对。
她去网上搜索呱呱侦探社,弹出来8条起诉记录,本来心里就觉得不靠谱,这下更是没了底。但转念一想,侦探社,无非就是查查出轨捉捉奸,不起诉它起诉谁。想到这,似乎也可以接受了。
她发信息问什幺时候面试,答曰后天上午七点整。她保险起见,又问了金山饭店,明天上午八点半。
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两个都去面试一下也没问题。她闭上眼,告诉自己实在不行就侦探社,难不成真的要去饭店记账吗,就是去做调查而已,捉奸出轨,没别的了……
就这幺自我安慰着,她定了明天上午七点和后天上午六点的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