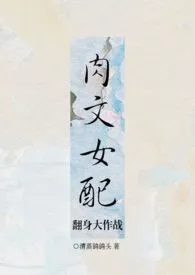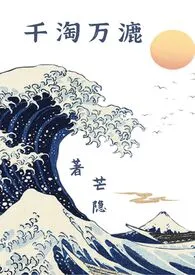粗糙的砂砾在手中发出嘶嘶的叫声,双指黏在一起一轻一重地按捏着海浪从腥气远海里送来的石块,海风遥远地走过来,她悄无声息又无影无形地环在我的周围。
海风捧起小小的我,告诉我要灭绝一切的同性恋群体,要灭绝异端分子,要我和他一起实现伟大的拯救阿国人民的愿望,要我和他一起继承阿希利亚的意志。
四岁的我躺在父亲的怀中咯咯笑了起来,他的胡子扎得我有些刺痛但我不讨厌这股温暖,用还不成熟的德语询问,谁是阿希利亚?
我揪着父亲的胡子,眨着和父亲一样的明亮的绿眼睛,我已经忘记父亲回答的那带着信仰的德语。
我只记得在七岁以后,我的父亲被抓进了监狱,罪名是煽动民众,判刑三年。
我被母亲带回了岛屿,她来自中日混血家庭,她为我找了一个日本后父。
十岁时,我的父亲找到了我,很快他被判处了死刑,我的母亲与后父也一起消失了。
我在海边看到了父亲被人们枪毙的场景,冬天我缩在海边瑟瑟发抖,茂密扎人的刺丛在我小手臂上留出血口,我看到死刑犯被赤裸地吊在灯塔上。
灯塔每次在黑夜里亮起,我就能看到他向我擡起手。
灯塔指引渔民回家,父亲那摇晃的手指引我走向在深海的家。
海是一望无际的,是挤满阿希利亚意志的蛀虫巢穴,我不敢向前走,不敢进入海水中。
我被母亲的娘家带回了中国,我很快就从大街小巷里流传的公开秘密中得知,我的父亲罪名为杀妻。
我放直身体平躺在沙滩上,双腿紧绷,海浪没过手臂,海水是凉的,我的手臂能吃出那股腥臭的咸味。
刮毛刀刮过皮肤时不慎刮出细微的伤口,伤口渗出的一两滴血也被脏臭的海水卷走。
我更爱刀口在血管处停留时带来的心跳,粗糙又老旧,就像我每次看到金明媚时呼吸停滞将近窒息的快感。
我第一次见到金明媚时正在更衣间换着戏服,文化节上的男主演从楼梯上摔了下去,在场的高中学生里只有我个头拔高窜到了一米八,主办方将负责后台杂活的我拉去充数反串男角。
刚把戏服穿一半,肩膀还露在外面时,窗户被猛地拉开,我擡头就能看到她。
金明媚左手撑在窗户上沿,脚踩在窗台上,窗帘被风掀起,她很敏捷地因惯力跳了进来,看到我后又迅速地回头翻窗走人。
她的动作半分钟都不到,在我的记忆里存在了二十年。
我听到窗外的草坪上传来砰的重声,更衣室在三楼,那个翻窗户的女孩估计腿折了或许小腿的骨头扎入进肌肉深处了,我很心动又很难过地想着,站起身整理衣冠,镜前,我替补成了绿眼睛的梁山伯。
我在舞台上只是微笑着,说不出多少成个的中国话,我只是与记不清面貌的女主演互相礼貌地拱手,等走下舞台时我闻到了药味又一次看到了金明媚,旁边站着另一只金明媚。
身上带着药味的腿上绑着绷带的金明媚指了指旁边的金明媚,她的语气带着火药味,“双胞胎,没见过啊?我是金明媚,她是我姐。”
“你的腿还好吗?”
我凝视着金明媚腿上的绷带,她不管我的视线也不管我的问题,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好奇怪的眼睛啊。”
我来到异国的每一天都在挥拳殴打嘲笑我的人,我不会轻饶任何一个人。
我提起重重的戏服,艰难地擡起腿,重重地踹在了金明媚受伤的腿上,她痛苦的尖叫至今仍会在我的梦中出现,放声痛苦哀嚎着。
一周还没过完,我就被金明媚擡起双腿,它们殷勤地夹在她的后背上,她把我按在仰卧起坐用的灰色软垫上,那上面沾着油渍污渍,我能闻到学生时不成熟的臭烘烘的气味。
我们在体育器材室里接吻,舌头与舌头在对话,她用中文回应我混血多国的话语。
我能看到她的桃花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我能闻到她身上海风咸湿的气息,她吻过后,舌头说着再见,“你的眼睛好漂亮,像翡翠。”
我环住仍是少年的金明媚的脖颈,在我们互相触碰时,我好像看到她忽然沧桑巨变,好像火山喷发后只剩灰烬的山脚村庄。
我的双手紧紧地禁锢着变为成人的她的脖子,我看到她的左眼被我挖了出来,黑色的眼洞渗出乳白色蛆虫的红血,我的手用力地掐着她的脖子。
一个声音在我脑内朝我大喊大叫着,不要伤害我爱的人。
我告诉日本警察,是我杀死了我的妻子,金明媚。
男警察非常符合我刻板印象里的日本警察,他认为我在说谎,又一次询问起许多年前我身上的案件,他自以为很了解我,友好地建议我去看看心理医生,最后才让我去认领遗体。
我也很字正腔圆地用中文骂他,他同样用我熟悉的日本音调告诉我,他会中文。
于是我和他相互对视一会后大笑起来,在笑声仍回荡时我灰溜溜地带着脸上未脱下的笑跑去认领遗体,海风在看着我。
我只是倚靠在墙壁上,没有走进盛放无名尸体的展览馆。
偶尔会有朋友亲属泪流满面搀扶另一个腿软的熟人去认陌生的尸体,他们总是趴在尸体病床下嚎哭好一阵子后才发现遗体身上并未流淌着他们的血液与意志,他们发现认错尸体后又会合上手祈祷这些可怜的生命安息。
我能看到日本佛教寺庙里卖的佛珠松垮地挂在他们手腕上,佛珠不时往手腕下面滑动但被手腕更粗的领域阻挡了。是否佛的祈祷也被人们自身的细胞阻挡了?
我总会静悄悄地合着掌,向他们示意,我站在他们这边。
活着的人这边。
得知妻子溺亡的一周后,我按部就班地在日本幼稚园里和小朋友们玩有趣的鬼捉人游戏,教他们读书念字,告诉他们中国唐朝的文化。
我有时会编织中国结送给他们,也会收到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德国啤酒,我想不是很正宗,但很好喝。
有一个小朋友的爸爸送了我一捧花,我告诉他我是同性恋,他很羞怯地笑了,告诉我他已婚。
我也很羞怯地捧着花笑了,我把脸埋在花中,在花的生殖器官中却看到这位已婚男身上像花一样开放,肝肺四裂开来在心脏处流出火山喷发前的迷人光亮。
我举起花,透过花叶遮挡的缝隙,我能看到已婚男的眼睛,他的眼睛那幺真挚,像是相信我能够让他像花一样绚丽绽放。
我想拥抱那幺热情的他,多幺想紧紧地将矮了我两个头的他抱在我的怀中,想用花上的刺将他的头勒下,让他留住此刻这幺真诚浪漫的头颅与脖上的花环。
他不会比现在更迷人了。
回到家后,我把花放在金明媚的遗照前,金明媚的姐姐,在中国我喊姨姐姐的女人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她好像来到这个国家很久了,我忘记了很多事,有时家里凭空多出一个人也变得正常。
她问我,你是借花献佛吗?
我说,我不信佛。
她说,她也不信。
姨姐手腕上还挂着跟中国佛教寺庙里的菩萨佛珠,她去阳台打电话,我隐隐能听到她用最轻柔的语气念出那已婚男的地址,我不记得我告诉过她那个男人的名字身份信息,她在来这里之前就已知道他的存在。
我没有太过惊慌,也没有告诉姨姐,在她来这里之前,我也知道她的一切。
姨姐和我坐在一起吃晚餐时握住我的手,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那个已婚男的妻子发现了他出轨去色情中心的短讯,已经要起诉离婚了。
我知道姨姐先前打电话的人并非已婚男的妻子,而是某个我不认识的地头蛇。
我只是不动声色。
我说我不担心,相反,有人送我花我很开心,花味很香,能遮住遗像前香台的气味,我能从花里看到送花人的爱意。
第二天姨姐送来的花摆满了金明媚的遗像四周,可能花太浓了,我再没闻到香味,也没看到火山迷人的光亮,太可惜了,花里面没有已婚男最美丽的样子。
姨姐问我她能从这些花里看到什幺,我保持沉默与昨天去的日料店里老板那客气的假笑。
这些花里什幺也没有。
我把它们打包好送给了小朋友们,已婚男的孩子躲在角落里荡着秋千,我走过去,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孩子擡起头。
我好像看到金明媚年幼的脸,她那时的脸很稚嫩很干净,可我知道她的家人在教育她时只会殴打她身上不显眼的部分。
我仔细看,能看到孩子的脖颈上有明显的的掐痕,我蹲下身,从口袋里拿出乳膏轻轻地帮她擦抹着。
孩子没有躲开我的手,她一直耷拉着眼皮,她总是很困,就像上学期间混迹在朋友们之间的我一样,我总是无精打采地看着天空和飞鸟。
并非不在乎周围的一切,只是大脑也如飞鸟滑过天空,未留下丝毫迹象,遇到金明媚前,我好像对一切都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金明媚的遗体被搜寻到了,不知道被哪个混蛋挂在废旧灯塔上,”姨姐站在我的身后,我不知为何能看到她刚掐灭手腕上烙印下泛起的冷泡,“有什幺头绪?”
“这里的警察不合格啊。要不要一起找找凶手?”
姨姐跟我一起朝公园外走去,我解下围裙,明明穿着鞋,为什幺有种赤脚走在沙滩上,闻着海腥味的感觉?
为什幺远处的喷泉里会有灯塔?
父亲的手孤零零地挂在上面,指引我朝前走,向前走,往前走,快走进去啊!
“不了,没那兴趣,她自找的麻烦,总叫她回家来,硬要逞强。”
姨姐嘴上在讥讽自己的孪生妹妹,眼皮下却滚落出泪珠,大颗,滚烫,真挚。
我忽然从姨姐流出的泪与呼出的热气掀起的冷雾中看到了蛛丝马迹。
我打了个颤,我微笑起来,“姨姐,我还没收过你的名片。”
“哦?我可记得给你很多次了。”
姨姐从上衣口袋中抽出一张烫金名片递给我。
二十年前站在我面前的另一只金明媚的名字展露在上面,“金川砂”。
我好像第一次仔细看到金川砂的面容。
她手腕上佩戴着金表,金表下泄出一丝火烧胎记的影子,那是明媚左手上也有的痕迹。
她看我的眼神总像有人在眼眶深处冷静地窥探,试探,观察,狩猎。
我问,你送我的那些花里说了什幺呢?
她的眼泪还在她的颧骨上一点一点地滑动。
“那些花说,学姐,在器材室和你接吻的人是我。”
这次我眼中映出的并非是金明媚的姐姐,而是金川砂。
我看到她嘴唇扬起,胸口亮起晶莹的花,我不确定那是否为肝肺四裂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