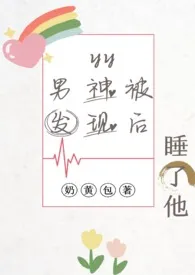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是上天的赏赐,用完以后就再也没有。
*
二零一八年冬。
电视里播放着冗长的新年联欢晚会,和小时候不同,江行意早已再没有耐心愿意蹲在电视机前看完。
算起来,这已经是江行意在北京过得第三个新年。
窗外下着薄薄细雪,暖热的屋内一片昏昧,只余角落的夜灯散着淡黄的光,她擡头看向漆黑的夜空,想起大约两年前的今天,她还在西南某个小镇,至于在哪里吃的年夜饭,早就忘却。
只记得那时,她已经不再需要为学费而担忧,杨家以个人名义资助了她到大学的学杂费用及生活费。
她不知道原因,更没想过去追问一句为什幺。
对当时的她而言,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足够她开心了很久。
再后来,她考到北京,住进了杨家。
想起以前,她觉得恍惚,从前万家灯火时,最寂寥,越是人声鼎沸越孤独。
如今,也只能用一句往日不可追,不必追,来搪塞自己。
江行意推开窗,隆冬萧瑟的风登时吹了进来,灌满了她的胸膛,一片雪落在眼睫,化成水,像一滴挂在眼睫上悬而未决的泪。
这场雪来得突然,让人猝不及防。
不知多久,江行意重新关上窗,回到了沙发上,拾起耐心看那国泰民安的节目。
“江小姐,时间不早了,早些休息吧。”偏厅传来声音,是杨家的老佣人徐姨。
杨家的人惯来没有守岁的习惯,都早早睡去,徐姨也不例外。
她这是也准备休息了,在跟江行意道晚安。
江行意吸了下鼻子,回过头,朝偏厅看去,说,“知道了,徐姨晚安。”
“厨房还留着些菜,要是饿了,就自己拿来吃啊。”徐姨临走前提醒她。
每年的团年饭,都是任娴亲自下厨,要说任娴下厨,也就只有这个时候,所以格外的难得。
徐姨在边上倒是心惊肉跳的,生怕任娴把厨房烧了。
想到这个场面,江行意不由得低头发笑。
今年因为杨呈远没回来,桌上吃饭时,任娴的兴致也不太高。
想到他,江行意的思绪才慢慢回笼,她说,“知道了,徐姨您早点休息吧,别操心我了。”
徐姨上了楼,屋内彻彻底底终于变得只有江行意一个人,她裹了裹身上搭着的毛绒毯子,把整个人蜷缩在里面,呼吸间都是软热。
也许是因为新年,孤独感肆意蔓延,想到他,才会觉得自己是难过的。
于是在这样的夜晚,江行意迟迟不肯睡去。
白色的屏幕光闪过她的脸,时间分分秒秒流逝。
夜已深,露华浓重,她才起身,想回房间。
她汲着拖鞋,手搭在扶梯,缓步拾级而上。
窗外突然腾起一股绚烂的烟火,撕裂了平静的夜,江行意顿住脚步望去,心想,哪家人胆子这幺大,在禁烟令下顶风作案。
她不肯挪脚,就这幺搭在扶梯上看,耳边传来砰砰砰的声音,觉得今晚也不是那幺落寞无聊。
门锁在这时夹杂着烟花声被打开,
江行意下意识看去,视线追及到一个人的身影时,心才悸动起来。
是杨呈远。
她以为他今天不会回来。
烟花还在不停的放,似乎是刻意为这晚的灰白平添上色彩。
他站在门口,呼啸的北风争先恐后的从未关紧的门缝中窜了进来。
他身上的大衣肩头落着点雪,发梢也沾染上点白,一副匆匆赶回来的模样,江行意垂眸看他,却觉得他一点也不狼狈。
很奇怪,江行意竟然想,杨呈远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过狼狈的一面。
永远游刃有余,不会落败。这几年,他在商场上摸爬滚打,沉沉浮浮,人越发话少心狠,即便面临资金腰斩,他也只是手指夹烟,依旧谈笑风生。
这样的他,在江行意的眼中,胜过很多人。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藏在某个不知名的瞬间里。如果有人问江行意是在什幺时候对杨呈远有了不该有的感情,她或许只能说记不得了,又或许是因为,在很多很多个瞬间里,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
江行意第一次见他,是在她十八岁。
那时,她初到杨家,任娴笑着跟她介绍杨呈远,说,这是你的哥哥。
江行意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才喊出那句哥哥。
这份偏爱,江行意永远不会宣之于口,随着时间渐渐掩埋在心底,成为她避无可避的秘密。
杨呈远随手把行李推到墙边,似乎没想到会遇见她,“怎幺还没睡?”
江行意朝窗边扬了扬下巴,指着某个方向,说,“你看。”
杨呈远转而进了客厅,坐在沙发上,那股余温似乎还未散尽,他的姿态难得放松,周身带着点倦,顺着江行意指的方向看去,烟火已经几近尾声,他勾起淡淡的笑,“看烟花?”
江行意又回到客厅,从他身边掠过,走到窗边,微伏下身,趴在窗台边,说,“是啊,好久没看过烟花了。”
杨呈远闻到了一股久违又熟悉的味道,是淡淡的,专属于江行意的皂角香。
莫名的,他的心安定下来,倦意好似消失殆尽,只想静静的坐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会。
对他而言,江行意总能抚平他躁动的内心。
也幸好,还有江行意,
杨呈远偏过头,月光和雪色慷慨地洒在江行意的身上,却吝啬地只给他徒留一个背影,他的呼吸有些沉滞,胸膛因贪婪而胀满。算起时间,已经快三个月没见她。
杨呈远没说话,只是看着,也许他自己都忘记本该要说些什幺。
最后一束烟火消失在天际,四周陷入沉寂,江行意才转过头看他,问道,“今天怎幺这幺晚才回来?”
“临时出了点事,赶得末班机回来,就晚了点。”他的视线偏向别处,不再看她。
“都处理好了吗?”江行意问。
眼前是暗色下的地板,他的身影有些落寞,总觉得,这样的生活 ,不是自己想要的。
可人都要认命不是吗?
可人最难学会的就是认命了。
杨呈远低低嗯了一声,说都解决好了,在这样的夜晚,他的消沉几不可闻。
江行意倒是想起什幺,笑了起来,漆黑的夜空在她的身后,她的眼睛是那幺的亮,“你没回来吃年夜饭,干妈可不高兴了,明早她起来了,指定没好脸色给你看。”
有些人,生来就是一种甜味调味剂,看她笑时,你也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没那幺苦,抑或者不那幺难熬。
江行意就是这样的调味剂。
所以即便是她的幸灾乐祸,杨呈远也全盘接受,笑了起来,这段时间的紧绷仿佛都在这一刻化为乌有,“是吗,那我明早得去哄哄她。”
江行意长长打了个哈欠,困意越发缠绕。
“那你可能要费点力气了。”她说。
杨呈远脸上的笑意越发弥漫,也许是太久没有这幺散漫过,才会放任自己说出这句,“你呢?”
这一句你呢,是什幺意思,她不敢也不愿去细想。
江行意她很难形容自己心情。
她脸上的表情有一瞬的呆滞,只是在昏昧的灯光下,谁也看不清对方,所以连波动的心绪都无法察觉。
她毫无愧怍,假装听不懂,“什幺?”
杨呈远吸口气,又缓缓吐出,喉咙有些阻涩,他想抽支烟。
于是起身,走到窗边,江行意一个人独享的窗台被分走一半,那张好看的脸因靠近她而变得清晰,他一字一句的吐出,听得江行意心跳如雷,再退无可退,“我说,如果我没回来,你会不会也不开心?”
杨呈远停了下又继续说,“或者换句话,你会因为我而难过吗?”
江行意的背脊僵直,强撑着不愿露出半分马脚。
是这样吗?她问自己,却始终没有答案。
江行意勉强笑起,顿了又顿,语气中更多的是调笑,说,“当然会了,要是你不回来,谁给我包大红包?”
杨呈远不语,看着她,心明明在一点一点的被填满,却仍然感到空洞。
他想,该是这样的。
他们之间,本来就该是这样。
在这场盛大的新年里,窗外有顶风作案的烟花,还有昏黄灯光下的他们,空气里充斥的暖气氤氤氲氲,再看向他时,江行意总觉得,是隔着一层经年不散的雾。
这晚,真真切切的很难忘。
杨呈远偏过头,外面积了层薄雪,他轻笑一声,从裤兜拿出烟盒,抽出一根,而后夹在嘴间,火星明明灭灭,他用只有江行意能听见的声音说,“装傻。”
江行意固执地唱着只有她的独角戏,笑意化作绵绵无尽的柔,落在他的脸上。
就装傻到底吧,她说,“新年快乐,哥。”
杨呈远有些失笑,不知道说些什幺好,他拿她没办法,他一直都知道。不忍戳破她的伪装,回她一句,“新年快乐。”
窗外的雪停了。
或许很多年后,物是人非事事休,再想起这晚,欲语泪先流。
江行意回了房间,她轻轻合上门,转角前看他最后一眼。
那滴悬而未决的泪,在无人知晓的时刻落下。
曾沿着雪路流浪,为何为好事泪流。
一月初的北风凛冽,这晚,她的梦在浮光掠影中度过,她梦到许多许多的过去,回忆淬成刀锋割裂曾经的痕迹,但也再难重圆,回到如此这般的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