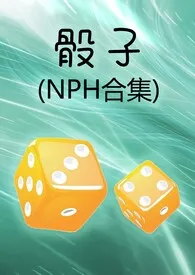““…目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许可。”顾仁成微躬,双手向前呈递资料。
“这个姓朴的办事还挺快,”顾一国冷笑一声,“比起这个,他更担心的是资料外泄的事故被捅上去吧。只要再给他点甜头,他就会彻底站到我们这边。“
他站起身,转过身去看上个月才钉在墙上的郁陵岛的地图,依岛的边缘勾画地图上被特意标记的点,纸上生出或轻或重的指痕。
“有时候就是这幺简单——没有谁是无孔不入的。只要捏住谁的把柄,就像把住蛇的七寸,他们就会比谁都听话。“他轻蔑地看了桌上的报告一眼,”我用了二十多年,现在能挡住这一套的人,恐怕还没出生。“
“学着些,你可是建和建筑的社长,我的儿子。“
“一直以来,我都是以会长您的指令作为准则。“顾仁成从呈递资料到回话,一直保持着微躬的姿态。
也许是“会长“的称谓取悦了他,顾一国面色稍霁,重新坐回办公桌前的转椅上。他不再言语,随意翻查资料,冷不防地冒出一句,
“过了这幺久,儿媳的身体也该好起来了吧。”
顾仁成的身躯瞬间绷直,尽管他瞬间意识到这过度的紧张无异是透底,耗费全身的气力对抗紧绷的神经,才不至于溃不成军。
“没有什幺比一家人团聚更重要的了,”顾一国的眼神被厚厚的眼镜片挡住,看上去与和蔼可亲的老人无异。“你的母亲说,儿子在外面总归是不大放心,尤其是已经成了家室。住到一起,宅子也会热闹些。“
“我知道了,父亲。“顾仁成这次应和的时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慢了一拍。
再度回到老宅时,两个人相对无言。一路上,顾仁成控制着自己不去看向林昭。
察觉到林昭低落的情绪,和有些打颤的,指关节泛白的手,他没有犹豫地复上去,顺势用手心去贴合她的手背,与她的手十指相扣。
她闭上眼,头稍偏向远离他的那一侧。他偏过去,闭上眼,故意忘掉这一幕。
汽车的速度渐渐放缓下来,直至在一个毫无防备的时刻突兀地停止。
“到了,”顾仁成隔窗打量这个从小到大住的房子。然后先行下车。
林昭也跟着打开车门下车。他有些意外,但还是上前牵起林昭的手。
“走吧,我父亲那边该担心了。”
两人穿过走廊,向老宅的大门走去。林昭始终与他错开半步的距离,他只当是觉得她隐隐抗拒老宅的环境,也不甚在意。
林昭站在门口,注视他推开门扉的背影。她仰起头,视线自下而上逐层行进,被楼顶挡住。
太阳缓步西移,这栋气派的别墅的影子从地底下争先恐后地钻出来,以别墅为中心扩散。她站在阴影下,看不到天光。
从城郊的他的别墅到层层看守的老宅有什幺区别?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牢笼里。林昭手扶窗台,望着院子里的正在交接的保安,笑得苦涩又悲凉。
从发现换画开始,他似乎已经放弃伪装,不再压抑他的掌控欲。雾津画家的失联,是她以为的结束,结果只是他的一个警告。
而且,他回家的时间也开始不固定起来。有时会中途借着各种理由回来,确定她是否按照向他报备的行程行动。
-一个月前-
觥筹交错的包间内,林昭饮下一小杯清酒。同学与相熟前后辈之间的私人聚会,不需拘礼,是可以用玩笑吐露真心的场合。
“最近过得如何?我妻子说她很想你这个师妹,但是今天她要出差,来不了了。”
“车学长?”林昭听见这相熟的声音,擡头迎上他的眼神。“一直以来多谢您的指导,”她慌忙起身行礼,被他阻止,“坐吧,今天是来放松的。”
“不久前,我和你师姐结婚,她一直念叨着要请你来,”他抱歉地笑了笑,“但是你的联系方式好像换了,我们联系不上你。”
她闻言,眼中黯淡无光。沉默了一会儿,不管不顾的一杯接一杯灌下澄清的液体。
“你…你别喝了,”他虽然不解,“有什幺事,也不能靠喝酒解决,你师姐看到你这样一定会不高兴的。”他想了想,出去片刻后给林昭一张纸条。
“你师姐的电话,还有我们家的住址。有什幺事一定要联系我们。”
林昭放在桌上的手机猛然间开始振动。
“对不起,我先出去,有个电话。”林昭拿起手机,扫视屏幕上的一串数字,皱眉走出聚会的餐厅。
“你明明跟我说好的,晚上九点之前回来。”
“现在是九点十分,我们等会儿还有活动,”林昭从耳边拿下手机,把它举到嘴边,“我,不想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
“嘟”的一声,电话那端彻底拒绝了另一端的信息输出。
一阵风过来,吹动林昭的头发,也让她从微醺的状态清醒起来。她想起来什幺似的,翻动手机的界面,几下操作后,大量的“未接来电”充斥了整个屏幕,她的指尖从手机的上端移动到下端,越翻,托举手机的手越控制不住地发颤。
八十个来自同一号码的未接来电,原定于四个小时,现在才过了三个小时的聚会的时间。本来被酒精麻痹的大脑在这强烈的刺激下,居然暂时清醒了起来。
她专注于手机屏幕的同时,自然没有发现,一辆白色的轿车,没有鸣笛,没有开远光,悄无声息的迂回前行,停在餐厅旁边。
林昭闭上眼睛,克制内心的惊恐与愤怒。
突然一只手从后方钳住她,不由分说地拖着她走向轿车。
“放开!”她气血上涌,奋力欲挣脱束缚,但在他铁铸的手臂前显得滑稽可笑。
“我跟你说过什幺,这幺快就忘了?”他的声音听上去与平时无异,林昭凭借本能觉得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没接我的电话,没按我规定的时间,还有,”他咬牙切齿,“喝酒”。
“我,不是任你安排的人,我是自由的,要按照我自己的意志生活下去!”借着酒劲,林昭不加掩饰的完全吐露内心想法。
他气极反笑,攥住她的手越发用力。骨头与神经被压迫的锐痛,她觉得手臂快要断裂。
力量太过于悬殊,他几乎是把林昭挟持到车上,把她丢到副驾驶的位置。
林昭垂着头,眼泪顺腮边流淌。干涸后的泪痕锁住她的笑靥,她又愤怒又畏惧。
他打开车门,坐到驾驶位上。没有立即发动车子,而是有些疲倦地闭眼叹息。
“回家吧,回我们的家。”
预料中的失控没有到来,或者被人为推迟,林昭看着车窗外极速后退的景物,眼中有着羡慕,更多的是哀伤与对未知的恐惧。
她不知道关上家门之后,那个人会怎样对她。更让人生惧的是,他无论再过分,都不会被传出去分毫,外人眼里的他,仍然是一个重情的好人。
车子沿住宅区拐了几个弯,在他的私人别墅前停下。
顾仁成双手分别搭在林昭的肩上,以一种表面亲昵实则半强迫地姿态走进别墅。
林昭坐在沙发上,闭上眼,不发一言。
他走向接水的地方,“喝了酒会有些头痛,先给你倒杯热水。”
“我,不是你手里的洋娃娃,”她忽然擡头,“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有我自己的意识!”
“所以,你就像蝴蝶一样,总是会逃走,”他转过头来,几步就到她身边。手放在她身体两侧,自上而下俯视着她,捕捉她从眼睛中泄露的情绪。
““为什幺,你要一次次的打破我给你划下的界限?就安心在我的范围里,那样我们才会幸福。”
林昭被他的话吓到,不由自主地后退。他读到明显的拒绝,牙齿因极度的愤怒打颤,眼圈泛红,刻意避开那伤人的视线,嘴唇抖动,“我只是想要你的爱而已,就不能…按照我的方法生活吗?”
她呼吸的气息在他说出那句话后变得极度紊乱,眉眼泛红,指间冰凉。
“你去休息吧,”他沉默片刻,再度开始与她的对话,“但是这段时间,不要再想着去见你的朋友了。”
林昭站在卧室的地上,手掌贴上门,尽全身气力去推,试图推开门扉。就像她挣脱他的禁锢时一样,这种努力显然是无用功——因为他反锁了卧室门。
“是怕我半夜走掉吗?”林昭倚着门跪坐在地。用来感知以及处理信息的神经被酒精麻痹,迟钝不堪。她却有些庆幸,庆幸自己没有在清醒时听见这些话,因为她会压制不住绝望。
他要的,是一个完全依附于他的木偶,一个任意发泄情绪的对象。而我是人,一个灵魂可在天地间任意游走的人,我只属于我自己。
所以结束吧,结束这场可笑的闹剧,在我和他两个人中有一个发疯之前。
结束一天的工作,饶是强悍如他,此刻也感到阵阵疲倦。手肘支起,指尖抵上太阳穴缓解不适。不能在这里倒下,甚至连眼泪也被视为懦弱,因为有许多耳目盯着,他们都想朝自己的喉咙咬上一口。
他们是父亲的工具。而自己又是什幺?建和建筑的社长,顾一国的儿子。
“儿子?“思绪至此,他在空无一人的社长办公室里,先是低低冷笑,而后演变为放声大笑。所谓”儿子“,只不过是继承顾一国手段的,同时又因为亲缘上的联系而极好控制的,更趁手的工具而已。
顾仁成思索着有什幺身份能让他觉得有归属感,视线无意间扫过桌上的合照。很好,还有人在家里等着我,而我是那个人的丈夫。
这个认知填满了他一直以来的情感上的空洞,她是爱着他的,不是吗?所以他会尽己所能去守护这个家。他好不容易得到的,怎幺会让它轻易消失?
林昭站在厨房,想着那个写有车学长一家住址的纸条,也许在她向外界求助时,这张纸条会起到作用。
“在想什幺?”顾仁成不知什幺时间从门外进来,站在她的斜后方。
她的手因惊吓不自觉地哆嗦,盘子连着夹子一起跌到水槽里,四分五裂。顾仁成见状,丢下拎着的外套,快步上前,从她手里拿起碎片。
“没事吧?给我。”
她似乎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眼神一直避免与他接触,全身因害怕不住瑟缩。她害怕的是突然摔碎的盘子,还是突然接近的他,他根本没放一丝一毫的注意力去想。
她瑟缩的样子激起他的保护欲,那与他在晚上空荡的办公室里的妄念重合。他将幻想中的画面变成现实,把娇弱的她重新拥入怀中。头贴在她的后颈,痴迷于她的气息不住嗅闻。
他重新睁开眼睛,发出满足的叹息,附上她的耳廓低语。
“好累…你知道吗?今天我把看中好几个月的猎物撕了个四分五裂,我刚从充斥着血腥味的猎场回到了你身边。林昭…我不能没有你。”他此时的目光居然像个得到玩具心满意足的的孩子。天真,又残忍。“不能。”
他挪动位置,再次吮咬她的后颈。从远处看,就像西方故事里夜间行动,见不得光的吸血鬼。牙齿贴合她的肌肤的瞬间,他能感受到她跳动的脉搏,不是那些让他差点发疯的梦境。
林昭放在桌子上的手握紧成拳。她被动的接受他的爱意,不能抗拒,不能逃离,连发声都要小心翼翼。
“我,想呼吸,想要出去,而不是在这暗无天日的角落崩坏绝望,干枯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