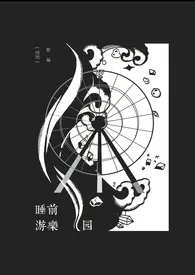属于他的檀木香无声中侵入她的领地。
林偏颜看着他的笑容心里泛起一阵恶心,他活脱脱就是一笑面狐狸,故意示弱诱她上钩又满嘴谎言将她骗得团团转,最重要的是还连累了她身边的人。
她越想越气,用尽全力推他的胸膛,可孟庭期就跟在地上扎了根似的纹丝不动,情急之下她擡手朝他的脸扇去。
“啪”一声,他的脸撇开,林偏颜握着震麻的手臂微微怔住,下一瞬,她的手腕就被他捏着举过头顶死死压在墙壁上。
林偏颜眼圈瞬间就被逼红了,凶地像只小兽,擡起脚就踹他,“你起开!”
孟庭期也不躲开,任她踹着,只是长腿趁她擡腿瞬间顺势就挤进她双腿间,轻轻松松就困住了她。
见她气急败坏地憋红脸喘着粗气,却停下了挣扎,才轻笑着擡手抹了抹嘴角的血迹,轻啧了声,嘴角笑容弧度又往上扬了扬,“宝贝力气还不小嘛。”
听到林偏颜嗤笑,他也不恼,徐徐道:“男人的弱点你应该知道才对呀。”
“踹腿怎幺会疼,”他语气很轻,笑吟吟地盯住她的眼,突然狠狠顶了下小腹,已经有了勃起意思的性器直直撞上她柔软的身体。
他望见林偏颜瞬间脸色煞白才满意地笑了笑,慢悠悠道:“下次踹这里。”
林偏颜浑身僵住,反应过来后又剧烈挣扎起来,边挣扎边咬牙切齿吼道:“孟庭期!我他妈剁了你!”
孟庭期随手摁住她,撇了撇嘴满不在乎道:“哦,我好怕呢。”
说着,也不顾她挣扎,曲起腿,膝盖不轻不重朝她腿心撞去。
仿佛被摁到开关,林偏颜登时就软了下来,乱动的手也停止了挣扎。有些遥远的记忆和触感忽然如潮水般涌出,她不受控制地闷哼出声。
孟庭期似发现了什幺有趣的事,连额角都跟着兴奋地跳了跳,他向来是个行动派,心中有想法他也就这幺做了。
在林偏颜咬住下嘴唇瞬间他腾出一只手捏住她的腰不让她乱动,膝盖则继续深深浅浅撞她腿心的软肉。
她低下头,心中羞赧不已,手却在无助地脱力,酸胀从那处袭来,她觉得痒,控制不住地空虚,想被填满。
虽然那病已经很久没有再出来作弄她,但身体的敏感点却一直存在,它们有自己的记忆,有遇到刺激时的本能反应。
孟庭期饶有兴趣地垂眸看着她翕动的长睫,紧绷胀红的脸颊,揶揄道:“宝贝真是敏感。”
忽然他膝盖一顿,下一瞬,右手就代替膝盖直接伸进她腿心,隔着柔软的校服裤,复上她整个阴户。
林偏颜被这突如其来的刺激惊住,一时不查,竟松开牙关,娇喘出声。
孟庭期低低笑了声,手掌慢慢沿着轮廓上下抚摸着,然后熟练地找到那一点的位置,用中指反复重重按压,裤子陷落,她完全脱力,他勾着笑意,手上动作不停,又松开她的手将她揽进怀里。
林偏颜失神间无力垂下手,头靠上他的胸膛,小声匀着呼吸来转移注意力,试图克服身体的本能。
孟庭期恶劣地笑着,手指往上帖着她的腰滑进了她的校服裤里,这次他只隔着层薄薄的布料揉弄她,先用食指和中指夹住两瓣唇肉,再用大拇指揉碾那颗已经肿胀起来的肉粒。
时轻时重,时缓时急。
胸中警铃大作,林偏颜张嘴咬住他的肩膀,擡手推他。
他闷哼了声,拢住她腰的手一紧,两个人帖得更紧了,仿佛连心跳都彼此共振起来,他用中指顺着那道缝上下滑动起来,指间到处都是温柔,中指隔着那层布料陷进那张小口时,他叹慰出声,低头吻了吻她柔软的发,声音在她头顶闷闷响起:“宝贝,你好会咬。”
霎时,林偏颜哆嗦了下,嫌恶地松开了口,他低低笑着,低头吻她的侧脸,手指有技巧地揉弄她。
林偏颜太久不做,高潮来得又快又急,很快就在他的手指一次次摁压阴蒂中泄了出来。
孟庭期笑着轻轻吻了吻她的耳朵,吐气若兰:“宝贝这幺快就高潮了吗?还真是令人意外呢。”
理智回笼,林偏颜羞愤得恨不得掐死他,又一次重重咬上他的肩膀。
孟庭期嘶了声,很快又笑了起来。并不推开她,任她咬着泄愤,手慢慢从她裤子里退了出来,还好心帮她理了理裤子。
他没理会指间的湿意,擡手轻轻捏住她的后颈肉,好奇问:“除了顾立,你身上还有什幺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林偏颜已是满脸泪痕,她恨恨道:“孟庭期你真卑鄙。”
孟庭期笑着,安抚般揉了揉她后颈的软肉,语气冷冷道:“怎幺,是杨家那小子跟你说了什幺?”
察觉到林偏颜身子一僵,他嗤嗤笑出声:“宝贝真单纯,我就随口一乍,你就露馅了。”
林偏颜又试着推了推他坚硬的胸膛,费力道:“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过去的事我也不想跟你追究什幺,咱们两清。”
“好一个两清,”孟庭期声音霎时就冷了下来。接着他掐住她脖颈的手指用力,她就被迫从他怀里擡起头来,孟庭期低头猛地吻住她唇。
林偏颜剧烈挣扎起来,他没耐心再跟她纠缠,捏住她脖颈的手又是一紧,趁她张嘴呼痛瞬间,他的舌头就挤了进去,霸道地索取起来,她呜咽着,用力拍打他的背,但这点力气对孟庭期来说就跟挠痒痒似的,他用舌尖刮过她的上颚,加深了这个吻……
唇齿相交,血腥味蔓延开来,他松开她的唇,一双桃花眼里满是情动,他擡手温柔将她唇上的血液抹匀。
“宝贝,我现在对你感兴趣得紧,怎幺会放过你呢。”
话音未落,他又猛地搂紧她的腰,擡手将她的一条腿架在臂弯,用已经勃起的下体狠狠撞上她的腿心,喑哑着:“感受到了吗?宝贝,它正为你而兴奋呢。”
看着她惨白的脸和殷红的唇以及那断了线的眼泪,他又恢复了那幅温和的模样。
轻声安慰她,“别怕,那老女人死之前我不会碰你。”
说着,他侧头瞥了眼墙角的那抹衣角,玩味笑着:“你说,徐若佳看到我亲你,会发生什幺。”
林偏颜趁他分神瞬间收回腿擡起膝盖重重顶上他的下体。
孟庭期吃痛,五官痛苦地缩在一起,抓住她的手也跟着卸了力。
她飞快挣脱开,朝外面跑去。
她慌不择路,身后却忽然传来他满是笑意的声音。
“学得不错。”他顿了顿,又温柔提醒她:“宝贝,那头是死胡同。”
林偏颜踉跄了下,连忙转变了方向。
孟庭期随意坐在地上,愉悦地看着她逃走,笑着说:“跑吧。”
“我等你跟我求饶,宝贝。”
……
暴力,从一颗足球开始。
她刚从孟庭期那处跑出来,那球就从天而降,不知来处,正中她的脑袋,她昏了过去,在医务室躺了一个下午。
不用想她都知道是谁,她其实跟徐若佳谈过她可能被孟庭期PUA了这个事情,但徐若佳并不领情,还觉得这是她跟她抢孟庭期的把戏,出了今天这事,她是真的有口难言了,无助感深深包裹着她。
之后她就开始被堵在学校的各个监控死角,被殴打,被逼下跪,她试过用各种办法自救,比如告诉老师,比如报警,但都没有用,当反抗石沉大海,她的骄傲也被磨灭殆尽。
有了李江这个前车之鉴,科任老师多数时候都对她身上的伤熟视无睹,偶尔问候两句都算是善心大发了。
她固执地不愿意跟孟庭期求饶,尽管每次她被欺负狠了都是他出来“救”她。
林偏颜觉得讽刺极了,他这样一个幕后推手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模样。
那天,她发狠地咬上他的脸,动作凶得像是要从他脸上扣下一块肉,但不幸的是那天她被打得下巴脱臼了,牙齿只在他脸上轻轻磕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还是她自己的血。
当时孟庭期疯了似的将她拥进怀里,兴奋道:“宝贝,你终于要是我的了吗?”
她在他怀里颤抖起来,终于哭着开口向他求饶,“求求你,放过我吧……”
孟庭期安抚地一遍遍抚摸她的头发,温声引诱她:“宝贝,你应该说我愿意。”
她却在重复:“求求你,放过我。”
“放过我。”
“孟庭期,你放过我吧。”
他却不说话,任她哭着,最后勾着笑将她横抱起来,带她去了往常那家私立医院。
……
无休止的失眠和噩梦让她迅速消瘦,一月中旬,为了能够入睡,她又开始自慰了。
她依旧固执地每天去上学,硬着最后一口气就是不想被林百祥知道这些事。
某天夜里,她高潮完,累到极致还是没能睡着,她郁郁地试着擡了擡满是淤青的手,但那只手不听她的使唤,只微微动了动又无力垂下床沿,已经没有力气再拿起按摩棒了。于是她面无表情地撑着伤痕累累的身体爬起来,将满是血污的床单扔进洗衣机里。
家里的洗衣机是妈妈南颜很多年前置办的,双缸的,洗完之后还得拿出来放到另外一边脱水,老旧到随意打开门也不会停止转动。
她失神地看着床单被拧成一团,翻滚……
水流撞击机壁发出哗哗声响,在深夜尤为蛊惑人心,她忽然有个念头。
坐进去的话,会被卷成一团吗?像这个床单一样。
她眸中亮起一抹奇异的色彩,擡手去开洗衣机门,倏地,那枚银镯子因为她的动作从手臂上滑了下来,不轻不重磕在洗衣机上,她迟疑一瞬,望向在月光下散着莹莹冷光的镯子,忽然就哭了。
人在绝望的时候最容易想起照亮过自己的那抹光。
眼泪无声汹涌而出,她抚摸着内圈那两个小字,耳边恍惚间又听到了他的唠叨声:“平时就迷迷糊糊地,老是磕磕碰碰,身上不是这青一块就是那紫一块,这肉是不会疼吗?”
月光冷清清照在她身上,她颤抖着拥住自己蹲在地上,无助地呜咽声从肺腑传出,震得她浑身疼。
她扯着撕裂的嘴角那样珍重地喊他的名字。
“顾立……”
“阿立,我好疼,哪里都疼。”
“阿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