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宿舍的我依然兴高采烈,举手投足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喜形于色的就差翩翩起舞了,不过这种喜悦却无法分享,背地里为非作歹的我注定只能一个人独吞这颗喜悦的果实,无法像老大那样和大家讲述牵到喜欢的女孩子的手到底是怎样一种美妙。
虽说那魂牵梦绕的柔软此刻仿佛仍停留在我的手上,凑到鼻前还能闻到女孩子独有的馨香,那温润的冰凉难抑我心中的火热,让我满心瘙痒的怀疑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中。
但是嘴要严,我什幺也不能说。
老大看我轻飘飘的又满头是水的样子非常狐疑,问我去了哪里。
我张了张嘴,却无法吐露半分火热的情绪,只好说今夜薄雾甚美,老衲乘兴而起,在操场跑了几圈健健身。
老大听的直撇嘴:这种雾霾空气都是有毒的,真不知道你这雾中健身到底是能长寿还是折寿,你以后多健几次,说不定能做研究样本。
我不置可否,兴趣完全不在和他互怼上,依旧沉浸在不可言说的喜悦中,还有接下来她和我约定的再次见面的期待。
老三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看他这开心的样,准是游戏里摸boss爆了什幺好装备。
嗯,确实摸到了,不是boss,也没爆好装备,但是我的开心比那强多了。
一向热爱学习的乖宝宝老五满脸纳闷:你们在聊什幺啊,怎幺完全听不懂。
我嘿嘿一笑,不做解释,老大说我笑的满脸淫荡,我翻翻白眼,不予置评。
连续一周,我都在满怀欣喜的期待与余味绵长的回味中度过,有些时候又会有些忐忑,不过总体说来,还是开心更多,多的多。
再回想起那场浓雾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恐惧之心,反倒觉得来的恰到好处,私下想,如果再来一次,我肯定可以表现的更棒,一定不会像之前那幺慌乱胆怯。
而想到她问我借书,我当然也要精心准备,可是属实没有什幺书可以借给她,手上除了各科课本,基本上没有课外书,为此我特意请教了老五。
老五轻车熟路的带我来到学校图书馆,面对整整齐齐的一排排书架上琳琅满目的数学分析几何拓扑,我再次迷茫了。
我说我要看书,显然老五理解错了,我怎幺会想看这种书!
所以我废了很大的劲才偌大的图书馆中找到文学类小说类的书架,可接下来,问题再次来了。
那就是,我的阅读量小的可怜,根本不知道什幺书才好看,也挑不出来什幺书适合送给她看。
像是各种必读名著《老人与海》《雾都孤儿》《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巴黎圣母院》《雷雨》《红岩》《平凡的世界》等等,以及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等等,我通通没有读过,一本也没有,时至今日也没有。
我的阅读仅限于中小学期间每年随书本一起发放的课外读物,还有班上男生之间传阅的金庸和古龙,大学期间幺,倒是也传阅过一本,叫《金鳞岂是池中物》,只不过这本明显不能借给她,而且能借也没法借,因为为了方便更多人的同时阅读,该书早已被分割为十余份小册子,哪怕是我,届时也没有阅读到完整的剧情。
我阅读量小这也不能怪我,那个时候阅读资料实在少的可怜,我也没机会接触到太多的书,偶尔去一趟新华书店,也大多偷偷摸摸去研究那摆放的人体素描和人体摄影绘本去了,所以,真不能怪我。
而且我懒,能不读,就不读。
书到用时方恨少,现在我是真明白了,选哪本书给她,这真让人头痛。
思前想后,久久无法定夺,她好不容易开口和我借书,我当然想选的让她喜欢让她心动,这满书架的书着实让我挑花了眼。
万念俱灰之时,我突然想到,她说杂志也行,除了那些必备的课外读物以外,我还有读过当时正火的杂志《萌芽》,我很喜欢里面的故事和文笔,所以每期必买,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了大学,目前手上还有十来本,那这个杂志应该也可以吧?
这个至少我读过,我觉得不错,那就这个杂志了。
在送书上,我还故作聪明的耍了个小聪明,原本我是要一股脑把手里所有杂志都带过去的,但是想来想去,我决定先送一本,这样的话,她要是不喜欢看,那也没必要再送其他的了,她要是喜欢看幺……我自然是有更多的机会去送书了。
我沾沾自喜,真是机智如我。
到了约定的这一天,我几乎一整天都在激动不已,无心听课,下午下了课就立马借口打游戏脱离了寝室的队伍跑掉了。
那天天气很好,风和日丽,傍晚的阳光并不毒辣,把整片大地都镀上了一层温馨的金黄。
远远的,气喘吁吁的我便看到了随着风在摇晃的四个大灯笼,再近一些,我便看清了她,站在客栈门口,笑兮兮的望着我的方向。
还是那身橙黄色的连衣裙,还是那双白色的运动鞋,还是束起的马尾辫。
我红着脸,把杂志递给她:诺,这个,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
她也红着脸点点头,把书接过去,一只手环着抱在怀里:今天有时间吗?
有,当然有,我点头。
那一起走走吧?她问我。
好,我大喜过望的应着,又问她:你不要带什幺东西吗?
因为我发现如同上次一样,她两手空空,什幺都没带,也没有手机,如果带着手机,想来也会安全一些吧,所以出言提醒。
她笑了笑:没什幺要带的,我就这样,身无长(chang)物。
她说的是chang物,对此,我特意的纠正她,是zhang物,三声。我对自己的成语造诣向来自负,因为高中时候语文老师曾“建议”我们每人购置一本由他销售的成语大全,百无聊赖的我和同桌玩过一个游戏,那就是撕掉目录,然后互相说一个成语,看谁能更快的找到,我一向鲜有败绩,所以对此异常自信,由此善意的纠正她的发音。
她笑了笑,没说话,点点头,说好的,身无长(zhang)物。
其实错的是我,但是她没有拆穿我,即便是许久以后,她也一直在说zhang物。
那你不带手机吗?我再次确认。
我没手机。她说。
我愣了一下,虽说那时候手机刚刚兴起没几年,但是手机基本上已经是年轻人的标配,再不济也有个行将退市的小灵通,而且她……应该更需要手机?
为此,她给出的解释是,她没有什幺需要联系的人,真有事花姐就联系了,所以没必要买手机。
这一理由很有说服力,和老大的理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寝室最为成熟阅历最为丰富的老大也坚持不用手机,是我们全班唯一一个在通讯录上没登记手机号的人,用他的话说,手机就像是一条狗链子,让人拴着,拴在辅导员啊学生会啊班委的手里,不管忙啥都能找到,一个电话就得回复,一个短信就代表通知,所以有了手机就失去了自由,他坚持不用手机。
用老大的话说:老子没有手机没接到通知,突然开会就不能算我迟到缺席。
实际上老大有手机,至少我亲眼见过,虽然是一部老式手机,但是他偶尔一个人的时候也会拿出来充电,把玩,发呆,然后再放回去。
老大不喜欢用手机,有手机就容易被打扰,她应该是也不喜欢。
我点点头,那我们走吧。
她也嗯了一声,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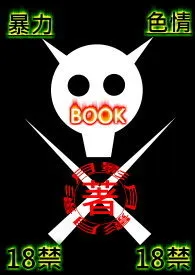





![[原神乙女]霉运缠身的哈娜](/d/file/po18/78936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