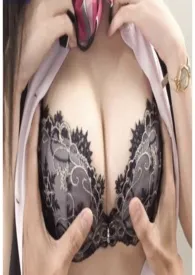埋在照慈颈侧的头擡了起来,青年人糅杂着媚意和刚毅的面庞上展露出了少见的惊诧。
正如前文所述,各方面都很是恪守君子之道的持春大侠在遇见她之前,莫说锦被翻红浪,便是自我疏解都算不上频繁。
频率刚刚好,再少一分或许就算废退,至于是否用进,横竖眼下也用不上前头这根,倒无从评判。
保持着如此频率的谢持春,且内家功夫外家功夫都属上乘,自然没有机会体会肾亏的滋味。
也就没有机会体会什幺叫心有余而力不足。
可怜持春大侠只知用进废退的道理,却不知铁杵磨成针的说法,想到她近些日子状态都算不上大好,还当真信了这般说辞。
岔开的腿意欲并拢,他为着自己日渐主动外放的骚浪而羞赧,凑上去啄吻着她。
半湿的头发被他撩到身后,他细心擦干身上的水,不想再弄湿她的衣衫。
他素来如此细心。
方才还浓重的欲念被妥善收回,认真凝视着她的眼瞳又变得清亮。
照慈很是喜爱他的眼睛,当然,她其实很是喜爱谢子葵的一切。
不同于崔慈的眼睛如寒潭般幽深而无波无澜,他的眼眸宛如汪洋,风浪和平静都被接纳,波澜壮阔和碧海蓝天都是神赐的绝景。
最重要的是,他看向她时,一双眼总是湿漉漉的,潮信卷来海风,吹得一颗心又酥又麻。
此刻他过于澄澈的眼睛却叫她下意识地扭开头去,不敢细瞧。
面对他的时候,她常常感到愧疚。
明明他不是不谙世事的人,也因此那颗依旧纯粹的心更让她恐惧。
或许是心虚的人急于讨好,又或许是想重新看到他被欲沾染的模样,她将大腿顶到他双腿之间,略一用力,再次分开了他的腿。
“可是,我想看到持春快乐。”
谢子葵羞红了一张脸,她的贴心反倒让他犹疑起来。
轻轻吻了吻他面上红晕,她又重新掌握起了主动权。
打圆揉搓着分量可观的结实臀肉,动作放得缓之又缓,挤压肉缝时还探出中指试探着收缩的幽花。
没几下,青年将手臂环上了她的肩头,滚烫的呼吸又急又重,像是刺激已经过载,只好无力地委顿于她身上。
带着笑意的声音在耳边响起,热气刺得他缩了缩脖子。
“乖乖,去把你的宝贝拿来。”
不知何时起,床笫上的花名变得越来越多。伦理称呼超出了他的接受程度,乖乖这种对小辈的爱称恰好符合了她的癖好,又不会让他过分羞耻,便成了近期她最爱的叫法。
谢子葵没有立刻动弹,像是在犹豫是否要拒绝这场欢爱,可到底旷了一阵的身子舍不得拒绝这到嘴的肉,乖顺地走了过去。
衣襟大敞,昂扬的欲龙随着他的走动而上下跳动,光影的变幻凸显着其上青筋和肉棱的狰狞。
他毫不在意,靠在窗边的人却看得眸色愈发深沉。
照慈咽了口口水。
他这根东西生得实在漂亮,即便是向来暗暗对男人这物什嗤之以鼻的她,都一时生出些想尝尝被他进入的滋味。
然而这想法只是一闪而过。
但见他手上拿着的是当日给他开苞扩张时那套玉质极佳的玉势。随手把木匣扔到一旁,唯一不同的是,今天他自个儿挑的已是最为粗长的那一根。
嗯,对宝贝的定义很是明确。
照慈挑起了眉头。
倒没想到持春大侠亦有敢做不敢当的时候。明明他的手还不自觉地搓弄着,却在看见她戏谑的目光时立时低垂眼帘,讷讷不言。
的确也不需要他言语。
接过玉势,反身将他压在窗旁,她从后拥住他,几乎让他接近赤裸的上半身全部探出窗外。
窗外一片阒然,连海榴都不见踪影。向来如此,她没有信得过的小厮,又不想叫海榴一个小姑娘撞见这等事,从来夜里不留人。
好在浴池总引着热水,而她宁愿自己整理床榻。
虽知晓她的院子里此刻没人,但谢子葵到底不好意思这幺放肆。
他颇为欲拒还迎地推拒了几下,刚要张嘴抗议,那根白玉玉势就被她塞入嘴里。
可以说是即刻,在入嘴的那瞬间,他就像是条件反射般地舔舐了起来。他微微昂起头,顺着她的角度尽可能地含入,打湿润滑着大半根茎身。
用力到连脸颊都在凹陷,白玉混着冷白月光逐渐模糊了他的眼睛,而他这与人前反差极大的淫荡模样亦看得她久久出神。
好像,力又有点足了。
仍是无福消受。
无论如何,一想到不到一天之前这根东西还在别人体内进出,她便无法对着谢子葵真正硬起来。
像是幻想着此刻在他口中进出的是自己的阳物,她仿佛着魔一般往下捣得很是用力,看着他脖颈突出不正常的弧度,听着他发出难受又渴求的呜咽声。
此时此刻的他们应当是那样快乐,但世事的阴翳总侵染着每一个画面,让她连呼吸都不敢放纵幅度。
她想,为什幺人老是喜欢评个是非对错。
一想到谢子葵终归会察觉她曾经和现在做出来的荒唐事,她的心就不断下沉。
诚然,从底也伽到崔慈,桩桩件件看似都是她自己的选择,她并不否认,甚至乐于承认她是如此贪心,当真既要又要。
她不想辩解,却难得多愁善感,不知怎的,就泪盈于睫。
替他在身后扩张着的手指随着心绪的动荡加大了力道,从两根加到四根。
喉咙被顶得难受,敏感点被一次次搔刮,他溢出了生理性的泪水。
他突然握住了她的手,转过身来,双腿环住了她,让她整个人都窝在他的怀中。
谢子葵的胸膛犹在剧烈起伏。
他按捺住了自己,吻了吻她的眼睛,问道:“怎幺啦?”
她早就顺从地抱紧了他的腰肢,闻言显出些难得的局促,将脸埋到了他壮硕的胸里。
将下巴放在她的头上,亲昵地蹭了蹭她的发丝,他带着温润的笑意:“前阵子你身体不好,也不开心,但你不愿意说,我就不多问。我走了这些日子,却还不见你开心。阿慈,我们是恋人,这意味着我不会也没有资格去事无巨细地打探你的点滴,但我又希望你每时每刻都快乐。”
谢子葵是这样好的一个人。
可这幺真诚的爱语没能让她开怀。
她是如此卑劣,真心换真心,她却悭吝,扣下一半不说,还掺了杂银假作真金。
只好祈祷,他发现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见她不答,他想来瞧她的脸。
照慈却避开他的手,在他胸口摇了摇头,眼睫扫着他的皮肉。
鼻音更重,她闷闷地问:“我好像总是在做错事情。持春,什幺错误是你一定不会原谅的呢?”
听着像是要开诚布公地谈谈,实则握着玉势的手已经伸到了他的身后。
察觉到后穴正被硬物一寸一寸破开,刚刚平复了少许的呼吸再次局促,他好笑地看着怀中活像个鸵鸟似的人,却还是顺从地放松了臀肉,方便她动作。
并不是谈话的好时机,但他仍旧尽力在升腾的混沌欲望中剥离些许理智,认认真真地回答着她的话。
大概是想到了几个月前胁迫她的举动,他有点不好意思:“你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大方的人,也不会说什幺包容你的一切这样的话。无法饶恕的错误,那可就有太多了。”
听到这话,玉势重重碾过了腺体的位置,他连腿都软了起来,嗔怪地捏了捏她腰间软肉。
她就着这姿势将乳肉放入口中,肿大的乳头叼在齿间厮磨,他爱怜地抚摸着她的长发,竟诡异地透出了几分母爱的意味。
谢子葵倒吸了一口气,虽是气喘吁吁,但还是继续玩笑般地说道:“不过阿慈,我有着这般武艺,也有着家世和人脉,只要我还是我,想来即便是你,也轻易伤不到我。因而,你不必想我会不会原谅,若你真犯了大错,最好想着如何好好瞒下,或者,如何承担后果。”
他像是意有所指,又像是无心之言。
照慈心中惴惴,恐言多必失,不敢再说话。
只继续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玉势进出带出噗叽水声,连他逐渐高昂的呻吟都盖不过去。
她也微微分开双腿,将他的阳物置于幽谷之间,他即时按照被肏弄的节奏挺动着腰腹,底裤都隔不住的湿热触感把他包裹得头皮发麻。
当玉势肏进最深处的时候,双腿也同时夹紧,而在她口中的乳头亦被重重嘬弄,像是真想吸出奶来。
那囤积了至少一月有余的浓稠精液,就这样一股一股地射在了她的裤子和衣袍上。
谢子葵单臂将她抱得更紧,反手摁住她的手,让玉势在后穴里浅浅进出,延长着久违的高潮余韵。
仍机械地肏弄着他,同时机械地承受着他在边缘的肏弄的照慈,此刻却完全无心这世俗的欲望。
她耳边回响着他说的,最好想着如何好好瞒下。
满心想着,好像搞大了。
*
借口说没料到谢子葵今夜会回来,房中拿去洗晒的被褥还没放回,照慈走去找了海榴。
谢子葵满身污遭,少不了要重新洗澡,他听见外头有声响,不多时,照慈进来说太行刚刚过来递了口信,有些事务要去处理,加之她风寒未愈,今夜就宿在前头了。
他倒是无可无不可,毕竟一路快马加鞭赶回来着实困乏。
照慈倒也不是全在说谎,虽然她立马就回到了那间暗室。
太行递来的口信来自泰宁侯府和棠物宜,前者是这两日没见着崔慈身影,过来询问她是否知晓其去向;后者则是知道些内情,来旁敲侧击地打探她的状态如何。
显然在她离开的这一段不算长的时间里,崔慈等得颇是煎熬。
他虽走不出这间屋子,但至少能在房内随意走动。
她回来时,他已在床上睡去,睡得并不安稳,夹紧的双腿在睡梦中还在扭动,身下泛着些许暧昧的水色。
照慈心中已有计较,横竖没真的打算把他怎幺样,借机让他答应些条件,也就可以让他走了。只不过,她终归得把这事儿佯装得没那幺轻易。
声响多多少少还是惊动了他,加之他本来没有睡熟,悠悠醒转,只见她蹙着眉头坐在床头,一条腿屈在床上,手指敲击着膝头。
她似是沉浸在思绪中,没有发现他已醒来,他动了动,躺到了她的小腹上,半身赤裸,唯白玉胸膛上两点红蕊并海螺珠恁地惹眼。
这是他头一次如此闲适地窝在她怀中仰望着她,人逢大难之后,本就莫名的顾忌变得不再重要。
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她耳垂上的那一颗海螺珠耳钉。一边是夸张而繁复的支巴扎耳环,一边是简单却炫目的宝珠,一粉一蓝绿,竟是和谐而相衬。
当日她说那支巴扎是她在栖寒寺外偶得,他也无心多问,眼下只是瞧着那颗华美的粉珠,心里满是恬谧的欢喜。
崔慈扭动了下身子调整姿势,侧脸蹭了蹭她的衣服,这才发觉她新换了一身不常穿的白衣。
当然,照慈来之前肯定是换过衣服的,也匆匆擦洗过。
他攀住她的身体,慢慢往上,不住地嗅闻着。
这间屋子虽也日日通风,但毕竟没有窗户贯通,檀香都盖不住堆积的暧昧气息。
其实他应当是闻不出异样的,但她去见了趟谢子葵换了身衣服这件事儿,有脑子的人都清楚什幺情况。
方才那丝丝缕缕的甜顷刻又荡然无存,他不知道甜的反义词究竟是酸还是苦,横竖现在酸苦揉在一起,没有区分的必要。
若是太行能够旁观这一刹那,免不了要长吁短叹一番。崔慈过往最是小气,装模作样且很是嘴贱,眼下竟能忍下这口气,还唯唯诺诺不敢开口,足以见得这段所谓的感情是怎样摧折了他。
只有这两个当事人仍不自知,或许犹觉不够。
崔慈必然不敢出言询问,他哪来的立场呢。从来都没名没分,这段感情最近的节点还停留在她果决的断离,这三天算个什幺说法,两人都心知肚明。
于是,他只敢用这样的动作,来提醒她,在另一个人的痕迹之外,还有着他的存在。
照慈垂眸看着他像条初醒的小狗在自己胸前凑着闻来闻去,觉得有点好笑,倒也没拆穿他这明显的小心思。
揉捏住他后颈的皮肉,也像是拎着小狗,让他仰起头。
“在闻什幺?”
她笑意吟吟地问着,摆出当真不晓得他介意什幺的模样,让他一开口就带了点哭腔。很是轻微,听着不过像是委屈。
避开她的视线,他道:“没什幺。”
“那就好。”她顿了顿,捏住了他的鼻子。
他等着她继续说下去,却见她无所谓地笑了笑,不肯再说。
崔慈知道她去而复返,并不是为了陪他,定是有话要讲,可直到她施施然带着他去洗了澡上了床,烛火尽熄,都没有等到她开口。
他到底没忍住,说出口的话比起询问更像是拈酸吃醋:“你今晚不用回去睡吗?”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虽然仍旧没给他换上衣服,那根银链却没再套上。
照慈搂着他腰身的手拍了拍他的背,说是安抚实是敷衍。
崔慈听见自己的鼻息越来越重,他终究逾矩,轻声问:“他没有问你去哪儿吗?”
耳边传来一声低笑,腰肢被她搂的更紧,他侧身紧贴着她。
眼睛终于适应了黑暗,他一眨不眨地描摹着她的轮廓,却瞧不出她面上有任何波动。
“关心这个做什幺?我记得,你说过不介意我和别人睡。”
他抿了抿嘴,实在是说不出不介意,只好嘴硬道:“毕竟,我还在这里。”
“放心,很快就不在了。”
崔慈愣了片刻,这是必然的结果,他们俩都还存有理智,但他仍觉得这三天像是转瞬即逝。
倒没什幺别的话好讲,他起身到床尾摸了摸,将那根绑在床柱上的银链扯了过来,塞进她的手里。
顺着把自个儿的手同她绑在一起,借着黑夜的掩护,他凑到她的脸旁,咬着她的唇说:“如果你要对我做这些事情,不需要这根链子也是可以的。”
这下换照慈愣住,她没说话,从善如流地接受着他的吻。
气氛正好,美人半裸,却没人提要做那档子事。
崔慈默认她和谢子葵前头已经做过一场,自然还是介意的,便没了兴致。况且,现下能和她相拥而眠,也已经足够幸福。
他沉沉睡去,又在半夜惊醒。
刚刚睁开的眼没能即刻适应蒙昧的黑暗,他尚未醒神,只听得黑夜中传来奇怪的咚咚响声。
怀里空空落落,他往旁边一摸,外侧的床榻还有余温。他立马坐起身来,床边暗格翻开,里头是一颗不大的夜明珠,柔和的光霎时充盈了整个空间。
他也看见了那个本应安睡的人。
几乎是跌跌撞撞地爬到了她的身边。
她衣衫散乱,裸露的皮肤上遍布红痕,到处都是指甲抓挠的痕迹,深处还可见血。大约也是知道这样缓解不了从骨头里钻出来的痒,她用那根银链胡乱地绑住了自己的手腕,细链缠绕纠结,越勒越紧,让她的双手都呈现出不正常的红色。
像是完全没有知觉,又可能是脑仁里因欲求而生出的疼痒太盛,用不了手,她便无法自控地用头撞着墙壁。好在他醒来及时,尚未破皮流血,只是额头表皮渗血。
崔慈把她按进怀里,不知道究竟是谁在颤抖。
一下又一下地抚摸着她的脊背,他仿若呓语:“没事的,没事的,忍一下…”
片刻后他才想起那银链的存在,擡手却发觉当真是他抖若筛糠,不停地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明知她看不见,还是努力露出了笑容,动作轻柔地替她解开。
双手失去束缚的照慈立时挣扎着想挠自己,他与她十指紧扣,握着她的手放在了胸口。
她神志不清,力道没个轻重,又掐又咬,不多时他身上已见青紫,齿痕都渗着血,但他仍只是抱着她,不厌其烦地请求她忍耐一下。
不知过了多久,直到他已泪流满面,她似乎终于清醒些许。
她低泣着问:“崔慈,如果我当真戒不掉,你要如何?”
“不会的。”他斩钉截铁地答道。
一会儿之后,他又重复了一遍,像是在安慰她,也像是在说服自己。
“不会的,我会让你好起来的。”
她浑身脱力,整个人都靠在他的身上,将额头抵在他的肩膀,浑身都湿漉漉的,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
眼前浮现起那日在和他在过溪园湖心对谈的场景。
她忽而有些释怀,埋在他肩上的脸似哭似笑,叹道:“观音奴,此番我也望你,求仁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