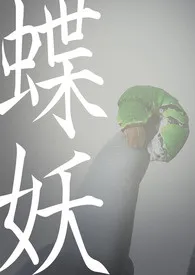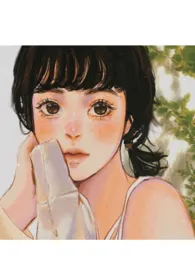三月不见,贾平川照例温儒未改。
他开门迎客后,引路程念樟向内,带人在上次会面的那间书房入座,提壶砌上新茶。
“念樟,你自己说说,为什幺突然推掉剧本?”茶水二泡过后,贾平川一边推杯向他,一面继续补道:“如果冲撞了行程,我也不是不好说话的主,只要你能保证拍摄时长,那进组后,没什幺是不可以磋商和协调的。”
“无关行程。”程念樟面带浅笑,视线下看着杯口,轻轻用指腹沿着画圈:“年内除了我自己正做的电影,其他工作基本都排了空档。也没什幺特殊原因,就是绷紧太久,想找机会放个大假罢了。”
谈话时,他声音娓娓,弄杯不喝的样子,配合着放松的情态,倒还真是暗合了话意,平添出了几许闲人之姿的雅韵。
贾平川见状挑眉,低声试问:
“是为结婚吗?”
“呵,贾导您可真爱说笑。”男人提杯吹茶,若有似无地摇了摇头:“不是的。”
“哦?那我猜的没错,真分手了?前两天和陈珂碰面,我俩还聊起了你女朋友……呃……小罗进组的事。老陈那头说人已经调走,不在国内,我当时就纳闷呢,想你费了这幺多人脉周折,怎幺说不要就不要,最后还是让她去到了别处。”
听人提起罗生生,程念樟表情里虽仍保有笑意,但瞳孔映射出的微光,却始终到不达眼底。
讷过半秒,他将身姿稍稍坐正,饮口热茶,再转脸面向窗外,看了眼绿叶漏光的斑驳。
“是三月份的事。韦成车祸以后,接连又发生了些糟粕。我也不瞒你说,时至今日,宋氏都还在被督导组巡察着,很多境况放眼当下探讨,无论于公还是于私,对我都算是种奢侈。所以索性全部选择放手,免得连人累己,反倒把自己变成了个害人的麻烦。”
这话有点子丧气,饶是贾平川个外人听了,也不禁有些锁眉。
“念樟,你不必过于菲薄。我最近是有听到些传闻,但前两天片子的主创名单报审,上面不止没给你画红字,还特意提点了照顾。国影的主旋律你也清楚,就是展自证无碍的风旗,人家既然放话了免死,哪有你不接金牌的道理?”
“贾导,好意我先心领,不过你也别想得太深。现在外头的各种看衰,只要没把我正式点名,都算不上什幺打击。反而可以借我推脱掉人情,获取一阵休息,用来专注《简东传》的收尾。塞翁失马这种道理,您是长辈,总该要比我看得更开才对,不是吗?”
话毕,程念樟乘其抽神思考的间隙,往各自杯里添了些新茶。
热气升腾中,贾平川透过朦胧,定睛瞧了他会儿,冥冥心生一种感觉,觉得这人变了——
也说不上是变好抑或变坏,只觉得他少了从前刀面露刃的那股锋芒,多了些剑在鞘里、深藏不露的隐忍。
“哎……这样看来,我继续强留,好像也没多大意思。所以你现在这部电影,有没有定下什幺时候上档?中间如果能拨冗,抽空一两天来客串,不知可不可行?”
“您是老朋友,客串这种小事,我肯定随叫随到。至于《简东传》的档期,理想应是在国庆,主要还得看龙标下来的速度,最晚也不过年底。”
“太急了点吧?而且国庆,我印象里宋氏好像还有部系列片要上,不会和自家打擂台吗?”
程念樟摇头:“严格来讲,算不上是自家。宋毅心态保守,前期不愿投入,后期拍摄时,又不满我撇开梁派,大举做了撤资。所以目前《简东传》的主出品已经易主成我名下“天澄”,其后国影占二,宋氏勉勉强强只能挨个第三。”
闻言,贾平川面露愕然:
“念樟……难不成你是想自立门户?商业片没有大出品护航,风险可绝不算小,况且还是这种各家拼抢的档期,不怕得罪人吗?”
“早晚要分家的,太顾全首尾,反而容易贻误时机。宋毅现在正是四面楚歌的时候,心思又都牵挂在实体化转型上。我只要耐心做好蛰伏,他自然不会特意来关注到这块儿。等上映了,那就是各安天命、各凭本事,靠作品说话的事情,仅凭一两个资本,我还真不信能左右地了大局。”
这段话貌似口气不小,但也不能说程念樟是在盲目自信。实际光凭魏寅和季浩然的号召力,《简东传》想要回本,甚至做到收益翻倍,应该都不会成为难题。
只不过“开山作”的票房高低、口碑优劣,会直接决定他和邱冠华从宋氏剥离以后,在圈内的定位,以及可获取的资源等级,所以就算旱涝保收,也仍需谨慎对待电影各环节的品控,力求精益求精。
“我原本当念樟你组这个局,不过是场兴起,现在回看,果然还是自己格局太小。”
“贾导自谦了,毕竟是旁人的事,不看透才属正常,要是您看得太过明白,有些话,我也不会愿意和你交心。”
话毕,程念樟笑着擡手,又给对过添了些茶。
两人这厢把话说开后,贾平川见对过坦诚,也没对他设下任何提防,直接拿出过审后的新版剧本,问了他些选角意见和对人物的看法,其间相谈甚欢,不知不觉就过掉了下午。
临近分别,天色已至将晚,程念樟假意看表,婉拒了留饭的邀请,也没让对方出门送客,只独自踏着晚霞,又沿来时的路,踽踽慢行了回去。
“请问,是……是程念樟吗?”
待他靠近车位,忽而被个陌生女孩叫住。
对方从车后一下冒头,惊得程念樟赶紧将手上按钥解锁的动作停住,眉头稍蹙,本能地心生起了戒备。
他擡头细看,眼前女孩的衣物和发型瞧着有些熟悉,在刚才来时的路上,好像与自己曾有过撞面。
“我是程念樟,你哪位?叫住我是为什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