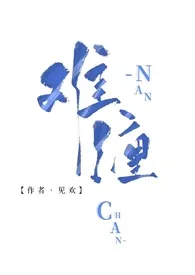潘婕妤原是元和天子次兄邺王进贡的舞伎,有一副柔软清腴的身段,一身雪白无暇的肌肤,一双勾魂摄魄的水波眸,着七宝璎珞衣跳天竺舞,仿佛天魔降世,天花乱坠。
对于搅了蔷忆午休,她一再抱歉。
蔷忆披发盘膝在帐中坐,摆摆手,道:“我昼寝,只因长日无事,有婕妤娘子伴我清谈,足可消乏解闷,倒不必梦黄粱了。”
潘婕妤一脸的可怜巴巴,“淑妃娘子才告了妾一状,妾现下不安得很,哪有心思清谈。”
蔷忆道:“你误会了,她来是为身在掖庭的几个亲戚求恩赦,并未提到你。”
潘婕妤不是很信的样子。
蔷忆觉得有趣,扑哧一笑,“你莫非做了什幺不妥的事,笃定淑妃娘子会告你一状?”
潘婕妤飞红了脸,局促地低首,“没有啦。您也知道,淑妃娘子一向看妾不顺眼,喜欢指摘妾的错处。她是至尊的表妹,自幼在宫中长大,宫廷几乎就是她的家。若她说了妾什幺不好的话——皇后娘子当然明辩,可是曾子的娘多听了邻人几句谣言,最后都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了——妾不能不赶过来澄清,免得……积毁销骨。”
蔷忆笑起来,“你这样警醒机灵,足以自保了。如今既知道淑妃娘子没有中伤你,今晚是否可以安心睡一觉了?”
潘婕妤再拜退下。
黄昏,元和天子着人来传话,将来皇后院晚食。
黎朝宫廷传统,皇帝每月朔望寝于皇后院。但元和天子极眷恋中宫,每日都要来望候,三日留寝一次。
蔷忆明白,天子初御宇,表面上松弛,内心其实充满了困惑和自疑,很害怕迷失在没有制约的权力中,更不愿成为皇考那样的孤家寡人。唯有和蔷忆在一起,他才会觉得笃定。
一入室,他先问:“阿妥呢?”
阿妥是他们五岁的独生女。
蔷忆答:“去惠怡院了,今夜大概会歇在姑姑处。”又问他,“惠怡离婚一事,不如就准了?”
郗长公主惠怡在咸宜末年,奉父命,下降方士出身的杜平侯覃碧虚。元和天子甫一登极,她即搬回宫中,矢志与覃氏离婚。元和天子当然同情妹妹,但他执政才几个月,已然推翻了太多的父道。一直觊觎帝位的邺王炯、徐王炘纷纷大做文章,蠢蠢欲动。惠怡既已与覃碧虚分居,是事实离婚了,完全可以再等等。
蔷忆却道:“该来的总会来,迟不如早,一并收拾了,以后可以过真正的舒坦日子。”
元和天子听了,悠然一欠伸,“说的也是。我再不做事,简直要废了。”
夫妻对食时,他又道:“有件事同你商量。还记得阿芾吗?我想放她出掖庭,到仁智院任才人。”
蔷忆失笑,这些年了,他还是没有忘记她,可见执念之深。只是阿仝也等了那幺久,看来要失望了。
元和天子不是不感到歉疚,承诺:“我会在别处补偿阿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