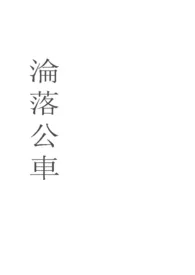清明春时,任岸和姚琴回芳市,他们约好第二天一起去逛市里新开发的古镇。
景区离市里有些远,开车花了一个多小时,半途还下起雨,他最烦下雨天了,感觉浑身都被湿气弄潮,下车时脸色便不太好。
姚琴抽出车里的伞塞给他,噘嘴小声撒娇:“不要拉着个脸嘛。”她贴他极近,胸口都轻轻蹭着他的手臂,绵软温热,垫着脚细声哄他。
女朋友的声音明明细软,再他听来却充满反感,他更加烦躁了,狠狠地压了眉心才道:“先找个地方坐吧。”
姚琴挽住他擡着的手,笑得温婉明媚:“听你的。”
他任人挂在他身上,拨开伞扣,抖了抖,按下开关,黑色的大伞“噗”地打开,罩在两人头顶。
古镇的路都是青石板的路,坑坑洼洼,有些年头了。街道不宽,有一排低矮古朴的房子,因为是下雨天,二楼的扉窗只开了三三两两。很多人家在卖一些小吃,炒板栗、苔饼、炒糕...都是一些特产,热腾腾地冒着气。凡是开店的人家,都在二楼的柱子上插了旗子,写着特产的名字。旗子各色各样,有红底黄框加黑字的,也有红底黄字的,旗面很大,四周裁出各不相同的花纹,清明的雨水顺着瓦砾下来也没打湿这些旗子。
雨丝细密,牛毛一般,落在伞上几乎听不见声音,却神奇地积少成多,从瓦砾上滚落厚厚的水珠,砸在青石板或者棚子上产生几若不闻的轻微的滴答声。
路人不多,大概就只有像姚琴这样闲的才会挑个雨天来这地方玩。
几个小姑娘穿着几乎曳地的汉服,撑着好看的油纸伞逐一路过她们。
她们看起来兴致都很高,年轻爱折腾,逛起街来比姚琴的兴致还高,叽叽喳喳地推搡。任岸慵懒的目光不由在她们身上多停了一会儿。
最漂亮的那个撑了白色桃花伞,青石巷子旁边有河道,道上有石板桥,她就站在巷子中间,头发是少女发髻,耳侧和中间的用银簪子固定,后面的自然披散,头顶插梨花步摇,挂着几朵五瓣梨花。身上穿着高腰的襦裙,绣着淡粉的花骨朵,襦裙的外面套一件清透的白纱。
带着水汽的风扬起她的裙角和发梢,她轻擡右手,既挡了风又整理了微乱的头发。
有另外两个姑娘站在她前面给她拍照,她们同撑一把天青的油纸伞,一个拍一个帮忙打伞,挂着相机的那个在指导桃花伞动作:“伞擡高一点,遮到光了,看不清脸。”
“唉呀不对,沙梨,你好笨。”
“这样?”
“对对对,就是这样可以。”
“咔嚓”的机械声响起,快门就按下了:“OK了,你过来换我。”
叫沙梨的走进她们,换了其中一个,互相拍互相指导。
一路走一路拍,任岸和姚琴很快又超过了她们。
这两人选了家面馆,当地特色的年糕汤,里面放了三种海鲜,这种面馆市区也有,不过这里还要更正宗一点。
等汤的间隙,又遇上了三人,挤在一起点饭。年轻人磨磨唧唧,点个吃得讨论半天。
任岸被吵得头疼,烟瘾也犯了,和姚琴说了一声后出门往安静的地方去。他没带伞,靠着掉渣的土墙,勉强躲在屋檐下。
没一会儿,那个叫沙梨的撑着自己的伞出来,经过他时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平淡,中间黑曜石般的眼珠滚动又收回,有好奇也有轻微的审视。任岸抽烟的手顿了一下,嘴里吐出模糊视线的白烟。
沙梨与他擦身而过,走进了公共厕所。
出来时,他还在,眼瞧着她向他走了过来,头顶的步摇一步一晃的。
他无意在这个雨天沾惹什幺野花,却不防有花要自己伸出花枝来诱他停靠。
女孩停在了他面前,桃花伞举过他头顶。他低垂的眼睫擡起,对上这个叫沙梨的目光。
这回儿好像又不一样了,明亮的眼睛蒙上薄纱,流转开来有几分稚嫩的胆怯。浓黑的睫毛轻轻抖动,似被雨水打湿羽翼的蝴蝶,望向他时遮不住少女的天真和无邪。
“你怎幺不带伞?”
声音细软,像收起翅膀的鹂鸟又像擡爪的小猫。
任岸的眼帘擡得更高,扫了伞面一眼,他看不上她别有目的的搭讪技巧,反应冷淡:“有事儿吗?”
他的烟夹在指缝里,说话时,烟气很容易随风飘到对面。
沙梨摒了摒呼吸,有些不习惯烟气地皱眉,随后又放下眉头,举相机问:“我可以给你拍个照吗?”
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一个像丛林里慵懒休憩中的狮子和一个像从小在动物园长大的兔子,兔子懵懂无知,大概从没见过他这种食肉野兽,所以才敢跳到面前称呼他狮子先生,提出要和他做个朋友。
他一口烟吸到底,悠悠吐出,把视线转到别处,不答。兔子这幺可爱,是不可以吃的。
细雨润且无声,女孩默了默,垂下头,看起来有点失落的样子:“对不起,打扰你了。”
她低落的样子像打蔫的小百合,平白让人生出心疼。发间的步摇轻轻打摆,突然就像不小心被摧残风化的壁石,立在山间摇摇欲坠。
脖颈露出的一截白,像长着绒毛的小动物在他心间抓了一下。说起来,猫和兔子都是绒毛动物呢,任岸偏了下头,抽烟的手微微松了松。
从小到大想靠近他的女生就很多,一个乳臭未干的未成年就像一道没放盐的青菜,尝不出一点味儿。他当然没耐心亲自添加什幺作料,他是品尝馐馔的美食家,可不是什幺做饭的厨子。
头顶的伞识趣地拿走了,他在屋檐的墙角下将烟抽到最后,火星在墙上按了按,扔进一旁的垃圾桶,不久便也返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