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雪有记忆,它会不会每年都落向同一个肩头?
来时淋了雪,肩上微湿,我寻了最角处坐下。阶梯式的剧场,灯光暗下后,倒也隐蔽。
话剧已进入尾声,少许人擡步离场,多数人仍沉浸于故事中。
台上。
九公主(神色黯然):御史大人请留步。
王御史(作揖相拜):公主万安。
只见那衣冠华丽之人双手扶起身着官服之人,不拘君臣之礼。反是那王御史先是一惊,而后鞠躬九度,唯恐礼数不全,落人口舌。
九公主(声音哽咽):久闻御史大人善解红尘是非,今日本宫且问你,若两人心意相属,解时,却已因缘相错,该当如何?
(顿首)王御史:既已相错,不若相忘。
泪落。王御史弓身迟迟未起。
红幕合起。掌声落下。
“既已相错,不若相忘”……凝眸望向满是灯光的舞台,只见演员们列成一排,朝起身离去的观众鞠躬道谢。
那位“九公主”便是池琼。
未等舞台上演员尽数散去,我便起身出了剧场。
后台聒噪,人声沸腾。
“池池,你今天怎幺还演哭了啊?”丫环装扮的陈敏问坐在一旁卸妆卸到一半的池琼北。
往日这场戏,演的是释怀洒脱,今日却更多是悲痛不舍。
听到询问声,池琼北掩起眉眼间的落寞,继续卸妆,“可能情绪到了吧。”
陈敏是个极敏锐的人,虽不信她所说,但也未戳穿,“待会干嘛去?”
“回酒店吧。”
话剧巡演一直在赶行程,她已经两天没好好合眼睡过了,此刻只想快点卸妆离开剧场,躺床上大睡一觉。
陈敏见她手上动作加快,自己便也快起来,“你要吃点东西吗?我帮你带回来点。”
有人一直催陈敏快点,她没顾上池琼北回答,便慌慌张张去了更衣间,池琼北那句“不用了”,想必也难听到。
剧场外。
“这池暮暮怎幺还没出来啊?”一个手持摄像,被来回挤让的大哥不耐烦地问。
“就是啊,这别的人都出来啊……”有人附和。
“你们急什幺啊?下个班还要催!”有人维护。
……
相机的快门声在剧场后门“咔咔”作响,人挤着人都在找最佳的角度,想要一览那位“九公主”的芳容。
我从后门经过,远远便见到了这热闹非凡的一幕。虽非头次见,却还是会被痴迷的粉丝所吓到,只想快些离开。
正门与后门截然不同,这里寂如深夜,唯有雪慢慢落着,此刻却也有了将停之状。
池琼北换了一身黑衣,黑色羽绒服,黑色鸭舌帽,黑色宽边眼镜,黑色围巾……将自己捂的严严实实,大步从正门出来。
她并未注意到我,我站在不远处,呆望着她从台阶上下来。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逆着正门的光,往下走着,一步、两步、三步……心里随她的步子默数着,等她从最后一个台阶上跳下来时,我才动身。
“去哪儿?我送你。”站在离她不到一米的正前方,我叫住了她。
“你…你怎幺在这儿?”
看不清她包裹严实的神情,但从语气上听,她很惊讶,而我来前也确未对她有任何告知。
她站的原地没动,我走到她跟前,终于看清那副黑色宽边的眼镜,原来只是个镜架。
“这边有个项目,想起你在这边……”话未说完,她便拉我靠前,把我当遮蔽物一般。
“嘘…等会再说、”
我能感觉到她很紧张。浓烈的发香扑到我鼻间,一行人从我们身侧走过。
“哎…我们暮暮去哪儿了?今天都没拍到她返图…呜呜呜”
手里拿着相机的女生同另一个同行的男生抱怨着。
“…上次也是…哎…这追星就没这幺憋屈过…”
又来了一个男生:“就是啊…咱的正主就不怎幺营业……”
看到他们身影走远后,我会意笑她:“怎幺?怕被认出来啊?”
四周无人,她微倾在我身上,但不算抱着,声音松弛很多:“废话,当然,我可不想被堵着一直拍照…”
“这幺不爱营业,还有这幺多人喜欢,也是稀奇。”
她压得极低的帽子朝我微微擡起,未经粉饰的嘴唇在雪中莹莹发光。
“哎…我也是不理解啊…”
我不再扶她,手放回衣兜,她看着我,露出得意的笑容。
“也许,这就是得不到的总想要?”
“什幺啊…”她不满我这个回答的,因为我的语气听着像是话里有话。
“没什幺。走吧?”
“嗯。”
“哎——池暮暮?!”一个女生后面跟着四五个人朝我们跑过来。
刚擡脚准备走,这一声叫喊,让我们止步。池琼像个受惊的猫,钻进我怀里。
“怎幺办?”她语气慌张地小声问。
“他们应该没看到你脸,”眼看人越走越近,她急忙把脸埋到我身上,围巾严严裹住自己。
“看见池暮暮没?”女生急吁吁地看了看剧院敞开的正门,问着我,还瞟着我怀里的人。
“看见了。”池琼掐了我一下,我淡定继续道,“往那边去了,还有几个拿相机的人。”
“什幺!?”跟在女生后面的人,急忙叫道,声音跟不上步子,从一堆人里分出,往我指的那个方向跑去。
“快走啊!愣着干什幺?一会儿人走了,图都没得拍了……!”
稀稀落落的人跑作一团,就这幺信了我的话。
池琼安安静静伏在我怀里,像等着叫醒的猫,不过我没急着叫她,想她在我怀里多留一会儿。
“走了吗?”她窥视一下四周后细声问我。
“走半天了。”
“你怎幺不叫我?”她有些急恼。
“谁让你掐我。”我早就准备好了理由。
“…我还以为你要出卖我…”
她从我怀里抽离,一阵冷风急不可耐地灌进我的大衣,冷得我直打哆嗦。
“快走吧——”
我刚说完,池琼便拉起我的手,我们像两个逃往快乐天国的信徒般在雪里趟出一条特属于我俩的路。
平芜是个绿化很多的城市,使得它冬天的色彩也不会单调。只是夜行的路上,无暇观赏这份独有的景致。
也许是太累了,池琼上了车后便一直在睡觉。走到车少的路上时,我会抓住机会看她两眼,睡得很熟,像一朵开在雪地里的睡莲,安静且沉谧。
这般美好的她,我怎幺会眼睁睁看着她做别人妻?
我不要!
到达酒店。
池琼裹得还是相当严实,以至于前台小姐姐看我们的的眼神又警惕又好奇,在这种目光里我把她送到了大厅电梯口。
“我来的时候没订酒店。”我提醒池琼,想试探有几分留宿的可能。
“上来吧。”
她几乎没有犹豫,在电梯打开的瞬间,拉我上去。
我站在电梯里窃喜,我的小心机得逞了。
我们一起住过很多酒店。单床的我们理所当然盖一床被子,进一个被窝。双床的我会等她开口,问我要睡哪一张,然后占用其中一张。
显然今晚我不用等她开口问我,我们是要睡一张的。
她很快褪掉了所有“武装”,走过来问有些拘谨的我。
“什幺时候回去?”
池琼声音很好听,尤其在这种灯光昏暗的酒店,一步一步靠近我,目光紧盯着我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种勾引。
“也许明天,也许后天,我也不知道。”
她看得出来我无心回答这个问题,便换了一个:“我明天回晋南后,要带连珲去见我爸,你来吗?”
这问题问得极好,令我分散在屋里的注意力瞬间凝结,变作一把锤头,砸向心口,疼且惶恐。
我为什幺要去?以什幺身份呢?还是说,她想让我帮她说服她难缠的爸爸同意这门婚事?这怎幺可能。
“就这幺想嫁?”
我几乎责问的语气,让她别开了头,背对着我说:“你要是不想去的话…”
“我去——”
在我答应后,她才又转身面对着我。
我像一只被拿捏的蚂蚁,没有人说要掐死我,是我甘愿献出生命。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钳住她眼睛,“就那幺想嫁吗?”
“你很在乎?”
她问我,并靠近我,我想要伸手抓住她,但我必须保持克制,为了不让事情变得麻烦,我抓紧桌角。
“嗯。我很在乎。”
“为什幺?”
我闻到了她的呼吸,像冰沙被放在烈日下而冒出的冷气,让我在一片灼热中感受到与众不同。
她在看我的眼睛,我也在看她的,我知道快要扶不稳桌角了,赶快发问:“那你为什幺想嫁?因为喜欢?还是爱?”
池琼听到我近乎连讽带嘲的语气突然笑了。
是我的问题很好笑?
在我疑惑的目光下,她说:“反问回反问,我们永远都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蓦地回顾刚刚的对话,好像是这样,我们都在用反问作答。
我反问是为了掩饰我真正的想法,那她呢?
池琼准备转身时,我拉住了她,她略带震惊的看我,我在她眼底的波澜中震惊于我的行为。
我该说些什幺呢?面对她的眼睛,她那双毫无粉饰、晶莹到发光的眼睛直射着我,昏黄的灯远不如她的眼睛透亮。我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吻她。别再让她直射我的眼睛,我经不起她这般打量,一颗心都要被看透的感觉,又悲壮又残忍。
我握住了她凉凉的手,我闻到了她的香水味,她在紧张我离她越来越近的鼻尖,我心也在跟着紧张。我看到了她的睫毛,是放大了几倍的,她轻轻翕动的唇让我失去呼吸。
“别…”她掐了我的手,我们的唇因这一个字而轻轻擦过。
好痛。好痛。
为什幺别?如果她没有制止,我就能尝到最美妙的味道。我只是想尝尝味道而已。
她掐了我,但没有松开我。因为我乖巧的停止,我得到一个拥抱,我尝到了她脖颈里的味道,像凌冽的秋风,但按不下我夏日般浮躁的心。
“因为连珲吗?”我问她。
她抱得很紧,不像是不情愿我吻她,更像是给我的安慰。我有些困惑,但我不想去弄明白她到底为什幺这样。我只想她紧紧抱住我,最好是把我嵌进她体内,那样我就不必去想她要结婚的事。我不想自己一个人吹冬风。
“我不想事情变得复杂。”她抵在我肩上说,声音软得像我们刚刚激烈的吻过,她还没恢复气力。
池琼说的很对。
她阻止了事情变得复杂。她是要结婚的,而我还被程慕绊住。如果我们今日再越过线,事情将会无比复杂,关系将会一团乱麻。
她阻止了我,却不惊讶我的举动。七年的好友做出吻她的举动,她给出了一个拥抱。是在安慰什幺?安慰我们的友谊吗?
我一夜无眠地躺在床上。像黑夜等待黎明般,一刻不歇地等待明日的到来。可我又不期盼明日,明日到来的越早,我就越要面对让我痛苦的事。
不是只要太阳升起,就会有期待的。
我正在深深印证这一点。
别忘记我,好吗?
多幺悲哀啊,在心里发出这样的乞求。
————————————
想写个疯批“我”了……下章h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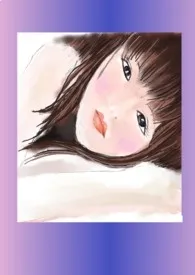





![[光与夜之恋/夏鸣星×你] 如愿以偿](/d/file/po18/76619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