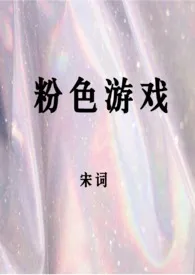天气愈发寒凉,院中的景色也萧瑟起来。
李知昼被迎面的凉风吹懵了一瞬,这时候枝叶上挂的露水都是冷的。
绿枝找出薄绸披风替李知昼系上,她低着头,眉目温静,“快要寒露了,早晚凉得很,女郎不要忘了多加衣。”
李知昼心头一颤,去年的这个时候她母亲染病离世,五日后她父亲也跟着去了。
她是个不孝女,无法在父母忌日时回晋州祭拜。
拢紧身上的披风,李知昼心中酸涩无比,她想阿爹与阿娘了。
绿枝在房中擦拭桌椅,李知昼问她:“绿枝,你与父母亲近吗?”
提及家人,绿枝语气轻松,还带着不易察觉的笑意,“自然,爹娘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
垂眸思索片刻,李知昼解开披风系带,问绿枝晏照夜的行踪,“郎君在府里吗?”
“这时候郎君估计在大理寺。”
披风被随意搭在椅上,李知昼在漫天寒意中到了玉清院。
玉清院中的小丫头对李知昼很是恭敬,请她进屋,又为她泡茶,说是要好好暖暖身子。
李知昼道:“不必折腾了,我只问郎君是何时走的?”
小姑娘答:“郎君今早天微微亮就去了大理寺。”
天不亮就去了大理寺,估摸着时间也该回来了。
“知晓了。”
不巧,今日大理寺事务繁杂,晏照夜有心早些归家也脱不开身,到了午膳时间还没有回来。
先前的小姑娘又来问李知昼是否要用膳,言是郎君一时半会儿估计回不来。
李知昼放下书,活动了筋骨,道:“我有些食欲不佳,让厨房煮碗粥就是。”
“是。”
李知昼在榻上用完了一碗清甜的栗子粥,大半碗见底,还没有晏照夜归来的消息。
食完粥又读书,书上的字越来越模糊,李知昼打了个哈欠,她困了,想小憩一会儿。
晏照夜的被衾整齐,李知昼躺在床上,熟悉的兰香包围着她,伴随她入眠。
李知昼做了梦,梦中她还是幼时,在晋州,有阿爹也有阿娘,她去学堂读书,下了学父亲就去学堂接她一同回家。
她沉浸在美梦中,醒时满脸是泪水。只有在梦中她才能见到阿爹阿娘。
李知昼一个人无声无息的流了半晌的泪,最后眼睛酸涩,头也痛。
窗外日头落了,侍女不知何时点上了灯,屋里总算不是一片黑暗。
翻身下床,不见晏照夜的踪影,她心下失望,想先回快绿斋,晚上再来玉清院寻晏照夜。
绿枝在玉清院等着李知昼,见李知昼眼眶泛红,使了个眼色示意众人不要多问,她跟着李知昼进了屋,轻声道:“女郎可要用晚膳?”
“不用。”
夜色浓郁,绿枝问了几次是否要用膳李知昼才松了口说用膳。
没滋没味地吃完一顿饭食,李知昼沐浴更衣想要早早睡下。
头上珠钗尽落,铜镜中年轻的容颜似是愁眉不展。
“吱呀”一声,晏照夜推门进来,他面色依旧从容,却隐隐有些不好。
他站在李知昼身后,同镜中的人对视,“听人禀报,说你在玉清院等了我半日,回来时眼眶是红的。”
闻言,李知昼转过身搂住他的腰,泪水涌出来,沾湿他的衣袍。
李知昼安静地落泪,一言不发。
晏照夜抚着她的肩膀,轻轻地将手覆在她的头上,“今日回来得晚了些,是我的错,玉娘不要怪罪。”
“与你无关,是我想阿爹阿娘了。”她的声音闷闷的,还带着哭腔。
李知昼仰头,眸子水洗过一般澄澈明净,唇如小鸟的喙,“过几日就是他们的忌日,我想回晋州祭拜他们,可以吗?”
克制住亲吻的冲动,晏照夜道:“明日我便去大理寺告假,同你一起祭拜父亲母亲。”
额头靠在他肩上,后背被完全地揽进怀中,轻微的呼吸声或是心跳在寂静的此刻格外明显。
李知昼不懂晏照夜对她情有独钟的缘由,她并无特别之处,甚至她只是利用他。
时隔多年再见晏照夜就以纳她为侧室为借口圈住她,将她留在身边。她当时慌不择路,为了活下去毅然跳进晏照夜为她设的陷阱,如今想来不知是福是祸。
王二郎是酒色之徒,吃喝嫖赌无不精通,李知昼在街上见过他,他身后跟着家仆,要往青楼去。
不过是二十岁的年轻人,脚步虚浮,獐头鼠目,任谁看都明白这是常年浸淫在酒色中的人。
倘若那日她回到晋州,在王家的胁迫下嫁与王二郎做妻子,与他成婚同房,那简直生不如死。
晏照夜不同,他洁身自好,内里再如何黑心黑肺,那张皮总还是朗月清风的,叫人看了就欢喜。
只一点不好,他太精于算计。李知昼常常怀疑他是否早就看穿自己心中所想。
她在晏照夜跟前娇气又爱卖乖,因为她吃准晏照夜爱她那副样子。
晏照夜喜欢李知昼依赖他,信任他,最好永远也不能离开他。
像是圈在缸里的小鱼,静静地游在翠绿的水草间,它自以为见过广袤天地,实则不过是水缸一隅。
李知昼不愿意做小鱼。
——————
最近在外地实习,大概没有时间写完了,抱歉ŏ̥̥̥̥ם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