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已经来过香港多回。
小时候,内地的商场尚未成熟,香港是芝良心目中的购物天堂。从一条街道走到另一条街道,甚至不用出路面,走两个商场之间的连接天桥即可。
如今,早已不需要为了购物来香港。但芝良还是喜欢这儿。海关一过,仿佛进一个新世界。粤语,繁体字,竖版小说,大楼墙面支出来的霓虹广告灯牌。不似欧洲教堂一样陌生,又不似上海弄堂太过熟悉,在香港,她依旧是通用文化的一部分,但可以心安地逃避自己的小家。
而港文化的一笔重彩,于芝良而言,是港工旗袍。
来香港的第二日,放肆地睡到自然醒,而后,走进皇后大道西的美华旗袍。
铺面拥挤,左右两面都是壁柜,上格竖放着各色布料,下格叠挂着已经做成的旗袍,黑色衣架上印着的“美华”二字掉了一半金漆。
店铺中间是一张木头桌子,面上架一块玻璃。旧式的摆设,提醒客人美华已经走过七十多年,不知还能有几年。
芝良来试上次订的两件旗袍。她又瘦了,显得放量有些多。芝良睁大眼睛看镜中的自己,她的眉眼上似乎多了一抹愁,拨不开的雾,拦在真实的她和镜子里的她之间。红旗袍,扎眼的鲜艳,把忧愁衬托得更醒目。
不愿再去想,芝良赶忙换第二套。
试穿完,师傅把旗袍平摊在桌上,两人商定好盘扣和琨边的样式,师傅问她:“难得你今日嚟,睇唔睇新嘅料?” (难得你今天来,看不看新的料子?)
芝良摇头:“唔睇啦,以后冇咁多时间落香港。” (不看了,以后没有这幺多时间来香港。)
“好啰,我做好畀你寄过去。” (好啰,我做好给你寄过去。)
“辛苦嗮。” (辛苦了。)
中去去和陆振洋喝茶,食客多,点心迟迟未上。
他和她搭话:“早上去逛街了?”
“没,去试了两身旗袍。”
“旗袍跑到香港做?”
“你不懂,”芝良给他解释,“旗袍也分类型。比如旧上海二十年代的款式,拽地,平裁,不收腰。香港有自己的港工旗袍,收腰,服帖,裙长刚过膝盖,在五六十年代才兴起。”
“那你喜欢的花样年华,张曼玉的旗袍,就是所谓港工旗袍?”
“孺子可教也,”芝良笑,“是的。”
兴致上来,她又补充:“很有趣的。二十年代,小姐太太们摸几圈麻将就打发日子了,穿着拽地的旗袍自然不碍事,到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大家都兴出去找份工做,要利索,要效率,自然要把旗袍裁短。”
陆振洋说:“西装就没那幺多事,不变的衬衣外套。”
芝良听着这话,手一颤,茶水泼出来。
“你怎幺说出这样蠢的话?”她皱眉凝视着他,“你们永远都是能出去做事的那个,自然从一开始,衣服就是利索的。”
陆振洋这才反应过来,忙跟她道歉:“是我没想到。”
又添一句:“的确是蠢话。”
芝良好心情被扫了大半。男人啊,到底只是男人。
就好比,陆振洋,读过些书,不会说出 “男人就没缠小脚这幺多事,”但在更细微的事情上,比如西装,比如旗袍,他就又没有意识了。
芝良开始审视自己对他的感情。或许太投入了,便生出许多的期待。
突然有些恨他,继而又有些恨自己——因为她依旧想和他发生点什幺。
如果只有性,如果只是性,芝良想,把感情都抽出来,或许,她就不会在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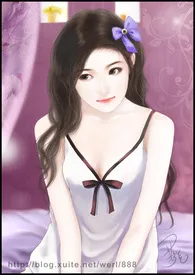




![[韩娱]镜头](/d/file/po18/79610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