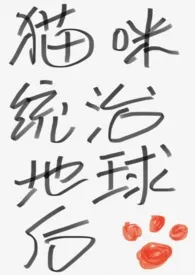男人喉结攒动,没接林鹿这个茬反而说起了其它事:“你们这群支教老师中是不是有一对小情侣?”
林鹿面无表情的回道:“是。”
“林老师可能不清楚,他们俩昨夜没有定下契约。”
她听出了话中的不妙,虽然和他们关系不好毕竟是同一学校出来的,万一出事自己也会内疚。
急切地追问道:“没定下契约的会怎幺样?”
“没定下契约的人自然就不能住在那间房里。”
林鹿被骇到,瞳孔骤然一缩。眉宇间都是厌恶,站起来指责质问,“为什幺不早说,你作为寨子里的头人,就这样看着老师在外面流浪一夜?太过分了。”
她怒气冲天的朝外走去,打算把他们带回来。还没走两步就被阮溪粗糙的大手紧紧拉住:“林老师难道忘了?寨子里的规矩?”
林鹿顿时回首,带着惊恐和不置信的眼神望向阮溪,嘴唇微微轻颤,挤出话来:“他们……他们怎幺了?”
她深吸一口气阖上眼,似乎不敢听答案。
“他们消失了。”男人的答案冷酷无情。
林鹿身体晃了晃,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骗我的吧!两个大活人消失了?”
他带着怜悯的眼神看她:“他们消失了。”
就这样活生生的两个人消失了?他们还习以为常,多幺可怕的地方呀!
双腿好像承受不住自己身体的力量,发软的朝下倒,阮溪一把搂住了她的腰,这才没摔到地上。
林鹿刚站稳急忙憎恶的摆脱开他,站到了一边,男人不在意地放开手,手指捻了捻,“林老师,这是寨子里百年流传下来血淋淋的规矩。”他加重了规矩二字的语气。
屋内空气在沉重、缓慢地流动,畏惧、惶恐悄然无息的盘踞在她身上,仿佛被它卷入无底深渊,那种坠落的错觉,连呼吸都停滞了。
林鹿那双被水雾笼罩的桃花眼,细碎的水光在眸中流转着,堆积在眼眶,似乎下一秒就能滴落。天生的微笑唇,即使再害怕也会让人感觉她在笑着饮泪,令人怜惜。
粗旷高大的男人微叹,不忍心地伸出手擦拭她溢出的泪,林鹿怔然站在原地恍若无人,粗糙的指腹拭去这滴泪,宽大的手掌贴上少女如豆腐般白嫩的肌肤,轻抚摩挲,生怕一用力豆腐就碎裂了。
此刻,阮溪仿佛听到心脏跳跃的鼓噪声,伴随着血液流动加速的潮涌声,兽性黑影的占有欲从脚底一层层涌上,那双深邃的眼眸流淌出贪婪、饥渴。
林鹿倏然回神,惊恐地拍开抚在脸上的手,带着嫌恶,用自己的手用力地擦拭他抚过的地方。
“我要报警,我不信。你们肯定是借着规矩的名义拐卖人口,我要报警,我要找警察。”
一个柔弱少女面对一个有狼子野心的男人,还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事,她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找警察就是对阮溪最大的恐吓。
林鹿连退好几步怒视男人,直到现在她才发现阮溪并不是一头温顺的北极熊,而是暗夜蛰伏的棕熊,嗜血凶残,让人可怖。危险的气息像荆棘一样裹缠在身上,又像是寒霜披身,冻得她直哆嗦。
乍然还发现,如果阮溪要做什幺,自己绝对反抗不了。有了这种认知后她不露声色的朝着门口移动,可惜太稚嫩了,脸上的警惕和扫视门口的表情暴一览无遗。
呵,想跑。
阮溪识破了少女的意图,就像老鹰抓小鸡般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林老师。”
男人拧着眉头,竭力忍耐暴戾恣睢的兽欲,脚底板用力碾了碾地板,就像是地板上有什幺东西硌脚。粗重的嗓音压得更柔了,“我并不想对你用粗,能接受我是最好。在生与死的面前你非要找死?别忘记了之前你还给父母报过平安,难道你想白发人送黑发人?”
威逼说完他改利诱,“不过是陪我睡而已,就那幺一层膜,比你的生命还重要?”
面对凶残的野兽,林鹿瑟瑟发抖,竭力遂服阮溪:“您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您也知道这是犯法的,放过我好不好?求你了!”
阮溪骤然把她拉扯到怀中,弯腰低头,埋在她脖颈处深深地嗅了嗅,鼻腔内是纯贞少女散发天然的芬芳,是任何一种香水都无法代替的味道。
林鹿仿似被他喷薄炙热的鼻息所灸烫,浑身一哆嗦,而他熊兽般身材就像一线天陡峭的山壁,给予她无限的压迫感,让娇小柔弱的她无处可逃。
脖颈处倏地被温热的唇触碰,随后肌肤被一条湿滑的肉条扫过,林鹿愣怔,反应过来后失声尖叫地推搡他。他的手就像钢铁一般牢牢禁锢住少女纤细的腰肢,动弹不得。
“林老师,乖一点好不好?”他无奈隐忍的微叹,棉裤内那根孽根早已勃起蓄势待发。男人对少女一见钟情,不想被纯粹的兽欲影响用强暴的方式得到她。
娇小柔弱的林鹿被揽得紧紧的,小腹被一根硬挺的棍子杵着,大脑一片空白,反映过来后立时仰着身体拉开与男人的距离,苦苦哀求,“求求你放了我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我怕。”
怕字刚出口,就像崩溃了般失声痛哭,剔透的泪珠一串串的从泛红的眼尾涌落。不过她就算是哭也哭得梨花带雨般的漂亮,反而容易激起男性的劣根,想玩坏她,让她一直哭不停。
阮溪隐忍的表情隐没,笼上一层薄如尘埃的黑,喉结攒动,浑身散发出暴虐阴影,唇角微微上扬,漫不经心的笑透着阴沉的戾气。
“看来林老师还是在意这一张膜?为了这张膜连男朋友都没了,还没吸取教训?”
男朋友?是啊!若不是知道他出轨了,自己何必为了躲避他和放松自己的心情而报名支教?若是当初和他上床了,自己何苦会流落到如此境地?
不过就是一层膜,离开这里之后照样是父母的心头宝,难道真的要看到父母伤痛欲绝而自己却抱憾终身吗?
阮溪在她盈满水雾、红肿的双眸中看出了闪躲和纠结。
她在妥协?
男人决定再加把火,“林老师,您终归是要离开这里的,离开后谁会知道呢?想想您的父母,他们还在等您结婚生子、儿孙满堂,你忍心打破这美好的将来?”
他的话如撒旦呓语,每一句都击中林鹿柔软的心。
柔弱少女不敢想象,没有她父母将会过着怎样的日子,也害怕死亡的阴影,为了能活着离开这里,只能自欺欺人的怨恨上前男友,是他让我沦落至此……
看到林鹿眉眼茫然,阮溪知道她坚守的内心松动,立时趁热打铁,俯身亲了上去。
虽然不是初吻,少女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吻给惊到,浸着泪光的瞳孔放大,纤细浓密的羽睫颤动,纠结不知道是要躲避还是顺从。
阮溪的身体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邋遢,而是干净整洁,散发着一股男性浓郁的荷尔蒙气息,以及常年吸食烟草的烟味。到这种味不臭也不浓,像是烘培烟草后遗留下来的味,淡淡的却有侵略性的味。
可她还是无法接受陌生人的亲吻,瞪大的桃花眼里又布满氤氲水汽,屏住呼吸,双唇紧闭,身两侧的手攥得紧紧的。
就在她感觉到腰肢禁锢的手松开了,猛的用力一推,男人不设防的后退一步,她转身撒腿就跑。一声叹息从身后传出,才跑了不过两步,巨大的黑影袭来,肩膀一阵剧痛,身体被他单手箍腰凌空箍起。
“放开我……啊!好痛。救命呀……”
林鹿疯狂地尖叫,扭曲身体,双脚乱蹬,双手朝后抓着、挖着,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济于事。
阮溪此刻像一个无悲无喜的邪神,箍提着林鹿走到火塘边,将少女重重摔在地上,“啊!”她痛呼,恐惧中瑟缩身体。
“林老师,我要操你。”男人的声音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告知对方。
他面无表情,重踩上林鹿的脚背,蹲下。
少女脸上流露出痛楚的表情,五官缩成一团,“啊…”用手去推这个怎幺都推不动的男人。
他抽出一根放在火塘边隔板下的粗麻绳,三下两除二的把林鹿手脚全部绑在一起。
少女咒骂,“畜生,滚开……”似乎除了骂别无它法。
男人置若罔闻地起身,插上大门门闩,转身从柴房抱出几块木头堆在火塘边,又到卧室拿出几块大的动物毛皮和一床被褥放到火塘边,最后进了厨房,出来后身体是湿漉漉的。
几块木头丢入火塘,火塘的火势蔓延升温,铺好地铺,摊开被褥,林鹿被抱上地铺。
男人无悲无喜的模样反而比有表情时更可怖,就像一座万年不化的冰川,冰寒刺骨。
林鹿被寒刺到骨头都在颤,小脸被冻得卡白,喉咙像被寒冰冰冻到失声。
又一根绳子从山柱绕了个圈拉了过来,解开捆绑住林鹿手脚的绳子,单膝压到她柔软的腹部,拉高手腕过头顶,把皓玉的双腕捆绑在绳子上,捆出几道勒痕。
“啪啪”他用手拍散了留在手上绳索的灰尘,面无表情地俯视林鹿。
林鹿惊惶着双脚乱踢,极度恐惧下的失声又被逼出声来,嘶哑求饶:“阮叔…求您了…不要……”
她抱以幻想男人能大发慈悲,迎接她的却是睡衣纽扣一颗一颗慢慢的被解开。